沈浩波论当代先锋诗歌(一)盘峰论争为什么?什么又是民间立场?

沈浩波论当代先锋诗歌(一)
——盘峰论争为什么?什么又是民间立场?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是诗人沈浩波所写的一篇三万多字长文,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一系列事件和在这些事件。文章深度探讨了盘峰论争、下半身诗歌运动、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时代与口语诗的成熟、“新世纪诗典、现代纯诗(口语纯诗和意象纯诗)、新世纪的抒情诗歌等诸多问题,为我们理清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起承转合的脉络。
一、下半身诗歌运动与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时代
二、口语的成熟与“新世纪诗典”
三、现代纯诗(口语纯诗和意象纯诗)与新世纪抒情诗歌
序幕:盘峰论争,是上个世纪的尾声,也开启了新世纪的中国当代诗歌
1999年4月16日到4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院等4家文学机构组织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郊区的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在这次诗歌研讨会上,持不同美学立场的诗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尖锐的论战,整个论战从会前到会后,持续了约三四年之久,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围绕这场研讨会的诗人论战后来被中国诗歌界命名为“盘峰论争”。
“盘峰论争”并非从盘峰宾馆的这场研讨会才开始。论争的氛围早已在会场外酝酿成熟。最初的肇始,来自于我的一篇文章《谁在拿90年代开涮》,其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三,这篇文章最初也只是发表在我所创办的北师大校园文学报纸《五四文学报》。文章的批评对象是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主编的,试图对90年代中国诗歌进行总结的诗歌选集《岁月的遗照》,并进而批评了在90年代新崛起的学院派诗歌写作者试图借助学院式的文学批评权力,构建一个完全由学院派美学主宰的当代诗歌秩序。我认为这种秩序的建立是对中国当代诗歌进入现代主义先锋性写作以来的一次重大的美学倒退,而学院派利用学院式的批评权力,对中国当代诗歌中明显的,并且成就卓著的先锋诗歌一脉进行了最大程度的遮蔽。《谁在拿90年代开涮》应该是90年代最早的一篇批评整个学院派写作体系并揭示出遮蔽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由北师大校园传播到了整个中国诗坛,80年代成名的中国第三代诗歌代表诗人韩东和于坚,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诗人伊沙纷纷给我写信,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1999年年初,韩东将这篇文章拿到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发表,伊沙则将这篇文章拿到西安的《文友》杂志发表。
1999年初,广州诗人杨克主编了一部《1998中国新诗年鉴》,于坚、韩东都是这部年鉴的编委,盘峰论争之后,我也成为这部年鉴的编委。《1998中国新诗年鉴》选入了大批被学院派遮蔽的,涌现于90年代的年轻诗人。后来成为中国小说界重要批评家的谢有顺,其时刚刚硕士毕业,来到广州从事媒体工作,为这部年鉴写了一篇书评,名叫《内在的诗歌真相》,同样有意无意地将批评的锋芒对准了以北京为根据地的学院派诗歌。我和谢有顺其时一个还在大学就读,一个刚刚开始工作,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都还没有与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什么关系,却因为这两篇文章,意外地成为中国诗歌界关注的对象。这两篇文章后来被视为“盘峰论争”的先声和导火索。我们虽然没有参与1999年4月的“盘峰会议”,但却在会上被学院派诗人愤怒地“缺席审判”,其后也都成为论争中笔战交锋的主力,也因此进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现场。这也是中国70年代出生的一代在诗歌界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场。
《谁在拿90年代开涮》和《内在的诗歌真相》侧重点其实差异性很大。这种差异性,几乎也就是“盘峰会议”被命名为“民间立场”一方的内部差异性。后来对“盘峰论争”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如坠云雾,至今难以阐明“盘峰论争”中被称为“民间立场”的一方,到底意味着什么?
盘峰会议的主持人,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吴思敬在“盘峰会议”上将论争的双方命名为“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一个即兴的命名。“知识分子写作”一词,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经过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程光炜等人的不断解释,涵义非常清晰,几乎成为中国学院派写作的代名词,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序言中已经将90年代的中国诗歌直接等同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这个词,则来自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一句封面广告语,其实并不能包含“盘峰论争”中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面存在的一方。
在“盘峰会议”的现场被主持人指认为“民间立场”一方的诗人,有于坚、伊沙、徐江、侯马、杨克和批评家沈奇等(代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诗人和批评家则是王家新、西川、臧棣、唐晓渡、程光炜等),而在会前会后论争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还有沈浩波、谢有顺、韩东、杨黎、何小竹、宋晓贤等。这个阵营实际上是90年代学院派试图树立起“知识分子写作”这一主流秩序之外的诗歌力量的聚合,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整体,因此也很难进行严格的命名。被指称为“民间立场”的诗人,有的认同这一命名,比如《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推动者于坚、韩东和杨克,韩东在“盘峰会议”后写作长文《论民间》,试图对“民间”一词进行解释;也有的对这一指称并不认可,比如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等90年代涌现的年轻一代先锋诗人。
另外,“民间立场”的诗人们对于学院派将自己命名为“知识分子写作”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学院派诗人们只是将诗歌当成了一种“学问”,一种可以操作出来的写作技术,而并没有体现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在90年代,学院派诗人们的诗歌被通过学院的批评力量,在所有官方报刊杂志上通行无阻,而真正的先锋诗人们的作品仍然更多在“地下”流通,很难被发表。这似乎也证明了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只是一种偷换概念式的自我命名,而并非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真正呼唤的那种反抗的道德。
盘峰论争中被指称为“民间立场”的诗人其实包含了这几个部分:
一是中国当代诗歌中口语诗人的集合。于坚、韩东、杨黎、何小竹分别是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大诗歌流派“他们”和“非非”的代表诗人,也是80年代中国口语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而伊沙、侯马、徐江、宋晓贤则是中国90年代最重要的口语诗人;沈浩波则在盘峰论争后,成为新世纪中国口语诗歌的代表人物。80年代的中国口语诗歌,被称为“前口语”,90年代的中国口语诗歌,被称为“后口语”。“民间立场”是当代中国诗歌中,三代口语诗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来对抗以学院派书面语修辞写作为主要语言方式的“知识分子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盘峰论争”在语言上的对抗,就是精神上更自由开放的当代口语写作与越来越陷入修辞崇拜和词语崇拜的书面语写作之间的对抗。
二是中国先锋诗歌力量的一次集合。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每一次诗歌发展,都意味着一场先锋与传统的对抗。“盘峰论争”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二次重要的诗歌论争。第一次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论争”。“朦胧诗论争”的主角是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北岛、顾城、舒婷、芒克、多多、杨炼、江河、严力等,和三位支持这群年轻诗人的重要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他们所对抗的当然是极权政治下的中国官方主流文学体系。由于这群年轻诗人的诗歌官方主流文学界读不懂,因此被命名为“朦胧诗”,北岛对这个命名显然并不认可,他更愿意将这批大多数成长于北京的,在他创办的地下文学杂志《今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称为“今天派”诗人。《今天》杂志也成为后来中国诗歌界民间的、地下的文学杂志的开端。所以,如果不知道“民间”一词中所包含的“地下”性质、对主流和秩序的反抗性质,以更自由和不断打破美学禁区为特征的“先锋”性质的话,就不能真正理解“民间”一词。自《今天》开始,到新世纪网络诗歌的兴起而终结,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发表阵地主要在各种各样的地下出版物上,也被称为“民刊”,即民间诗歌报刊。从1978年北岛、芒克创办的《今天》,到80年代的《他们》、《非非》、《莽汉》、《倾向》、《海上》,到90年代的《诗参考》、《葵》到2000年创刊的《下半身》,构成了长达22年的中国民刊时代。所谓“民间”,正是民间诗歌报刊的“民间”,正是地下、反抗主流与权威、自由意志与打破美学禁区的体现,是诗歌先锋性之所在。
进入80年代以后,“朦胧诗一代”战胜了陈腐的官方主流文学,北岛、顾城、舒婷们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他们所代表的文学经验成为新的主流和权威。这时,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已经在“地下”孕育和成长,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欧美的更多美学思潮大规模进入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不再是居住于北京的少数人能接触到的特权,而是更多地延伸进平民阶层。在这样的气氛下成长起来了新的一代诗人,他们普遍出生于1960年到1965年之间,更多地集中于成都、重庆、南京、上海等地,而不再是北京。这一代诗人后来被命名为“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这个叫法的含义,至今莫衷一是,但最初出自四川成都的大学生诗人之口。“第三代”诗歌形成了三个对当代中国诗歌有重大影响的诗歌流派,分别是“他们”、“非非”和“莽汉”。韩东、于坚、杨黎、李亚伟等80年代的重要诗人均来自这三个流派,并且都选择了口语化的诗歌写作,“口语写作”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主流诗歌语言的一种反抗。他们不满于“朦胧诗”一代建立于“意识形态对抗”基础上的诗学,主张诗歌与意识形态分开,建立一种更纯粹的诗歌,也可以被称之为“纯诗”。尤其是“他们”和“非非”,其诗歌美学的根基构筑在“语言”本身——韩东明确主张“诗到语言为止”——而不再是构筑在通过意识形态对抗展现的抒情诗意上,不再是依附于庞然大物而存在的那种崇高感、悲壮感和道德感上。以韩东和于坚为代表的“他们”诗派,是中国当代诗歌中“平民化”的开始,强调日常生活的诗意;以周伦佑和杨黎为代表的“非非”诗派,在诗歌文本上进行了更多的语言实验,追求一种更极致的语言探索(杨黎在这种语言探索过程中成长了至今为止中国最重要的语言诗人之一,并在新世纪的网络时代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废话”诗学),在精神上则明确反对那种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诗歌和建立在崇高道德基础上的诗歌;“莽汉”诗派则是中国最早的彰显生命意志的诗歌群体,也是“身体诗学”的最早尝试者,可惜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形成自觉的理论系统,在写作上也只是不自觉地浅尝辄止,其后,这个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如李亚伟等更多地热衷于在诗歌中彰显自己的修辞才华。“第三代诗人”在80年代中期之后迅速成长为与“朦胧诗一代”分庭抗礼的诗歌力量,虽然没有明确的“争论”事件发生,但却有着确凿的美学对抗。这同样是新的先锋对新的主流,新的秩序的一次对抗。无论是口语诗的产生、平民意志的伸张、语言诗学的建立、纯诗的态度,对文化、道德等“庞然大物”的反抗和对浪漫主义抒情诗歌的反对等,都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贡献。
在以口语化的先锋诗歌为主体的先锋诗歌为主体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席卷8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下,与“第三代”诗人同一代的,更多地继承了朦胧诗一代诗歌经验的一批诗人(后来在更多场合被命名“后朦胧诗歌”,以作为和“第三代诗歌”的区分),显得缺乏美学上的创新。这批诗人以海子、西川、骆一禾等北京大学毕业的,具有浓重精英意识的诗人,和以欧阳江河等部分四川诗人为代表,也包括其时在《诗刊》杂志工作的一度被视为“朦胧诗一代”晚期诗人的王家新,他们在早期更多地继承了“朦胧诗一代”建立在象征、隐喻基础上的早期现代主义诗学,和建立在浪漫主义美学基础上的崇高抒情,乃至肇始于杨炼和江河的史诗写作等。1989年之前,在他们的前辈“朦胧诗一代”和同辈“第三代诗人”的双重挤压下,他们的声音并未被彰显。尤其是海子、欧阳江河、廖亦武等人的史诗写作,更被证明为虚妄和无效。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8年,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以民间刊物《倾向》为阵地,开始尝试性地提出“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影响力很小,也并没有能够浮出水面。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写作”则成为以书面语修辞写作为特征的整个北京学院诗歌体系的代名词,因此容纳进了以更年轻的,北京大学毕业的诗人臧棣为代表的,更极致地以修辞和词语构成“纯诗”的一批现代性表征更强的诗人,这批诗人是肇始于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语言诗学在口语之外,向学院书面语体系发展的一支力量。
1989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这来自于两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一是3月份,北京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种惨烈的死亡方式令海子成为某种殉道士般的悲壮的抒情符号,同一年5月,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海子挚友骆一禾病故,更加重了这种悲剧的抒情氛围。海子和骆一禾的写作,都带有浓烈的根植于农业文明社会的浪漫主义抒情特点和根植于道德和文化的史诗写作特点,而这些正是第三代先锋诗人所反对的。海子和骆一禾的死亡,在80年代末尚未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构成了根植于农业文明社会的浪漫主义抒情诗歌大规模死灰复燃的道德基础,也令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阵地,这是当代中国诗歌中学院派力量的第一次爆发,也为根植于学院体系的“精英诗歌”的崛起提供了可能。
第二个意外更为巨大和深刻。发生在这一年的某场巨大悲剧,一举将80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积攒起来的自由、开放的精神力量消耗殆尽。随后,中国的政治气氛走向更为极端的高压,由此也带来了文化上的极度保守,文化和文学上的自由派和先锋派失去了社会根基。在文化领域的一切层面上,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以先锋、实验、反抗和自由为根基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戛然而止。与此同时,被压抑的中国知识界又在呼唤能为他们带来泪水的,能满足他们的良知和道德需求的文学,尤其是诗歌。而朦胧诗一代如北岛、顾城、多多等都已离开国内,远在海外,在1989年去世的海子和骆一禾因此如同祭品般被推上了神坛;其时在《诗刊》工作的,朦胧诗晚期诗人王家新以一首《帕斯捷尔纳克》迎接着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大规模进入90年代的中国诗歌。这是一个需要抒情,需要泪水,需要知识分子哭泣的时代。
与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三杰的西川,和继承了朦胧诗一脉道德抒情传统的王家新,以及从四川来到北京,早期写作史诗,后来转为隐喻和修辞写作的欧阳江河,代表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几股重要力量。欧阳江河、程光炜等诗人和批评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特点,开始将“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扩大到整个根植于北京的学院派体系,扩展到以学院书面语修辞写作为特点的诗人群体,北京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唐晓渡以及程光炜等大学教授的加入,使得“知识分子写作”获得了整个北京的大学院校批评力量的加持,北京重新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重镇,大学院校取代了过去的官方作家协会体系成为新的秩序中心,第三代先锋诗歌力量的现代主义诗歌成果被一点点吞噬。直到1998年,程光炜主编90年代诗选《岁月的遗照》出版,将“知识分子写作”与“90年代诗歌”直接划上了等号。这才直接导致了我的那篇《谁在拿90年代开涮》的产生,也催生了谢有顺为《1998中国新诗年鉴》所写的那篇《内在的诗歌真相》,令80年代第三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诗人于坚、韩东、杨黎与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90年代“后口语诗歌”的倡导和实践者伊沙、徐江、侯马等汇集为“盘峰论争”中的“民间立场”。
所以“盘峰论争”从诗歌精神上来说,就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第三次对主流和秩序的反抗。也是先锋派对传统诗歌价值观的反抗。与“朦胧诗一代”当年面对的庞然大物,中国官方文学相比,这一次的主流和秩序的代表者,是中国新成长起来的学院文学系统,“知识分子诗人”正是依靠这一系统获得了90年代的诗歌话语权。无论是官方文学的诗歌体系,还是学院诗歌体系,都是借助于社会化的庞然大物而得以存在并获得美学话语权,但真正的“民间”、“地下”和“先锋派”则永远站在任何庞然大物的对立面,更多依赖内在的精神探索、美学探索和先锋的魅力而生长。这一次的论争和对抗,也证明了80年代以来,中国地下的,民刊时代的先锋诗歌发展道路并未被中断,从前后语到后口语,从第三代诗人到伊沙、徐江、侯马、宋晓贤、贾薇;从《他们》、《非非》、《莽汉》到《诗参考》、《葵》再到《下半身》,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中国先锋诗歌一直在承继和发展,从未停止生长,只不过被新的主流话语体系遮蔽了光芒。
三是中国外省诗歌力量的一次集合。除了我在上文中所陈述的口语诗歌与书面语修辞诗歌的对抗,先锋诗歌与主流和秩序的对抗,“盘峰论争”其实还隐含了一层外省文学与首都文学之间的对抗,这同样意味着对主流的反抗。正如上文所说,“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体系首先是借助北京的,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学院体系完成了文学话语权的占有。而盘峰会议前后参与论争的诗人中,除了我和侯马之外,其他诗人都来自外省,尤其是南京、成都和广州。南京和成都分别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重要诗歌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代诗歌运动本身也包含了年轻的外省诗人们对位居首都的“朦胧诗一代”的反抗。杨克和谢有顺生活在广州,广州是中国最具平民性和世俗性的城市,《1998中国新诗年鉴》在广州出版,主编是杨克,云南的于坚和南京的韩东是其核心编委,而于坚和韩东在80年代,又是以诗歌的平民精神和日常生活美学为特征的“他们”诗派的代表人物。《1998中国新诗年鉴》与程光炜主编的《岁月的遗照》直接形成了选本与选本之间的对抗,如果我们把杨克、于坚、韩东、谢有顺称为“盘峰论争”中的“年鉴派”的话,就更能清晰地看到“盘峰论争”中这种外省与首都的对抗,平民主义精神与学院精英派写作之间的对抗。可惜的是,“盘峰论争”中构成“平民主义”精神的“年鉴派”在日后并没有真正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中彰显平民精神的文学人物,有的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
盘峰论争中,“年鉴派”之外的另一支“民间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被称为“北师大诗群”,包括伊沙、侯马、徐江、沈浩波和宋晓贤,均毕业自北京师范大学。这批毕业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诗人是中国学院文学体系的“逆子”,他们直接承继了8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先锋意志,并以更强烈,更坚决的先锋性与主流、权威和秩序对抗。在“盘峰论争”中,“北师大诗群”更多地代表着“民间立场”中的口语写作与先锋精神。这群诗人中,徐江与侯马的写作直到新世纪以后才臻于成熟,伊沙是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真正意义上的代表诗人。
如此抽丝剥茧,方能呈现“盘峰论争”的美学真相。这是先锋与主流,先锋诗学与传统诗学的对抗,是口语诗歌体系与学院化的修辞诗歌体系的对抗,也包含着平民意志与学院精英主义的对抗。
“盘峰论争”从上个世纪末延伸到新世纪初的头两年,时间大约是从1998年到2002年。一场论争为上个世纪的写作划上了句号,也为中国的“民刊”时代划上了句号,同时也开启了新世纪以为互联网为主要发生现场的诗歌时代。
(——原文刊载于《磨铁读诗会》微信号: motiepoems)
转自:http://www.qianxiwenxue.cn/qxwx/vip_doc/3440118.html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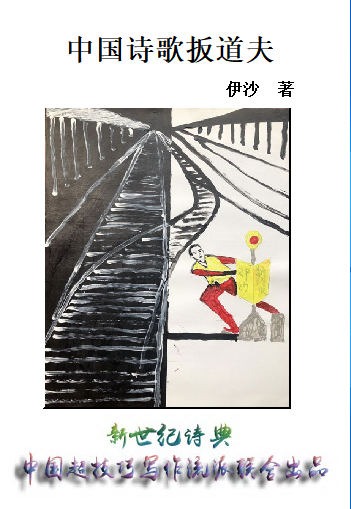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