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土著高晓松》(外三篇)伊沙

《北京土著高晓松》(外三篇)
◎伊沙(本文来源:诗生活伊沙专栏)
伊沙
我一直以为“知识分子”诗人是不说人话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说人话,用的是中国人唱意大利歌剧的那种美声腔调,真是把人恶心死了!而在他们比作品还多的“学术论文”中,总是不厌其烦地罗列:里尔克说了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又说什么,所以什么。他们从来不说:我说了什么。
我的成见终有被打破的时候,那是在不久前的一天,我在《阅读导刊》上读到了孙文波就“盘峰论争”的一个简短发言,短短三百来字的发言却是说人话的,人味十足的。但这是什么样的“人味”啊!
孙文波说:“要我现在再来谈谈对盘峰诗会的看法,我只能说:没有看法。那些由它所起始的诗歌论争,用我今天的目光看,除了给爱嚼舌头的人提供了一些话题,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的疑问是:既然孙文波对“盘峰论争”持这种虚无的态度,那么他干吗还要在论争结束后伙同王家新将“知识分子”一方的论争文字汇编成册出版,并再次盗用“90年代诗歌”的名义?照他的说法,出版的目的不是让更多的人嚼舌头吗?真是人爱掌嘴你拦不住。
孙文波说:“时至今日,我对我写了一些报纸小文很不以为然。我知道,如果盘峰之争发生在今天,我肯定不会说一句话。”
这是反思么?他以为人们会相信他反思的真诚态度么?“盘峰论争”也就是一年前的事,那时的孙文波比现在是小了一岁,但也是成年人啊!他那些“报纸小文”不是他自己写的么?谁逼他了?他现在是看结果悔当初,他不骂人他的平庸就不可能被揭露,难怪连一位“知识分子”的主将也在私下里说:“在盘峰论争之后,孙文波的平庸成了尽人皆知的事。”
孙文波说:“论争,如果论争就能产生诗人,那我们才要嘿嘿一笑了。”
我记得孙文波还在某篇论争文章的结尾处谈到过这么一个意思:让“民间立场”的人去论争吧,他们论争文章写多了就顾不上作品。真是可乐!这完全是高考前那些笨学生的心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指他这个以作品平庸著称,靠“知识分子”十年来的学术包装起家的人,却整天口口声声作品作品的,让人颇觉滑稽。王家新说:二十年后再看。看什么?我要没理解错的话,他大概也是指的看作品。他们真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作品吗?我把话搁这儿:我用我今天的作品和你们今后二十年累积起来的作品比,我今后二十年的作品另有比处(不是你们),就这么着了。
孙文波说了那么多,最后通向哪儿?他这三百来字没有标题但有题眼——“我要告诉别人的是:我已忘记那鸡巴毛的论争。”
“鸡巴毛”——这就是孙文波的“人话”吗?抑或是“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民间语言(以其对付“民间立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引用圣经的话来针对“知识分子”的某些无稽之谈,还不包括“鸡巴毛”之类。而现在,我像一个过路的人,面对路边的这堆垃圾,我的疑惑是:这是从哪个垃圾站运来的?
陈村是个“好孩子”
伊沙
有些人在烂掉,我说的是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在这里具体指的是一个名叫“陈村”的上海男人。
他喜欢整天呆在网上和一帮网虫厮混,那是我管不着的事。只是有一天,他忽然在电视机里倚傻卖傻地攻击起了现代诗,让我直想冲过去揪住他的脖领子。
“小说家一说诗,诗人就发笑”。说此话的是诗人徐江,他真是一不留神说出了一句当代名言。女小说家赵凝在一篇主要是针对我的文章中说:“很少见有小说家跳出来指挥诗人如何如何写诗的,但诗人就很狂,就可以告诉小说家怎样的小说好,怎样的小说坏。”赵凝说我一提小说家老马原马原的,而在我的印象中,赵凝提到诗人可是老徐志摩徐志摩的,这就是差距,这就是不对等,这就是我可以骂小说而你不能骂诗歌的根本。如果赵凝女士还是不服气的话就请看你的著名同行陈村先生在湖南卫视《新青年》节目中的腐朽表演。
当沈浩波、尹丽川等四位青年诗人各朗诵完自己的一首诗后,这个唯老不尊的陈村陈不住气了,开始大加攻击。让我感到邪恶的是他提到了于坚的《0档案》,他借此教育沈浩波说:你的诗缺乏形式感,而《0档案》就很有形式感。在我看来,在诗界于坚属于革命的一类,沈浩波属于继续革命的一类,用革命来压制继续革命,是为邪恶。而此种邪恶在陈村那里表现出的是小说家的浅薄(在我看来在中国的小说家身上从来都充斥着官文场的气息),他就是要用你们认可的名诗人来压你,一压一个准?借口“形式”什么的。但是我告诉你,于坚有于坚的形式,沈浩波有沈浩波的形式,他们之间不是相互取消的关系,你能谈出于坚的形式你就谈于坚,你看不出沈浩波的形式就不要断言他没有。
接下来令人喷饭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陈村要进行现场即兴做诗的表演,他以为这是玩古诗呐?古诗的形式是给定的,你即兴做诗的形式是刚从沈浩波那儿偷来的(你偷来了你认为没有的东西),你在偷来的形式里制造了一堆文字垃圾:我从上海来到长沙,见到一伙青年诗人,我们在房间里聊天,后来我们去吃夜宵了……别丢人了!你用别人的形式制造垃圾能证明别人形式的问题吗?小说圈里逻辑混乱的人真是太多了。
还有一个叫李冯的住在北京的广西人,过去也曾在《他们》上发过点诗,这点经历并不影响他说起诗来傻气乱冒,他说时代感并不是摸一摸发廊女的屁股就能达到的。针对的是我的《在发廊里》一诗。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混在其中的所谓“新状态”小说,是颇喜欢涉猎这种场所的,他绝对不是大惊小怪的要当卫道士,我知道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层鸟意思,就是写这类题材要有悲天悯人之心。除此就不能动用别的情绪了?我真是又一次见识了小说圈这类面瓜的智力。难道小说就真是等而下之的一类“艺术”?
还是回到陈村吧,他要自己烂掉你是拦不住的,还是在这次电视活动之前,有个记者问他:你和王朔见面,他会不会骂你?陈答:好孩子不骂人,我们见面喝酒。听罢,我心里真像是吞下颗苍蝇那般难受,是的,陈村是“好孩子”,写小说的都是他妈的“好孩子”。
北京土著高晓松
伊沙
印象中他是一写歌的,作词作曲都能玩。
印象中他的歌还是好听的,词也写得不错,《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什么的,挺单纯的好歌。
曾经,也就是在听到他这些歌的当时,因为曲风的相似性和他在歌词方面所展露的才华,我在瞬间对其有“大陆罗大佑”的期盼。但很快发现了这一想法的荒谬性,罗大佑可不仅仅是几首校园歌曲啊!再说像大佑这样的选手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出上一个吧?
后来他的歌也少了,听着也不像那两首代表作那么好听了,这也
没什么可奇怪的,中国做文艺的基本上都属于气短型的。
再后来听说他拍了一部电影,叫《那时花开》什么的。电影未得公开,但也炒成了一锅粥。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这年头媒体多如牛毛,记者总得吃饭。
这个人大概也真是“时代宠儿”一类的,一个写歌的,比前台唱歌的还要抢镜头,拍了一部子虚乌有的电影(据看过的人说拍成了乱七八糟的大MTV),就被认为是多才多艺无所不能。这也没什么的,这年头不连湖南卫视的那个李湘也认为自己是“多栖”的,这个人与那个李湘相比,不说是更有才华,起码也更有文化吧。
再再后来,又见此人去了一家网站挂了个什么衔,这更没什么奇怪的,名人奔网站这不是当今一大俗吗?
此人忽然叫我恶心是在不久前央视的一个谈话节目中见到他,当主持人问及他的“闪电结婚”的时候,主持人的问话是够庸俗的:那女孩子什么地方吸引你呀?作为嘉宾的此人回答得挺脱俗:美貌。看到主持人稍有疑惑,他赶紧又说:美貌,就是美貌。说一遍是脱俗,说二遍是庸俗,说三遍是恶俗。对脱俗的强调是庸俗,对庸俗的强调成了恶俗。听说此人还有在另一台电视节目中大抠鼻屎的表演,被一些人说成是“名士风度”,我想那不过是用行为演绎了一把以上所述的“另类怪圈”。
再再再后来,此人又出版了一本小说,大概是小说蒙事儿比前几项困难的缘故,文学记者也不似娱记那么好对付,此人忽然激动起来,那是在记者说他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上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不同意你对我小说的看法,我觉得我这篇小说是自己精心构制的,不是我胡写的。我老是觉得我特别有才华,一会儿就写完了……”看到这儿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如果你还是没有想起他是谁的话,我告诉你他叫“高晓松”。那副典型的北京土著的一副俗像在时下的报纸上不难找到。顺便说一句:这种有点聪明而要以俗为旗的北京孩子,如果内心里缺少了坚硬和大智慧的东西,就是满胡同爬的虫子而不是他们自以为是的龙。
无聊“十大”
伊沙
《视点》杂志推出“中国十大影视风云人物”,我得知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办刊人对办刊人的——《视点》的同仁们真的黔驴伎穷了?在我看来,现在实在没辙了才搞什么“十大”评选,而且搞了也是白搞,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九八年《文友》推出“十差作家”也算有我一份,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有恶心。但那时人民群众的觉悟普遍偏低,在我们之前好像也只有《海上文坛》搞过一个“十差明星”评选,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只要点找准,还是有效果的。所谓点找准,就是宁找文人不找明星。文人心理素质差,受不了这份刺激,他们自己会跳起来,他们一跳起来就有好戏瞧,其它媒体就会跟着忙得团团转,人民群众再跟着一起看热闹。明星在这种事上的心态真是太好了,你说我最差我管你呢!这只能说明我的知名度高,我忙着挣钱还来不及呢!所以我很难理解:气势很大的一本《视点》为什么又弄出这么一个“十大”,而且还是正面的,是“风云人物”。这也太小瞧劳动人民的智力及其品位了吧?我看那篇文章中说“与其它行业稍有不同的是,影视业的风云人物不是以成败而论的,这主要取决于他(她)在这个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什么叫不以成败论,你依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和成败是没有关系的吗?尤其是在影视业。这是狗屁不通的逻辑,主要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的矛盾与糊涂,他也不知道该以什么做标准,或者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当你用这个标准要求他时,他可以用另一个标准来进行自我辩护。
文人和办刊人老是觉着自己聪明,自己做的事更有道理。其实你要是真想以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标准来评,不妨索性来一次真的群众投票选举,结果可能是很有意思的,邓建国也绝不可能当选“十大”更不可能位列头名,群众的趣味有时候比文人更单纯。他们表现出的愚昧也是耐人寻味的。比如说在1999年,各种“百强”、“百优”之类的世纪评选层出不穷,其中只有群众选出的“十大”是有点意思的,在群众的眼里,琼瑶、金庸、三毛是可以和鲁迅列在一起的,贾平凹、王朔的当选也就没了光荣感可言,相反倒是鲁迅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里显得不对劲,那是群众的自卑和矫情造成的。现在,我面对《视点》推出的这个“十大”,连琢磨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我明知这是两个自由撰稿人自以为内行的小算盘。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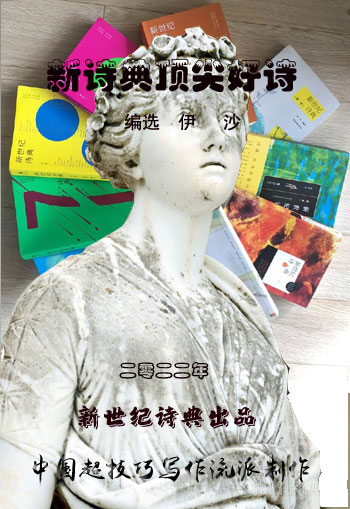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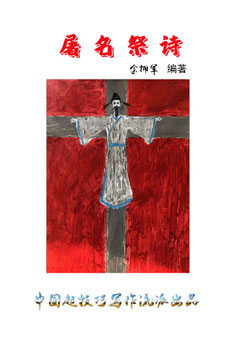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