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论当代先锋诗歌(三) ——现代纯诗 PK 抒情诗

沈浩波论当代先锋诗歌(三)
——现代纯诗 PK 抒情诗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是诗人沈浩波所写的一篇三万多字长文,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一系列事件和重要的诗歌现象。文章深度探讨了盘峰论争、下半身诗歌运动、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时代与口语诗的成熟、“新世纪诗典、现代纯诗(口语纯诗和意象纯诗)、新世纪的抒情诗歌等诸多问题,为我们理清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起承转合的脉络。
三、现代纯诗与新世纪抒情诗歌
我虽然是口语诗运动的重要倡导和参与者,但并不是一个唯口语主义者。事实上,我自己写作中,亦有重要的部分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口语,对于意象、修辞等常规的书面语诗歌手段多有涉及。我对口语诗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倾向亦有疑虑和质疑。
一是,口语诗运动中的偏重技术,偏重口语经典化的一支,正在形成某种更坚决的“纯诗主义”倾向。
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大抵就是一个不断“纯诗化”的过程。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一代的质疑,以及提出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乃至非非主义的“反抒情”、“反文化”、“反崇高”,再至杨黎、何小竹以“废话主义”为旗帜的语言乌托邦,以及学院派诗人对于词语和修辞的极端强调,其实也都走在一条“纯诗化”的道路上。80年代纯诗化写作的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是建立在语言诗学基础上,即用纯粹于语言本身的态度来反对诗歌的抒情功能和其他社会功能。
随着新世纪以来口语诗歌在语言和技术上的成熟,口语纯诗与书面语纯诗(意象纯诗)相比,具有更为幽微而深刻的迷人魅力,且更能实现当代性和通往后现代主义。也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开始以“纯诗”的标准来要求自我和同行。这当然是当代中国诗歌在观念上的进步,使得诗歌不再承担额外的社会、文化、政治功能,不再试图通过对任何庞然大物的依附,通过对任何人类集体情感的应和来“打动读者”,诗歌的写作不是为了实现“意义”,更不是依赖读者对诗歌所实现的“意义”的解读来达到诗歌的效果,而是纯粹于微妙的内在“诗意”,选择以心灵智性、心灵洞察力和敏感度为基础的“诗意”和“诗性”,而非“揭示意义”和“抒发感情”,让纯粹的诗歌本身展现内在的迷人美学,让“诗”本身而不是其他动机和目的成为写作的核心。这使得诗歌从观念上来说更为高级,进一步成为某种专业性更强的文体,也越来越形成了只有少数优秀诗人自身才能成为合格读者的现实。这确实祛除了诗歌写作中很多“非诗”因素,明确并凸出了什么才是“诗”这一终极命题。
“纯诗”是诗歌现代性的内在体现,或者可以将命名为“现代纯诗”。
现代纯诗在中国的发展,其实一直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口语诗运动中的当代中国口语诗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口语诗歌,终于大规模地抵达了“现代纯诗”,其成熟的标志在于,不再像80年代的早期口语诗歌(或被称为“前口语”),更多地将诗意建立在语言本身所形成的语感效果上,而是如上文所说的,不仅拥有了语言,还获得了身体,注入了灵魂,实现了个性;另一条线索是,沿着欧美现代主义诗歌已经被验证过的现代性美学,尤其是从“意象”诗学(从20世纪早期庞德等英语诗人树立的“意象派”,到詹姆斯.赖特,勃莱等诗人倡导的“深度意象诗”,乃至像法语诗歌中博纳富瓦的用现代性美学改造此前的象征主义的美学表现,其实依然在“深度意象诗”的范围内,再至中国当代诗人更为熟悉的特朗斯特罗姆,意象诗学的发展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现代性诗学线索,用“意象”来成为诗意的凝著物,让诗性显形和形成超现实的通感,反对抽象的抒情、空洞的言说和功能性地解释意义)中汲取经验的写作方向。
可以将这一美学系统的写作称为“意象纯诗”,1983年,接触到特朗斯特罗姆后的北岛,可能是当代以来,中国大陆第一位走向“意象纯诗”的诗人,在此之前的北岛和整个朦胧诗体系,其实都在写作一种抒情诗歌或象征主义抒情诗歌,现代性贫弱。朦胧诗的另一位在当时略显边缘,但后来证明其写作的实际重要性远远高于同代人,并且在新世纪显得越发重要的诗人严力,也是从很早就进入现代意象纯诗的写作体系,并以超现实的语言智性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他在当时之所以没有显示出重要性,恰恰是因为他的诗歌很早就抑制了抒情和意义,在朦胧诗一代普遍以抒情或象征性抒情为特点的风潮中,显得有点超前。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运动,口语诗逐渐成为现代纯诗的主流,除了孟浪等少数意象诗歌的写作者外,意象纯诗在这一阶段被淹没在第三代运动的口语潮流中。此后的“意象纯诗”在中国书面语诗歌系统中的发展,非常奇怪地偏向了某种带有语言实验性的,以“词语”和“修辞”为写作特点的学院修辞学写作,从意象纯诗转向了其实更带有语言诗学特征的“修辞诗意”,虽然仍然在现代纯诗的写作轨道上,但语言大于内在的心灵感,导致诗性减弱,语文化的组词造句式写作占据了上风,诗歌变成了一种修辞的学问,而纯正的“意象纯诗”越发式微。
这种从根本上来说建立在语言诗学基础上的诗意实现方式,其实与80年代早期口语诗异曲同工,只不过,一者依赖修辞,一者依赖语感。“意象纯诗”的式微,在我看来,除了建立在80年代以来“诗到语言为止”的语言诗学大环境基础上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意象诗的语言载体往往是书面语,而书面语同样也是传统抒情诗歌和象征主义抒情诗歌的语言载体,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积淀过于深重的古老国家,即使是时代已经发展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人内心中普遍的文明意识依然大规模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对抒情的偏好使得大部分从意象出发的诗人,迅速地滑向了抒情。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意象纯诗需要更冷峻、深沉、复杂的心灵,而这,好像是中国人天生缺乏的,中国的意象派们又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意志去建筑这种心灵人格。这么说可能会更为清晰:口语纯诗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意象纯诗对应的标准的现代主义,而带有象征主义特点的抒情诗更多对应于前现代主义。
新世纪以来,即使在学院修辞写作体系内,也没有出现新的重要诗人。虽然中国一些具有诗歌传统的著名大学里的年轻诗人们(尤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为代表),仍然普遍在用这种方式写作,但很少有人能写出新意。在我看来,作为“意象纯诗”分支,或者说是“意象纯诗”分支进入高校象牙塔后变种的修辞学写作,本身在美学上因过于狭窄而缺乏进一步发展的通路。最能展示出重要性的,仍然是几位出生于60年代的,成名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已经因病去世的第三代诗人张枣和供职于北京大学的臧棣,此外,桑克、周瓒、姜涛、胡续东、韩博、蒋浩等也是其中的代表性诗人。张枣的诗歌发展大致经历了抒情诗、意象纯诗和修辞化的意象纯诗三个阶段,在新世纪的头几年,张枣在进一步沉迷于他在意象纯诗基础上的修辞实验,展示了他奇妙的词语想象力和修辞想象力,他试图构建更复杂的以词语、意象、修辞为基础的诗歌结构,以达到一种更深刻的语言效果,但我个人还是更偏爱张枣前期和中期建立在情感和心灵基础上的抒情诗和意象诗。而臧棣则创造了一种日常修辞学的诗歌体式,后现代特征明显,他创作了大量的即兴式的诗歌,用自己的语言系统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并将一切语言化,呈现出事物被语言化之后另一重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以臧棣为代表的学院修辞派诗人,虽然在90年代同样被容纳进“知识分子写作”的阵容,但与王家新、西川等抒情特征明显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相比,其实更接近现代纯诗范畴,而“知识分子写作”从命名本身就可清晰看出,具有明显的“反纯诗”特征。
另一些经历过书面语抒情诗、意象纯诗、意象纯诗修辞化路径的诗人,由于更强烈地收到后现代主义美学的感召,以及对意象纯诗和学院修辞诗歌等书面语诗歌系统无法展现足够的当代性的焦虑,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走上了一条也许可以被称之为“杂语化诗歌”的尝试之路。即在诗歌语言中大量加入各种具备当代社会属性、当代媒体属性的传媒语言元素(也包括各种杂糅进的陌生化语言元素,当然更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的杂糅),加入一些直接的甚至是口语化的面对当代生活言说与直陈,其中典型的诗人是西川和孙文波,也包括局部的陈东东和柏桦(这两位诗人更多地着力在语言层面)。但这其实只是让诗歌容纳进了一些当代元素和当代特征,体现出一种表面的后现代美学,仍然缺乏内在的,更有生命力的当代性。并且这种写作付出了巨大的伤害纯诗性的代价,或者说,其本质就是“反纯诗”的,是以“不纯”为代价,以一种由内到外的芜杂,来强行实现当代性,有点倒洗脚水倒掉了孩子的感觉。而不是那种,有效地将“不纯”消化进纯诗的内在探索,更不是对纯诗本身美学容量进行不断拓展的美学尝试。齐白石在谈论中国画时,有一句话,用在这种“杂语诗”的尝试上,也很合适: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诗如果写得太像诗了,太像传统意义上或大众肤浅理解意义上的诗的话,是媚俗;但太不像诗,太芜杂,太杂语诗化,就有可能完全丧失基于心灵的内在诗性。“欺世”这个词太严重,我能理解书面语体系中滋生出来的这种“杂语诗歌”写作潮流,的确是基于对诗歌创作本身的某种内在焦虑,也尊重他们的艺术尝试,但其效果很可能是南辕北辙。臧棣的诗歌中,也试图容纳进大量的杂语,尤其是现代学院里的各种学术性术语,但控制得比较有效,这些“杂语”只是其语言修辞学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是目的。
同时,另一个迹象是,更为纯正和宽阔的“现代纯诗”,在新世纪一些年轻诗人的创作中,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迹象,70年代出生的诗人李宏伟、80年代出生的诗人里所等,其写作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但与此前的现代纯诗诗人相比,他们的写作语言变得更为灵活,容纳进了更多口语特征和基于事实而并非完全基于语言的内在诗意,这种紧密围绕内在的诗意核心的容纳,就显得更加自然和得体,并非是生硬的为了杂糅而杂糅,这使得他们的诗歌既具备了更能被辨识的心灵感,也具备了当代性的可能。而在一些口语特征明显或者说往往被认为是口语诗人的年轻诗人中,也出现了容纳进意象特征的写作方式,并因此形成了充分的语言个性与个人气质,比如出生于80年代的诗人旋覆和苇欢。纯正意象诗歌的复兴以及口语和意象的交融,可能将越来越成为新世纪中国诗歌的一种现象。
即便我如此清晰地揭示出“现代纯诗”的重要性,但我依然对将“纯诗”的意义绝对化保留疑虑。当“纯诗”变成一个非此即彼的真理式判断标准时,我就一定会质疑。我同意对抒情的限制和尽可能的压缩,但这一定不应该是绝对的,一定有一些足够尖锐、诚实和强大的情感,哪怕采用传统抒情诗的方式,其情感本身的迷人亦足以令诗歌散发另外的光芒;一定有一些站在文明高度上的追问和思辨值得用诗歌这一文体来承载;一定有一些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洞察构成批判和洞察的诗意。而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纯诗”论所能概括和穷尽。美学的发展永远是辨证的,任何美学思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流之后,都应该注意其绝对立场所带来的偏见和偏狭。很多时候,美学的惊喜并不来自顺理成章的发展,而是来自意外。先锋与传统,永远是既对立而又在互相汲取。站在一个更高级的立场来说,“纯诗”的文本本身是否有容纳进更多“不纯”的胃口和消化能力,以“纯诗”的现代美学精神来容纳进更庞杂丰富的“不纯”,甚至容纳进意义,容纳进情感,但最后仍然抵达“纯诗”的效果和境界,并让纯诗变得更自由、开放、生动、先锋,对很多以现代纯诗为追求的诗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同样的原因,我对口语诗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另一个绝对倾向,或可称为“口语原教旨主义”,亦持质疑态度。当代一些重要的口语诗人,纷纷采用一种更为彻底的日常化口语,并将这种口语形态,称之为“纯口语”,并进而将这种纯然的,彻底的口语语言,视为唯一先进的诗歌语言。而在当代中国诗歌中,除了标准的书面语修辞写作和纯口语写作,更多的诗人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往往处于这两者的中间状态,带有书面语特点的口语和偏口语化的书面语。 在我看来,不同的语言形态,在杰出的诗人那里,能展示出不同的美学效果,承担不同的美学责任,具有不同向度的有效性。我对口语诗的提倡和践行,当然是因为其更符合我本人对诗歌的理解,尤其是,我以为口语,尤其是纯口语,到目前为止,最能承担诗人自由、反抗与创新之先锋精神,而这正是我的追求。但我依然不喜欢将口语或者“纯口语”绝对化、唯一化、标准化。我以为这反而与自由与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比如说,不是已经有足够多的优秀诗歌文本,显现出口语容纳进意象后所呈现的魅力了吗?
基于我对上述几种绝对化倾向的质疑,站在更客观的生态现场来考察新世纪当代中国诗歌的生长,还有一些重要的诗歌现象和美学变化值得被高度重视。
一是,重要的女性诗人越来越多,并且这些重要的女性诗人一旦出现,其精神气质比起男性诗人往往更为凌厉,文本辨识度也往往更高。我并不太喜欢“女性诗歌”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诞生和存在,本来就更意味着男性诗歌的主导地位。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新世纪以前,每个历史阶段,只有极少的女诗人显示出其重要性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不同年龄段的杰出女诗人如井喷般涌现,各具特点,精彩纷呈。王小妮、小安、娜夜、蓝蓝、尹丽川、巫昂、宇向、吕约、君儿、琳子、唐果、西娃、旋覆、春树、鬼鬼、莫小邪、李成恩、宋雨、从容、安琪、图雅、湘莲子、里所、苇欢、闫永敏、冯娜、易小倩、玉珍都是在新世纪有重要表现的诗人。其中,既有在某一阶段体现出极强先锋性的女诗人如尹丽川、宇向、巫昂、春树、旋覆。也有先锋指数虽然不高,但情感浓度、精神纯度和写作重要性尤为突出的诗人如王小妮、西娃、君儿、宋雨。王小妮是从朦胧诗时代一直到新世纪,始终保持着旺盛创造力和文本重要性的杰出诗人,其内敛、强硬、深沉的抒情质地,令她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最好的抒情诗人之一,虽然她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抒情诗人,但其诗歌中的抒情性确实大于现代性,我认为这并未损害其在新世纪诗歌中的重要性。西娃在本质上也是一位抒情诗人,但其诗歌并不缺乏现代性,她诗歌中的宗教感和生命意志,口语、意象、抒情,混杂成了一种奇异的文本质地,真挚、浓烈、神秘、浑浊,她在用一种非常强大的姿态进行写作,用情深、着力大,硬碰硬地往心灵的深处写。西娃与君儿、宋雨、从容都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首先以抒情诗人的形象引人注目的女诗人,她们的抒情特征和题材范畴各不一样,均拥有很强的个人辨识度,也都是心灵感和精神性强大的诗人。其中西娃、君儿和宋雨显然充分意识到了抒情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她们正在走向一种更深刻的,现代性更强的抒情方式,或者干脆走上了口语诗歌的先锋之路,她们是新世纪第二个10年到目前为止写作成熟度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三位女诗人。
不仅仅是女诗人,整个中国诗歌,在纯口语写作和学院书面语修辞写作之间的广阔地带内,带有一定现代性的抒情诗仍然是中国诗人的主流写作方式。与上个世纪流行的那种传统的土得掉渣的乡村抒情和情感粗糙嗓门却很大的社会主义抒情诗歌相比,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诗人,抒情的方式也开始多元起来,现代性程度和口语化程度也都在不断加大。另外,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及的,中国官方文学期刊,尤其是诗歌刊物,在互联网时代重新找到了立足的读者根基,由于官方期刊必然的保守风格和意识形态下的安全边界所注定,先锋性强烈的口语诗歌和晦涩难懂的书面语修辞写作都不可能被其真正接纳,但它们也必须跟上时代的进步脚步,体现出部分能被接受的现代文学性来,因此,这种带有一定现代主义因素的新世纪抒情诗歌便成为官方刊物的首选和宠儿。很多官方诗歌刊物的编辑自身也是诗人,也大都写作这种抒情主义的诗歌。而且抒情诗歌也确实容易被更广泛的读者接受。《诗刊》杂志成功推出的女诗人余秀华,就是一则典型的案例。
在抒情诗向度上,只有现代性越强,情感纯度和真挚度越高,精神性越强,生命意志越强的诗人,才有机会成为真正重要的诗人。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一位出生于60年代前期,在上个世纪的写作并不成功的资深诗人脱颖而出。身患重病的潘洗尘一跃而成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我认为潘洗尘和西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好的两位抒情诗人。他们都拥有更现代的抒情写作意识,拥有很高的情感真挚度、浓度、纯度,也都呈现出明显的口语写作特征,尤其是,都能直指生命的内核。尤其是潘洗尘,他的每一首杰作都像是命运对他的褒奖,并且越写越自由,越写越开放,他甚至将抒情诗写出了先锋感。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语言纯诗的开创者,早期口语诗歌的领袖韩东,其在新世纪诗歌中的抒情比重越来越大。韩东的诗歌其实在80年代和90年代,本来有两条美学线索,一条是纯诗倾向明显的,以语言本身构造和实现诗意的口语纯诗,但令一条脉络则让他获得了更多读者,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深具抒情特点。这两条脉络的并存,令他既成为8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领袖,又同时获得了先锋派之外更多读者的认可。进入新世纪以来,其“语言诗学”的特征仍然明显,但开始开始更加放大内心中抒情的一面,并更加追求一种优美、温和、润泽的典雅语言效果,语言上也越来越倾向于意象特征明显的书面语。韩东在新世纪的抒情诗歌这一向度上,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抒情诗人。与韩东这种语言诗学和抒情相结合,构成优美、温和、内敛抒情风格的,还有武汉诗人张执浩,在新世纪同样收到较大关注。另外,在90年代和新世纪头10年,以建立在奇诡意象基础上的语言实验著称的,并且创建了“不解”诗派的语言先锋诗人余怒,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诗歌中的抒情含量也在大幅度提高。
在“新世纪抒情诗歌”范围内,还出现了某种带有明确“主题抒情”特点的写作,比如诗人雷平阳以其故乡,中国边陲省份云南为主题的写作,他试图向尚未被现代文明完全蚕食的边缘生态,向被称之为“蛮荒”的原住民的文明深处拓进,用诗歌记录下这种吞噬、蚕食、对抗与死亡,呈现出一种哀歌与挽歌式的抒情。从某种程度而言,雷平阳的社会性程度较大的写作,恰好是“反纯诗”的。再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民族题材写作,抒情性非常浓烈,中国的少数民族诗人往往更停留在传统抒情诗的写作范式中,藏族诗人德乾恒美、卓仓果羌也是现代抒情诗写作中的佼佼者,其中卓仓果羌更接近现代纯诗的写作,并开始转向先锋性更强的口语纯诗。近年来,新疆的一批用维吾尔语写作的维吾尔族诗人,他们的诗歌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翻译成汉语,引起了汉语诗人的关注,这些维族诗人中的佼佼者们也同样是以传统的抒情诗写作为美学根基。相比较于汉族的新抒情诗歌写作者而言,少数民族的抒情诗人们情感更加炽热和尖锐,但内在的现代性则更弱。
同样以这种“非纯诗”的主题抒情,在新世纪获得更大关注的,是被称为“打工诗人”的群体所创作的“打工诗歌”。这些诗人都是有过在工厂、工地打工(以农民工为主)的经历,并通过对打工经历的控诉式抒情诗获得关注。由于“打工诗歌”强烈的社会属性、现实属性和话题性,很容易被知识分子、媒体和欧美的中国社会研究者们纳入到自己的解读体系,获得了“被解读”的文本传播力。广东女诗人郑小琼一度是这个群体中影响力最大的诗人;2014年跳楼自杀的年轻诗人许立志,去世后其诗歌开始被广泛流传。以许立志为例,无论是持“纯诗”立场的口语先锋派,还是热爱抒情的更广泛的知识群体和诗人,对他的评价都比较高。这是因为出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许立志,其诗歌写作正处在一个迅速的成长阶段,正在从一个抒情诗人向真正的现代性诗人蜕变。持“纯诗”立场的口语先锋派们已经读到了许立志的几首写得非常现代,祛除了“非纯诗”抒情因素的杰作,这些作品从诗歌本身来说显然更为高级,代表作如《悬疑小说》。但像《悬疑小说》这样高级的纯诗杰作,并不能得到更多的流传。那些对诗歌内在美学认识较为浅薄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媒体人和学院里的文学批评家、诗歌研究者们,更多地还是在解读和流传许立志那些写得并不高级的“打工抒情诗”,这些诗歌靠其社会性、主题性、控诉式抒情获得了传播。但无论如何,许立志之所以能从众多打工诗人中脱颖而出,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依然是因为其诗歌,哪怕是“打工抒情诗”,其中的现代性含量也比其他打工诗人更高,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具备一定现代主义特征的抒情诗,与现代纯诗相比,其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与诗意的实现方式。现代纯诗的实现方式是语言和心灵,抒情诗的实现方式则是通过情绪、情感甚至情怀。心灵和情感不是一回事,心灵更内在,更客观化,在诗歌中往往体现为心灵智性、心灵洞察力和心灵敏感,是心动、感受、发现、洞察、创造。或者说,语言敏感和心灵敏感共同构成诗性的根本,其中“心灵敏感”更为根本,口语纯诗中所重视的“事实的诗意”正是或者说必须建立在“心灵敏感”的基础上。而情绪和情感,固然是建立在心灵基础上的,属于心灵敏感的一种体现形式,但与内在的心灵敏感相比,却更外化、更夸大、更主观、更缺乏微妙。所以,纯诗强调内在的诗性,而抒情诗则更外在,更依靠“以情感人”的情感号召。从观念上看,现代纯诗更为高级。但具体到写作实践,却不能完全绝对地以观念的高低来评价诗歌成就。杰出的抒情诗歌,往往因其真挚、锐利、浓烈、深沉、疼痛等品质而具备生命含量。高级的抒情诗,必须具备精神和情感的现代性,如果没有这一点,那就缺乏了现代诗歌美学的一切根基。
一些杰出的当代抒情诗人,比如西娃、君儿、宋雨、马海轶等,也正在越来越自觉地转向现代纯诗的创作,这种转向,意味着诗性基础的改变,一定十分艰难,但一旦内化成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写作优势,即她们有能力让更丰富更复杂的生命体验和人生体验纯化为诗,将情感内化为更敏感的心灵。我们永远不能低估现代诗歌中情感的力量,只不过,情感也需要现代化,需要更现代的情感,并将这样的情感内化入诗,而不是抒发成诗,这样的抒情诗,其实已经同样具备了现代纯诗的那种更高级的艺术效果,同时又有着内在动人的情感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抒情与现代纯诗的边界将会取消,现代抒情诗也将成为现代纯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可称之为“抒情纯诗”。而一些以口语技术和口语智性为根基的口语纯诗写作者,也应该意识到,如何完善自己的语言敏感、扩展自己的生命感受,丰富诗歌的内在心灵空间,而不是自恃观念高人一筹。只有观念,而缺乏内在的生命质量、心灵层次和复杂性的话,容易陷入单调、干燥和另一种意义上的粗糙,尤其是,不能将心灵、心智、智性导向唯智和炫智,那将失去“心”。
在新世纪抒情诗歌的这一特别广阔的范围内,被关注较多代表性诗人还有娜夜、蓝蓝、李南、商震、树才、杨键、沈苇、独化、唐果、周瑟瑟、陈先发、谷禾、谭克修、朱零、蒋雪峰、明迪、廖伟棠、东荡子(因病去世)等。
最后,我想谈及当代抒情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方向,即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说是带有强烈知识分子心灵特质的抒情诗歌,这是一种精神性抒情。比如我在上文中提到韩东诗歌在新世纪的抒情化,他的这种抒情化其实还具备了某种清晰的知识分子心灵特征,追求心灵的纯净与崇高,向往某种圣徒式的灵魂。
与 “盘峰论争”中自我命名为“知识分子写作”的那些诗人相比,我以为,新世纪以来至今,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也才开始成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必然首先是精神与心灵层面的,而不是知识层面、技术层面和姿态层面的。追求知识分子式的心灵纯净感或崇高感,站在文明与良知的立场上追问和思辨,追求光明、救赎与正义,洞察邪恶,反省灵魂,体现气节、烛照人性,凡是以上等等,方可被称为真正的建立在知识分子心灵基础上的诗歌写作,这也一直是诗歌这一文体愿意主动承担的一种写作价值。但对于诗歌而言,如何使得诗歌不至于沦为某种社会层面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工具和武器,而是恪守诗歌本身的律令,内化为一种遵循诗歌美学的精神性文本,是衡量这种“知识分子”性写作是否具备足够文学性的的底线标准。
我愿意将新世纪以来这种带有明显知识分子精神抒情特征的诗歌,称之为“新知识分子写作”。任洪渊、黄灿然、朵渔以及部分的姚风,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事实上,我在上文中放在先锋诗歌序列和口语诗歌序列中重点提及的诗人徐江,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
出生于50年代,偏居于澳门的姚风,直到新世纪才开始显示出其写作的重要性,并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越发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中成就较为突出的诗人。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均站在人类文明的根本立场上,站在文明一边,表达对文明的亲近与渴望,对反文明的质疑与抗拒,是姚风诗歌中重要的主题。他写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与现代文明碰撞时的荒诞与隐痛。当然,与其诗歌中的知识分子性相平衡的,是姚风的语言和控制力使其诗歌更具有内在的纯诗特性,甚至其现代纯诗性更大于其知识分子心灵抒情;而长期居住在香港,近几年才搬回中国内地的诗人黄灿然,则在诗歌中展现出某种知识分子式的崇高与洁净的心灵感,这与韩东颇为相似;作为“下半身诗歌运动”发起诗人之一的朵渔,在“下半身诗歌运动”结束后,转向了一种“形而上”式的诗歌写作,其诗歌中的道德感,与现实黑暗的对抗感,以及对崇高价值的追寻,均带有鲜明的知识分子书写特质。
诗人徐江往往并不被视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式诗人,甚至在很多时候,他被视为这种写作的对立者。这与他作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现代性的重要鼓吹者,以及在中国的口语诗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通常人们更愿意将他与伊沙、侯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这从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徐江的独特性。在我看来,徐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式的诗人,对良知的秉持、对崇高的憧憬、对文明价值的追问和探寻,均是其诗歌写作的基本底色。只不过,他并不站在任何已被确定的集体价值观上来展示这一切,而是更个人化,更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与解构特点。令研究者难以对其进行归纳。他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一个异类,他在试图让个人心灵、抒情性、口语、现代理性经验、人类文明价值在诗歌中得到共生。
我想特别重点地提到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任洪渊,今年已经80岁了。在退休前,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伊沙、徐江、侯马、桑克、宋晓贤、朵渔、南人、沈浩波等当代重要诗人都是他的学生,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他在新世纪创作了几组非常重要的涉及历史与文明的史诗性力作,其中《1967: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1972:黄昏未名湖》是自上个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诗人第一次用如此强硬的内心姿态来撞击“文革”这个在今天几乎已快被遗忘的重大题材。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人格的巨大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一座无边无际的囚禁灵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可悲的是,40年来,中国诗人并未为这一场中国人的灵魂灾难贡献出足以匹配的重大杰作。新世纪以来,朦胧诗一代的诗人严力重新对这一题材发起了进攻,并屡有名作。但我以为,就诗歌内在所抵达灵魂深度,以及精神之严峻深沉凛冽而言,直到任洪渊的这两首诗,尤其是《1967: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才真正算是有一位重要的诗人用“正面强攻”的姿态填补了这个空白,提供了匹配的文本。这是两首带有史诗性质的心灵悲歌,但任洪渊先生又没有将笔力停留在悲歌的阶段,而是试图进入更深邃的沉思、追问与求索。任洪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诗人,他不是那种概念和主义里的“知识分子诗人”,不炮制说法和概念、不巧言令色、 大言欺世,他依赖的是心之至诚、思之至深、诗之至强硬,他因此才会为自己,也为一代人在《1967: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中留下了这么一副悲怆的自画像:一座低首、折腰、跪膝的遗像。唯有将这低首、折腰、跪膝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心中,并以此为永恒之罪,才能构成救赎之光。
(——原文刊载于《磨铁读诗会》微信号: motiepoems)
转自:http://www.qianxiwenxue.cn/qxwx/vip_doc/3440231.html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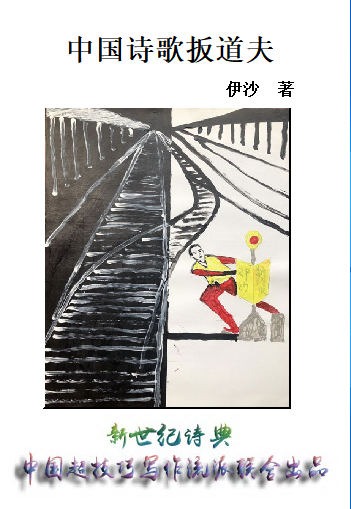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