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坚和伊沙的访谈

对于坚和伊沙的访谈
时间:2003年8月
地点:西宁某宾馆咖啡厅
人物:
于坚:诗人 伊沙:诗人
唐欣:诗人、兰大博士生 马非:诗人、《快乐青春》副主编
郭建强:诗人、《西海都市报》专刊部主任
黄少政: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 韩涛:《青海铝业》编辑
吉敬德:《西海都市报》记者
郭:两位能否简单谈谈关于诗歌语言的问题?
伊沙:许多动感的语言在空洞地消费,只不过我们知识分子没有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实际上,我觉得应该首先恢复这个。多少民间民众在饭桌上玩着他们的舌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但是你的写作对不起这个东西。中国现在有些短信中聪明就表现出来了,幽默智慧就表现出来了,这种东西一直在用,包括文革时期也一直在用,只是你的写作对不起这种资源。(民间语言在)唐诗宋词不明显,元曲特别明显——元曲一定是北京大都人说话的方式,元曲就非常对得起那个时代汉语的活力。所谓每个朝代文学差,只是作家没有能力或意识承担这种相衬。老百姓的语言永远是活的,再压抑的时代也永远是活的。比如文革时代,民间(语言)也有幽默,歌谣,也有鬼故事,不一定是黑压压一片,大家整天都在背着毛主席语录说话,并不是那样的。我们反而对口语和非口语并不是那么在乎它细节上的差异,我们反对的另外一种语言只是它没有活力,因为它的语言资源全部来自图书馆。当然同时我们也警惕那种带着哈拉子、带着口水直接进入书面的这种方式。这是相互挤压,几重压力中的创造。
黄:我认为你们做的这个工作是北岛开始做的一个工作,从70年代开始,大家都在这中间做这个工作。你们做的这个工作给中国诗歌证明了两个问题:1.诗人是民族的智者,诗中是有智慧的,我们诗中没有智慧已经很多年了,可能一千多年了吧。自从那几位大诗人走了以后,我们的诗中已经没有智慧了,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是诗人作为我们民族的语言的保健师、医生,恢复语言的活力,使得诗歌的抱负能够满足民族的这种文化的需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真正的诗歌的文本。北岛提供了一些,包括食指也提供了一些,最近看到的更多一点。诗歌文本在这个时代开始确定下来。我对诗歌划分的年代不一样,我认为胡适、李金发他们,这是第一代诗人;第二代诗人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代是从北岛开始一直到你们。
于坚: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一个灭生的年代,它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创造的心灵世界彻底毁灭。我觉得从我们开始的这一代诗人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心灵世界,心灵世界当然也包括智慧。既然用这种汉语来写作,而且这种汉语如此有活力,那么我们的文本要对得起这种汉语。什么样的汉语是最牛逼的,我认为是一种有灵魂的汉语,这种汉语应该是让别的民族,别的语言的读者看到后就会对这个语言肃然起敬,而不是标语、口号、大字报,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说到口语,我认为口语这个概念并不成立,没有口语这种东西。我们可以说普通话,又可以规范普通话的考试。全国的公务员可以用统一的试卷进行普通话考试,但是口语就不能这么做,你说你规定一个口语试卷,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口语只跟记起的人的口发生关系的时候,口语才存在。如果我不说这是伊沙的口,这是马非的口,这是唐欣的口,我就说不出什么是口语。在这之外的口语是不存在的,这是我最近发表的东西。
诗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象北岛那一代人“我不相信”,也不是知识分子写作在书斋中搬弄语言,也不是年轻人认为用口语写就是好诗,都不是。我觉得它就是要重新回到心灵的自由创造,舌头的自由狂欢。我觉得一个诗人在任何向度上都应该可以自由地使用你的舌头,使你的灵魂获得释放,你使用文言文也可以,使用书面语也可以,你使用自己的母语也可以,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只看结果——文本,这个文本是否能使我们感动,而不是你写的文本象庞德,象博尔赫斯,而是文本能否让我们感动,如果感动了,即便是文言文又怎么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两个朋友分别要走了,我们还会念上一首“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个并没有时间的隔阂,如果再具体地谈起,就象李白刚刚把这个诗写完,扬长而去一样。这种什么语并不重要,今天为什么现在很多诗人会强调口语,因为相比之下,你自己的身体语言是最有活力,离创作最近的东西。当然,胡说八道也容易创造,有很多诗人就看到这一点,他觉得只要我口里面能说,我写出来肯定就是一种创造,但实际上,从表面看很容易的创造,实际上又是最难创造的东西,他必须要创造之创造。如果你用已经有标准的文本,比如说你用翻译的模式来写,大家一看诗就是这样的,你这个诗人肯定就会马上被承认。如果你用自己的口语来写,要承认你是诗人很困难,就象伊沙,今天中国很多人不承认他是诗人。你承认他是诗人要有智慧,不象海子或某些诗人的诗,中学老师教我的诗就是这么写的,大家一看这是个诗人。看伊沙的诗你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你要把你心中的知识那种的魔障全部破除,你要相信你感动了没有,你要忠实于你的心。如果你觉得感动了,你应该承认这个感动,你不要去承认知识,因为知识说这个不是诗,你看,海子写的那种才是嘛!他这种不是嘛!但实际上你非常感动。好比我们去谈恋爱去找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种美人,你的标准是刘晓庆啊、巩俐啊这样的,但是这个女人的善良、贤惠,她的心灵之光,她的肉体的光辉使你感动了,但是你不接受她,结果你永远当鳏夫,你找不着对象。还是要回到内心的感受,不要相信知识对你的那种遮蔽,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没有创造力,他也没有那种对抗自己知识的〔自己照片的遮避〕的能力。很多人去塔尔寺,他自己的眼睛不存在,他必须要有一个导游告诉他这是什么什么,没有导游,他什么也看不到:这破房子一堆,回家去。标志是回到心灵自由的判断,回到感觉。
黄:刚才你说到文本很重要,我跟马非交流过这个观点,我觉得17世纪18世纪普希金建立了一个文本,所以俄罗斯文学从此就有了一个标高在那儿立着,大家写作时就有了个高度。但是我们现代诗从1911年开始实际上没有文本嘛!所以我们的诗歌这么低劣。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建构这个文本,而不是象普希金一次性就把文本标在这儿,莎士比亚一次性把文本标在这儿,他这种语言写作永远有一定的标高,不会把诗歌写得太滥了。但你看从1911年到现在这么多诗人在做什么呢?白干了。
于:文本的建立除了作者的努力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比如《诗经》中那些诗已经存在了几百年,那些作者早就存在了。但孔子一出来删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是孔子把文本系统建立起来了。文本系统作者自己不能负责,是不是文本我觉得是时间的问题,作者只管抒发他自由的心灵。实际上,历史总是选择最强大的灵魂的文本作为文本,这个作者不用担心。这要留给时间证明。实际上关键是你的诗在你的时代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打动人心,每首诗都能打动人心,但是有的非常肤浅,就象在皮肤上敲了一下,但是有的可以穿透整个灵魂,甚至可以穿透时间,而且他的诗是生长性的,就象塔尔寺一样,十年前来是一种感觉,五年后你来可能又是一种感觉,十五年后又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生长性的。
伊沙:我觉得现代汉语从白话文运动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看到了某些独立、成熟的语言,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为什么这样讲?我觉得比如说口语意识的觉醒开始发展得非常慢。在80年代以后,口语意识的觉醒把这个进度加快了,或者找到了一条路,以前没有路。以前也有很多干扰,比如毛泽东说,只能向民歌学习,只能向古典诗歌学习,这就是一种干扰,不能向外国诗歌学习,什么庞德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一种人为的干扰。还有一种来自于创造意识的匮乏,你比如五四时代,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靠胡适的想法,白话诗从胡适开始,可能郭沫若基本上同样的早。他们的想法,尤其是胡适,郭沫若可能还好一点,他主要的想法是怎么样把古诗转换成白话诗。郭沫若作为诗人,他的天然感强一些,所以他就抓激情,他就用浪漫主义的东西来写,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可笑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很幼稚、很粗糙了。在这个时期,凡是同古典文学关系比较近的作品就显得成熟一些,显得圆润一些,或者同外国文学关系近,就显得成熟。实际上这就说明语言草创时期的幼稚,她只能依赖,对古汉语、翻译来的外国文学只能依赖,是这样一种关系。当然到了艾青好一点。语言上第一次相对成熟是艾青,我们总结说艾青的诗歌有点散文化,实际上所谓的散文化是艾青真正地有一点“说”的意识,把“说”的意识带到了诗歌里,中国的古典诗歌基本上是唱的,是吟的意识。过去是吟唱,古诗的特点,艾青是第一个把“说”带入诗歌的,当然这个说还是非常不自由的,是一种还是小心谨慎,甚至是在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幼稚的。后来,比较成熟的诗歌还是这个情况,比如说台湾的50、60年代的诗歌,包括余光中、洛夫、痖弦实际上他们的作品还是呈现出这一点,比如说,我认为痖弦的文本非常成熟,还是对中国古诗的依赖感非常强。如果我的修养好,我的古典文学修养好,我就牛逼,这在台湾文学里是一大景观。谁的国学修养好,谁就牛逼,还是在依赖的状态,直到北岛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朦胧诗依然是这样的,朦胧诗写得好的,在舒婷那里你看到的是宋词的修养,在北岛那里你看到的是他读翻译作品的修养。所以还是靠修养写作,这个是不独立的。就是说我吃狼奶比你多,或是我有机会吃狼奶,或者是靠一些天然的诗人才份,比如说芒克,他靠天然的。只有到了于坚、韩东的口语的觉醒,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可能性的开始。这时候,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舌头是最重要的,图书馆不重要。从80年代发展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认为她的成熟在于什么?就是图书馆我也不拒绝,你如果能够回到我的舌头上,你有使用性。我的观点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认为被使用性最强的语言就是最有活力的语言,哪怕那种语言是非常粗鄙的,是那种厕所文学,如果你老在使用她,她就是最有活力的。那么我们最不使用的就是线装书里那些语言,如果你能让她有使用性,你就可以使用她,没有,就让她暂时搁在一边。用我们的舌头重新去检验图书馆里的语言,包括外来的。你看在80年代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一个开头唤醒了中国所有的先锋小说作家。先锋作家叙述进入复杂叙述的开始。二十年来,这个东西被先锋小说家已经普及化了,在一部分中国文人中普及化了,甚至变到口头上。我有一个证据,球评界有一个球评人叫李承鹏,在新世纪的一篇足球报道中,就使用了这样的开头。这种语言模式自80年代来到中国,作为先锋作家的一种笔式,一种特权,先锋作家的一种标牌,现在成了足球评论员调侃的语言。你说进入了没进入生活?它已经成为我们汉语的一部分了,轻易使用的一部分,虽然你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叫一些东西还不够普及,实际上还是普及了。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成了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所以说从口语开始,现代汉语容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非常成功。要我书面,我想书面就书面,我想调侃书面也可以,我想玩书面也可以,我想玩古典也可以。她现在已完全有这种能力。
黄:你说你对北岛来说你就是在抢银行了,你解释一下你抢了些什么?
伊沙:如果在你成长的时候,在你18、19岁时,你想成为一个男子汉,突然有一个人在诗歌中呈现了,你就读到了北岛的诗。这个男子汉穿着风衣,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对自己的爱人说,不,我要去受难。做为18岁的你就被俘虏了。这就是我要说的,这对你的成长是有用的,包括刘晓波对我的成长是很有用的,但在今天来看,该怎么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碰到了他们,你的骨骼正在发育。那么老于对我来说是专业意义上的一个发现,我突然知道写诗不是青春的爱好,我要做诗人的结果,让我突然发现我能写诗,我能写很好的诗。他的道路让你一下觉得自己在语言上有才能,他是专业的。北岛是一个少年的理想,是少年发育成长的方面的语言。
黄:严力呢?
伊:中国诗现代化的进程是很慢的,中国诗现代化进程不是知识分子的那个意义,是一个文明都市人的色彩,这个通俗地说是中国诗写得土,严力是我觉得写得比较洋的,真正洋的。多多的诗写得土,多多的诗是一副红卫兵的腔调,北岛的诗也写得土,严力是一个真正的天然的西方状态的(诗人),他不强调什么,不夸张什么,但所有的情绪都在,而且游戏感很强。
于坚:他是朦胧诗中的一个另类。
黄:我觉得诗人最后无法回避的是,可能是一个小诗人,可能写成大诗人,可能写成大师。我看普希金给自己写的墓志铭,他说:“人们不会淡忘我的,因为我的诗歌在人们心中唤起了善良的情感,我在这个专制的时代在讴歌自由。”我认为诗歌里存在两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北岛的工作并没有做完,他在这里讴歌自由正义,哪怕他的文本并不成熟,但这个工作并没有完成。因在我们今天的诗歌里,这个任务应该由谁来做,让我们看到很成熟的文本。
伊:这项工作以更内在的方式进行、进行、一直在进行。北岛的那种对自由呼唤只是一个开始,那个开始是很简单的,是一种姿态。你呼唤自由这个词和你真正呈现自由,我去用我生命的自由感动读者,去教会读者自由,换取读者的自由,是两个层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后来做的事情比他做的事情更不表面,更内在,可能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一个读者站出来说:“正义啊……”
黄:从文本角度看,诗人与专制政权玩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北岛定义的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被追捕人同追捕者之间的一个距离。他这种感受我觉得是来自生命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没有过去,不象西方已经进入文本时代了。他没有这种张力的,在体制之间和个人的表述,在话语的纠斗之间。所以有很多文本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能指符号的自身复制了。我们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人怎样用他们的智慧来产生文本,让人民都看懂。因为普希金天天在皇宫周旋,作品被下层人民捕捉到,人民能够怀念他,他给人民提供了一种大怜悯、善良的东西。普希金不仅给18、19世纪的俄罗斯人树立了一个标高,给全世界的诗人都树立了一个标高,他经得住翻译。你说你们做的更隐秘,我希望从你们的文本中也能读到这些东西,一个民族渴望看到这些东西。
伊:我的观点是随着中国的优秀诗人越来越成熟,中国今后每遇到一个新的广场事件的时候,就越不会站出来,实际上就是说在十年前广场事件中站出来的诗人都不是最优秀的诗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专业的成熟和他们每天都在发生作用。关键是真正优秀的诗人他们每天都在发生作用,你要说他们在解放人,他们每天都在解放人,如果你阅读诗,他们就解放了一个人。他们用不着站出来,因为站出来是最简单的形式。我觉得这是跟过去时代不一样的。
唐:而是展示什么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生活。
马:每天发生作用和就那么一下,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黄:我同意你的说法。普希金天天同沙皇在周旋,他没有站出来,从来没有站出来,他周围全部是命妇、贵夫人,但他的诗歌里头,大家都能感受到┉
伊:你这个有点是事后作为人文学者该如何界定这个事情。每天同沙皇周旋,但是我觉得,我特别要强调:诗人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凡胎肉身,对他来讲,就是他的生活而已。包括李白一样,你很难说他就是在跟统治阶级周旋。
于:你不能说他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你不能说他是暗藏在谁的身边。他就是如此生活,他自然而然就会代表全人类发出那种声音。你象歌德一样,他的周围都是什么大公,他和大公的关系也是真实的,不是敷衍他,确实是他的朋友。但是他写的都是最牛逼的诗。象李白可以去皇宫跟高力士在一起,只要稍有可能他就会写诗给杨贵妃。我觉得诗人最重要的是这种自由和灵魂是通过诗歌呈现出来,而不是对自由的一种呼喊,而是诗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但是北岛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他肯定只能首先呼唤自由。由于他对自由的呼唤,才会有到我们这一代对自由本身的那种呈现。
黄:诗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要反应出人民的呼唤。
伊:我认为满足人们的呼唤和把人民看成是〔庸众 〕(相比),我觉得我们的境界更高了,因为满足人民的呼唤,你实际上是带着一半政治家的思想。你觉得人民是可以利用的。这种诗人很容易和政治家穿一条裤子,成为一种天生的桂冠诗人,就是人民是可以呼唤的,国王呼唤他,我作为首席诗人也可以呼唤他,你呼唤他干什么?
郭:他们的声音同专制者的声音其实是一致的。
伊:我们已经把“人民”这个词实事求是地说叫做〔庸众〕,因为他对我们的存在就是吞噬。你跟人民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你不要自作多情。如果有一天,我的诗、老于的诗象余秋雨的散文、汪国真的诗歌那样拥有读者,那么我们就完蛋了,我们的诗歌一定在某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可怕的裂变。你肯定完蛋了,或者说你失效了,你是靠一种强权在执行这个东西。
于:我对这个问题反思是很深的。我认为“人民”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人民是什么?其实没有人能够说出来“人民”到底是什么。你看,我写这首诗很可能是因为伊沙在这一瞬间感动了我,我这首诗为他而写。由此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感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这一瞬间。这个里面要有诗人自己的生命质量和知识结构。如果他是一个很牛逼的诗人,他就包括一切。他既有你说的反专制的东西,也有反知识的东西,我觉得他就是反抗一切。那个一切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压抑生命不让她自由的东西。那个东西在一切范围,不是来自沙皇,也不是来自秦始皇。压抑来自各种范围。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代,某种压抑构成了单一的力型,大家都注意到了这种压抑,象北岛那个时代,但有很多普遍日常的压抑就被人们忽视了。到了现在更多的普遍压抑通过我们的作品得到了释放,不仅仅是表面的自由的诉求,而是灵魂彻底解放的那种诉求。象李白,李白的诗也不是在呼唤反抗唐王朝专制,他和唐玄宗打得火热。为什么他的诗千古流传,他的自由精神是天地的自由精神。
伊:直接就打开你的身体。
于:如果你反抗的只是一个时代的专制,这个时代一旦过去,你的诗就结束了。那种自由只是暂时的。
伊:当时代背景的压力一解除,比如说北岛的诗,他去了国外,他的所有诗马上就魅力顿失,所有的艺术感染力都没有了。这也是诗人幼稚的地方:他必须放在一个背景下,诗才张力无比。一旦没有这个背景,一下就失效。你说,他对文革有感觉,他对现代化的压力和焦虑,难道就没有感觉?他孤独得要死。咱们去北欧,那都是他走过的路。在那儿空虚孤独,难道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压力?怎么就表现不出来了呢?所以说这种反抗决不是政治工具的反抗,它一定是诗人的反抗。
郭:于老师和伊沙能不能 评价一下当代诗歌的大体。朦胧诗之后,第三代到现在,大致勾勒一个轮廓。
马:给普通读者勾勒一个大致的线条和你们的主观评价。
伊:其实刚才有些话题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只是谈的不是那么具体。就以朦胧诗开始谈起。朦胧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历史时期的一个产物,当时中国诗歌的先驱艺术表现的是高干或中干以上,中干高知以上的子弟。他们有一个阅读上的特权,就是吃狼奶的特权,他们能够咬到狼的奶头,而别人咬不到。所以你看朦胧诗的作者群里除舒婷和梁晓斌以外,全都是北京人。这个就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权的结果,他们可以读到作为批判材料的所谓灰皮书,从顾城的答问录里可以看到他读到过洛尔加等人的东西,当时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是根本读不到的,他拿这个东西来写,这种艺术在最快的时间里,能够在我们当时的文艺环境中显示出他的性格或独特性,就是因为他跟世界发生了关系,实际上是“拿来主义”,模仿的东西。
于:也就是刚才谈的,他需要依靠这个东西,依靠西方的东西才能存在嘛!
马:借助外力。
伊:这代诗人的特点是有一些做了诗人之外的事情,做了广场发言者的形象,这是时代的一个特征。这一代诗人贡献非常大,文学史说破除坚冰,这些作用都完成了。我说他们模仿也不抹杀他们的创造。因为包括西方的学者也在讲,他们欣赏北岛的诗歌,最关键原因不在于他的艺术形式,因为这种艺术形式对他们讲是非常落伍的,斯蒂芬· 欧文讲是他们五十年代的,如果放在瑞典就瑞典50年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没有新鲜感,斯蒂芬·欧文非常尖刻地说:北岛的诗经常让西方诗人想起他们的少年时代的作品。如果你要是有尊严的话,你的尊严就受到了污辱,你说北岛和他们是平等的艺术家吗?不是的。他是把你看成了另一类,他们可以原谅你的技法非常落伍,那么什么东西在吸引他呢?就是他呈现的现实,他呈现的现实的相对的质感。
于:他的背景。
伊:他在北岛诗中读到的中国的现实与中国当时的现实吻合度比较大。而此前的贺敬之、郭小川那都是颂歌式的,他们在厌倦那个的同时读到北岛的诗歌,他们也兴奋。这种从阅读到写作都是一个大的非常时期的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到西方去,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诗人对外影响最大的还是朦胧诗人。原因是什么?你问他们,原因是在那个时期的汉学是显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汉学是显学,他们搞这个东西很热的,他们这个抓一个北岛,这个抓一个顾城,这个抓一个杨炼,他们就是看政治的:中国人在反思文革的灾难,现在他们准备进入另一个时代,是带着这种目的去阅读的。这是一个特殊的,所以我们既肯定真正的诗人在这中间的创造,也要看出他的特殊性,这个时代,朦胧诗人的活动,意识创造活动基本早已终结。可以各个分类看:北岛今年出版了在多少年以后在国内出版的诗集,我想,懂诗的人都会看出这本诗集被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国内曾经激动过大家、感染过大家的作品,另一部分是他在国外的作品,这部分作品已经丧失了他的感染力,为什么,因为前一部分的诗歌是在对抗文革,让他的感染力全部升发出来。我觉得杨炼认为他始终是个混子,就是一个文化混子,他在写抒情诗的时候,就是这种意象,基本抒情诗的时候,也是朦胧诗人中写的最差的一个人,最笨的一个人,几乎就是进来就是可笑的,后来他突然怎么就雄起了,他借助的就是中国古文化的这一套符号化的东西。我们在谈李白是产生一种生命上、精神上、灵魂上的想唤起、想沟通,他是一种完全(死胡套的),注释易经啊,这一套东西,然后把他与西方所谓的现代主义的技巧嫁接在一起,来哄骗老外。因为老外对你这一种符号化的东西是恐惧的,对那一套阐释系统、对那套表现系统又是熟悉的,他对你的句子是熟悉的,对你阐释的内容又是惧怕的、神秘的。这就是杨炼对于西方的魅力。严力和北岛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状态,他企图想表现西方,但是发现是无力的,他在表现西方和表现中国的时候,那是有区别的。你在表现资本主义对你的压迫的时候,实际上在虚构了某种东西,你与其那样去表现,你不如回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以那一代人是一个特殊的产物,包括他们的已经具备的文化素质什么的。不是很多西方意义上的流亡作家的概念,什么精通几门外语,可以进入别人的文化,他们一直在外国做中国人,写着一种想象中的中国。即使是严力,他试图想进入,但他没有美国的质感,他写不出美国的质感,包括他的形式也落伍了,意象的方式。他表现不出美国的具体形式,纽约的具体形式。他还是思考型。
马:他最好的东西还是以中国为背景的东西。
伊:这一代已经过去,不用谈那么具体,第三代请老于来谈。
于:刚才他讲的就补充一下。朦胧诗这一代诗人的主要年龄段实际不是在5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是49年左右
伊:共和国的同龄人。
于:算的是知青这一代,高一、高二、高三这一代诗人,他们主要的诗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北京的,都有干部子弟的背景,当时干部子弟有中国内部专门印一种灰色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翻译很多的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一般人看不到。多多在1974、75年写的一首诗叫《致茨娜塔耶娃》,我最近才看到,感到很吃惊,那个时代象我们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茨娜塔耶娃。对于我们这种生活在中国外省的诗人,没有这种接触资料、资讯的机会,那么我学习诗歌的道路是走民间的道路。我是通过在文化大革命烧书禁书以后,残余下来在手上秘密流传的手抄本,唐诗、宋词,还有俄罗斯19世纪的作品,包括普希金,普希金对我来说,是我一个如数家珍的诗人。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自己摸索的,走的是民间道路。比如说朦胧诗当时还有一个不大被提起的诗人:贵州的黄翔,黄翔这个诗人实际上是很有才华的,但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读过现代派的作品,他东西比北岛表达的“我不相信”还要强烈,他在1965年写的诗就是,那个“巨大的怪兽虽然卡住了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吼出我的声音”,非常强烈。1965年写的,北岛那个时候根本不敢写这样的诗,但是他使用形式的全是旧浪漫主义的东西,他不可能接触到西方的东西,他在贵州嘛,很边缘的地方。黄翔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诗人,后来我读到黄翔的诗,我真是觉得非常震惊。那比“我不相信”强烈多了,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在里面,这是要补充的部分。
当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时代肯定要选择一个东西来表达时代自己的声音是吧,朦胧诗的崛起是官方选择的结果。大家以为朦胧诗是一个地下,实际上不是的,朦胧诗是先在《今天》上私下流传,在很快就被《诗刊》接受,80年
伊:77年、更早。
于:北岛的诗后来是在《诗刊》上登出来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那个时代很需要这种声音来表达当时中国的情绪,不是现实。朦胧诗没有表达现实的力量,朦胧诗不是现实主义,她是抒情主义,她表达的是那个时代的情绪而不是那个时代的现实,真正表达那个时代现实的反而是艾青,我觉得,艾青在1976年写的《站在列宁像下》、《两个工友》都比他们的诗有现实主义。朦胧诗恰恰是回避现实,通过一种曲折迂回的修辞方式来传达那种反抗精神。比如说我不相信,你知道他说的不相信什么?我们都以为他说的是我们想的那种不相信,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不相信的是什么。“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个卑鄙者是谁,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都以为他说的很清楚,实际上他通过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了这种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地说出来。当然这也是朦胧诗被叫做朦胧的意思,朦胧诗当时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认为这个不是诗,没有人说过朦胧诗不是诗这个话,这是非常重要的,都是说它是什么意思?它在暗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朦胧?他的狼子野心是什么?批判朦胧诗都是这么批判的,它是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情绪,象征的方式。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朦胧诗的鼎盛时期,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结束是第三代的鼎盛时期,89年是个标志。第三代的成分非常复杂,不能以年龄来划分,比如她既有象我这样50年代中期出生的,也有象伊沙这种,他虽然不能算第三代,但他一直受第三代的影响,是广义的第三代。第三代首先是四川的一本文学刊物,叫做《现代诗歌内部资料》,在这个刊物中有一句话: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诞生的第三代人。第三代的特征不是口语,是一种自由的大家一起揭竿而起的阐述。第三代既有我的这种风格的写作,他们风格;也有非非的,那种受到罗布格里耶写作方式影响的;也有四川的整体主义诗歌;也有上海孟浪他们的撒娇派,同时崛起的就有50多种,还有云南的还魂主义,可能你们都不知道。第三代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虽然语言方式不一样,对文革时代假大空的文化、英雄主义、假的人格力量的反感,共同的反感,而不是一种共同的美学,大家都有一种要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状态这种倾向,当时出现了一大拨儿的诗人。pass北岛,不是我们提出的,pass北岛是程卫东提出的,程卫东是浙江人,有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在报纸说出这句话,我们从来不说pass北岛,那时候我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北岛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一个延续过来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开始。一个局外人,一个不写诗的人,突然乱说了一句,在混乱中乘机乱说,大家就说“哦,好、好”就跟着说,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什么第三代嘛!我的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就是说我的口语就是我于坚写的,后来我们为什么都跟着说我们是第三代?是为了表述方便,表述那段历史没有一个合适的名词。我们就干脆用这个算了,但是同样的名词也很多:后朦胧诗,后新诗潮等等。第三代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诗人,但她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是知识分子后来延续下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在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的一本《青年诗人谈诗》,那个上面欧阳江河、海子都纷纷发表他们诗观,那种诗观直接了当地说就是跟着杨炼写史诗,受杨炼、江河的影响,这是他们的老底、渊源,他们现在不说这一点。
伊:有三个人这样讲:海子、骆一禾、欧阳江河。
于:实际上杨炼写史诗是当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寻根文学,韩少功、阿成这几个人搞起来的,杨炼跟了一把而已,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诗歌唯一一次落在小说后面的就是杨炼了。
黄:他们怎么能被误导呢?我读杨炼、江河的东西,八八年读,我就觉得没有诗味呀!我不知道他们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误导呢?象海子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误导呢?
唐:当时他们的东西还是很有感染力的。
马:《诺日朗》当年还是很吓人的。
伊:这个东西有一个大诗人的诱惑,就是要做大诗人就要写史诗。
于:其实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北岛开辟的是“我不相信”,所以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对政治的含沙射影上,忽然这个人出来把诗的方向引领到文化的方向上,但是他的文化也是纸上的文化,是阅读的文化,《易经》、八卦不是空气中的文化,每个人都在写。而且朦胧诗中还有许多软性的东西,黄昏的丁家滩、红纱巾,但杨炼突然来了个“高原如猛虎”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力,但是那种诗还是非常空洞的东西。那个时候也有了搞文化诗的,象欧阳江河写《悬棺》,宋渠宋玮写《大佛》,现在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东西,但是真正文化写的有点感觉的是柏桦,柏桦那个时候写《在清朝》,还有张枣早期写的《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情》,四川这一代人喜欢玩文化的感觉,我觉得他们玩得比杨炼好。这是第三代人的一支,知识的一支,发展到90年代,由中国史文化转向西方的史文化。另外一支,我觉得他们基本是强调要回到生命本身,强调非英雄化,表现普通人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个肯定是以《他们》为主的诗人。那个时代,虽然北岛他们是反抗文革的,但是他们同文革的基本基调是一样的,都是骨子里面都是假大空的英雄主义,都是要玩阳刚之气,都是要振臂一呼:跟我来吧,我不相信。但是忽然一看南方,在长江边上秦淮歌舞的地方,韩东写的是温柔的地方,写的是在被子里睡觉的时候,妻子的手放到他的手上,
伊:还有老婆的拖鞋。
于:还有朋友在背后的厨房给你一嘴巴这些东西,大家突然发现我们的感情开始丰富了。再看到我的《尚义街六号》等等,诗歌回到了人的正常的感觉,不再是振臂一呼的英雄的单一的高音喇叭,而是有那种非常温柔的,柔软的东西,而且诗歌里开始出现了叙述,说的东西更讲究。说也有很多种,大喊是说,细语轻谈也是说,出现了细语和呼喊,慢慢的声音就小下去了,我们就听到了耳语、细语,不再大喊,到了伊沙就是结结巴巴。实际上诗歌的历史也反映这个时代的生理的问题,先是声嘶力竭的那种大喊我不相信,变到那种结结巴巴,中国的声部就慢慢变得正常了,从高音降到低音,低音又回到中音,中音再降到低音,低音又升到了高音,最后就非常正常了,这是一个打开声部的过程。
唐:过去那个像歌剧里的高音一样,实际上口语就像回到了通俗歌曲,用肉嗓来唱歌,伊沙实际上又有点摇滚化了。
伊:实际上也是对那种一味强调世俗生活的反抗,比如什么老婆的拖鞋,就是诗歌也不能就这么下去,实际上也就是反反复复地反拨,相互强调整体才健康,就是诗人也不能是过日子的小男人,一天絮絮叨叨,所以必须有,怎么说,可能每走一步前面的东西给你逼迫的同时,必须对他进行反拨,就是这样的。
于:如果用声部来讲,文革时代是用普通话的独白,就是其他人都没有资格说话,就他一个人讲,然后呢北岛把这个话筒抢过来,文革是站在左边独白,北岛站在右边独白,他们都是普通话的声音,然后到了第三代人,地方语出现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是有方言的国家,不光是普通话,还有四川话、吴侬软语,还有秦腔,那么声音就温柔下去了,小男人、小女人都出来了,到了伊沙,声音又高上去了,就象他说的摇滚。摇滚和朦胧诗不是一样的,实际上朦胧诗的意义只有一种,就是信还是不信,我不相信。到了伊沙这里,诗的意义就无限的广阔了,包括性的意义、生存的意义,母亲的意义。诗歌不能只表达一种非常简单的单调的意义,就是政治上是否正确,要么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这种极其简单的事情。诗歌的意义是非常辽阔的,要给人一种智慧,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不要诗歌要直接回答,最起码要对此有所暗示。这个意义不存在正确与否,而是来自诗人身体对世界的感受。你说伊沙诗里的意义你可能不完全同意,但是你起码可以体验到自由,这个意义可能是你完全不能认同的,但是他可以这么写。这个时候自由就开始出现了,自由不是在政治正确的范围争取自由,我觉得还有更广泛的范畴,自由可以表达这种意义,这种宗教,这种思想是我一个人想起来的,你们都不可能认同,这也是自由,我觉得到了这种自由在诗歌中出现的时候。
郭:两位能不能谈谈对昌耀的看法?
于:1997年我从西藏下来,经过西宁,我在西宁住了三天,我同昌耀也认识,但我没有找昌耀,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诗歌中的西部与我亲自感受的西部相差得太远了,不是一回事儿。
伊:我对昌耀的感觉,首先不说正面负面,
郭:对,对,就谈自己的。
伊:咱们混起来谈,也不要说哪一代人或一个时代的,昌耀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因为你可以回想,他的环境不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具体生活的环境,没有给他任何支持。他在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写出了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些作品,那么如果有一点支持,就是在他们修养里残存的一点支持,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可以说的更明白一点,朦胧诗是得到了支持的,第三代同样也是得到了支持,朦胧诗得到的是政治开进时期的支持,第三代得到的支持更大,80年代是一个文化高度膨胀的时代,是一个诗人可以成为英雄的时代,很多时代的诗人得到了许多支持。作为写作人我理解的昌耀他是最孤独的,我很钦佩昌耀这一点,不要说他比他的同代人优秀,他是唯一的,几乎是唯一的。
郭:我看他就是唯一的。
伊:同代人是一堆人,他为什么游离于这个之外,我认为是他的才华。他认为这种东西就是诗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昌耀的写作在他的生前就终结了,他是没有给大家留下悬念的诗人,也就是说他还有什么可能性,没有了,因为当我看到他写的关于苏联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我认为那个有才华的诗人已经完结。
郭:我理解伊沙的话,就是说从他的艺术表现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是吧?
于:我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昌耀是在他的幻觉中写作的,他的写作背后没有那种可以支持他的写作延续下去的有力的掩体,他的幻觉有几次非常天才的闪光,但是他的这种东西不能持久,我觉得主要是他不和他的生活发生关系。
伊:我觉得昌耀大的思维方式还是那个时代的,比如他的《划呀、划呀、父亲们》。
郭:那个是他83年、84年的作品。
伊:那个还是时代整体的思维。我认为他之所以是昌耀就是因为他的才华,而那个才华是孤绝的,绝对是孤绝的,那个时代是没有第二个同党什么的,就是没有第二个对话者。
郭:那么能不能请于坚老师和伊沙具体地谈谈自己的创作,我觉得我确实对这个感兴趣。
伊:我先不谈自己的创作,你只会谈自己的创作(对于)。我先谈我对青海的感觉,我要提到马非。刚才说昌耀和青海的关系不是肉身的关系,是幻觉的关系,实际上他对现实是恐惧的,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来,他对具体的现实是恐惧的,而且是回避的,是想象中的现实,想象中的西部,西部丰富了他诗歌的质地,这个质地在当时的中国非常雄性,也非常独特,实际上这跟他的生活现场都是有距离的。在我想象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成就诗人,没有哪个地方先天的更好,或巴黎或纽约更好,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有的地方成了,有的地方没有,我想是具体的诗人没有利用这个地方,昌耀算是一个成功者。我觉得马非也算是一个成功者。为什么这样讲,马非的诗歌从青海这个大环境逼迫他不得不陷入一种孤独的情绪里面,如果你麻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要正常的话,要敏感的话,那么这种孤独最终你会体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肯定是一种非常慢的,非常个人化的,非常背对大家的行为,所以需要一个人把自己的时间放在里面。昌耀证明了这一点,马非也证明了一点,而且他还能证明一点,青海的诗歌未必就一定是非时尚的,我认为马非的诗歌很时尚的,我喜欢时尚的东西,我说的时尚是在一个变革的国家里,你要对时代的微妙变化,环境的微妙变化作出反应。
于:他的意思是马非的诗歌并不意味着青海的诗歌是在世界之外的,是与世界没有关系的地方,恰恰是马非的诗歌让我们感到青海置身在世界的核心,他的诗歌比起中国内地的那种时尚诗歌一点也不逊色。
伊:否则那是不真实的,因为青海每天也在造楼,大家还在、新一代人还在象昌耀那样把青海变成一个概念,青海就是大漠,就是巨石,诗歌就没法前进。以我有限的阅读,我觉得青海的更多的诗人陷于了一个试图在昌耀的道路上前进,但是无法前进的困境。
郭:青海的许多诗人确实是陷入了昌耀的语言圈套。
于:你讲的这个还不只是青海,我觉得中国的边缘地区,比如云南、青海、贵州、西藏的诗人都有了这个特点,他们都在虚构自己生存土地上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我也是生活在一个边缘的外省,实际上我的诗歌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在云南写的,这也是马非的诗给人感觉,他的诗好像不是在青海写的。
伊:在这个话题上就等于谈他的写作了,你比如说在他的写作里可以表现那个永恒的云南,比如群山,所谓南高原系列的云南在他的诗中呈现了,变化的云南,变化的昆明,现代的城市也能呈现,这就叫丰富,真实的全部现场。那个云南的群山就是不动的,一千年、一万年就是不动的。在马非的身上看到了,我在很早就说过一句话,甚至马非在还没有写出更大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新疆诗人的作品,他们老是天山什么的,就是西部,包括整个西部,陕西就非要是窑洞、黄土高坡、婆姨,甘肃就非湟水、敦煌,甘南的藏族什么的,我觉得实际上西部陷入了一个圈套。我当时说,真实的新疆诗人绝没有住在天山脚下,他就住在乌鲁木齐的一个跟我一样的寓所里,说不定比我的更人间烟火。所以我就怀疑这个诗歌是不真实的,你看那个沈苇,他就想成为一个新疆的昌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马非好像就是掉头而去,就像他站在昆明掉头而去,他反而我觉得倒是将来能够成为和昌耀一样有成就的诗人。
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西宁也可以写最时代前沿的诗歌。你说新一代的70后,象沈浩波他们在北京这个地方,尹丽川他们跟酒吧写作关系最近的环境,当他们想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现马非早已写过了,一个青海人早写出来了。在我们谈到青海诗歌的时候必须回避的一个误区,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于:中国当代文学我觉得她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她因为她把少数民族文学当作一种特例来运用。实际上,我认为文学不存在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文学就是文学。
郭:只有好的和坏的。
于:而且一个作家我觉得他自己的世界,而且我觉得他自己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作家是在世界之外,包括鄂伦春人和爱斯基摩人。福克纳就是最好的例子,福克纳在世界之外,实际上它是一个世界作家,他一生都住在邮票大的地方。反过来,我可以把卡夫卡看成是一个爱斯基摩人,因为我觉得他写的就是爱斯基摩人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认为卡夫卡写的是世界核心的事情呢?你完全可以想象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爱斯基摩人写的,没什么问题。中国西部的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跟49年以来的文化有很大关系,老认为文学是分为少数民族的、汉族的,实际上我认为少数民族是不是意味着文学标准能够降低,一种照顾,这就影响了许多诗人,认为我是少数民族,我就必须写中国所谓西部,就是一种固定的大概念,所谓鹰啊、草原啊,我觉得其实上这是一种最表面的东西。
伊:就是说当一个诗人这样想的时候,他就自卑了,就是说我要取长补短,就是说我要发挥地区优势,他自己自卑了,他已经把自己打入另册了。一个弱省的省长可以这么想,这是一个政治思维,一个群体思维。
于:对,这个是地缘政治的思维,我的特产是什么,我的经济优势是什么,这个不是诗歌的事,诗歌不是这种东西。哪怕那个地方只是水泥厂,盛产的只有水泥一样,你牛逼,你也可以成为一流的诗人。哪怕你就住在那个地方,转过来看见的是狮子,翻过来你看见的是玫瑰,抬头看见的是上帝在上面,你是傻逼,你还是傻逼。
伊:这个话题不光是对青海写作的人,对整个西部的写作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在西部写作的人。
郭:刚才伊沙提到了马非的写作,谈到了一个时尚,就是我们在一个不时尚的地方,落后的地方,也仍然能写出时尚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时尚的作品不一定意味着是好的,我觉得象于坚的作品,比如《哀滇池》那些诗,我非常喜欢,但我从来不把他当作时尚的东西。
伊:我的时尚不是时装杂志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要勇于向前,不要恐惧向前。
郭: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向前有的时候也意味着向后,就是勇于后退,我的意思。
伊:对、对,因为这个话已经被于坚喊出来了,勇于后退,所以我就要喊勇于向前。因为前面还在发生,还在不断地改变,不是说大家现在都为止了,中国就这样了,一个稳定的中国,不是这样的,关键是在西宁这个地方你强调是向前还是向后,在西宁这个地方你还强调向后吗?
郭:昌耀去世以后,他可能对60年代的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们70年代的诗人不是这样的,阅读昌耀,马非有马非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各走各的道。
于:我觉得伊沙的话可以这样理解,向前向后是诗人自己的一个调整,自己的事情,自己调整自己。你这个诗人肯定有一段时间会向前,有一段时间会觉得他在向后,唯一的目的是你的作品大家看见后会觉得怎么样。
伊:我的意思是你要勇于表现变化。
郭:这是每个诗人必须得追求的。
伊:不要把表现变化的特权交给沿海城市,这对青海是一个问题,这也是对我的一个问题呀。我从北京回到西安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我前面有一个人叫岛子,他是东北的,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写大兴安岭、森林什么什么抒情曲,他一回到西安他就钻到八卦里,他就恨不得跟兵马俑住在一起。他写不出兵马俑的,我的意思是这个,你不要省长思维,什么地缘优势,我的意思是这个。
黄:于老师刚才说昌耀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虚构,这种生活不是我的感觉。我和他原来一起在劳改农场呆的,我就没有他诗中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的这种东西是虚构的,他的身体跟我的西部没有发生关系。
伊:起码有一点要说一下,因为关于昌耀的生活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尤其在他死后听到的更多,那么在他诗中你看到他和他老婆之间的冲突了吗?你看到的只是他爱一个土伯特女人什么的。
韩:这是他的早期作品,当时他确实和他老婆感情很好。
伊:对,早期你相爱你表现了,冲突为什么就看不见了?
韩:我觉得这只是诗人一个选材问题。
伊:绝对不是选材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昌耀承担了过多生活的个人压力,他对这些东西是回避的。
韩: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曾经在诗集《于坚的诗》的后记里说:“作为人类的一员,诗人在我们中间。如果诗人也死了,那才是真正是世界的末日。”在这里,你把诗人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你能不能谈谈诗歌对人类究竟有什么意义?
于:简单地讲,20年前我们崇拜日本的产品,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到中国来,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如闻天籁,真是了不得了。而20年后,中国人已经不买日本的产品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产品比他们的还好。那么说明什么了,就是你经济、贸易、科技方面的领先是可以依靠时间解决的,只要这个民族不怎么笨,他总有一天可以超过你,和你平起平坐。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诗,这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人代表她的智慧,这个是无法赶超的。中国有李白有杜甫,你日本就是花一千年、一万年也造不出一个李白、杜甫,我可以造比你更好的原子弹,但是我造不出松尾芭蕉来,这就是诗对一个民族的作用。诗是在文化领域、经济领域唯一不能替代的,她代表着这个民族智慧的最高点,诗人是不能通过时间来解决的,绝对和一个民族的传统、独特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我们为什么会说某个民族很牛逼,为什么会对某些民族不在乎,可能这个民族科技很发达,但是那个民族没有诗人。我们尊重一个民族,是因为她的语言被少数人表达到最高的境界,而且这个境界不单是这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语言如果都进入这个境界都可以感受到的,她是可以让一个翻译家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就是因为她有这种伟大的诗人存在。诗歌是文明的光辉,提到意大利我们会想起但丁,提起英国我们会想起莎士比亚、济慈、雪莱。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人类学家到非洲,把非洲人当做动物一样,把你的嘴掰开,给牙齿照相, 纯粹是制作标本 。英国的一个人类学家到昆明的时候,我问过他:你们19世纪到中国来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象对待非洲人那样把中国人当成一个毫无人性的标本?他说,不敢,他们只是在旁边旁观,照一些照片。他们不敢这么对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民族是有文明有文化的,只是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诗歌主要是表现在一个民族为什么要尊重另一个民族,绝对不是在尊重她的武器、科技力量,而是尊重她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不仅是本民族的,就是另外一个民族的人读到这种话语,他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是值得我活下去的。”科学技术、经济它表达的永远是地方性的知识,诗歌表达的永远是全 人类的知识。伊沙的诗在瑞典朗诵时,我坐在旁边听,我觉得那种掌声和我在北师大听到的掌声是一样热烈的,他的诗是先译成英语,再通过英语翻译成瑞典语的。诗歌节结束的时候,那些人对中国人肃然起敬,我们好象成了一个团队似的,象奥林匹克,那种胜利的,以至于到了他们要求我们一起唱一支中国歌的地步。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尊重汉语,他们发现汉语不是随便说着玩的,不能蔑视。汉语不再是摆在客厅的花瓶,而是一种反应,一种肉体真实的反应。你去西方不能永远背着一颗原子弹说我造的比你大,不是的,我们在包包里装上一片纸,就可以征服他们。
韩:还是在那篇后记中,你说诗人之光直指人性,你认为什么样的诗才是直指人性的诗,什么样的诗才可以直指人性?
于:我觉得有很多的诗你可以去读,李白杜甫的诗我觉得都是直指人性的,伊沙的不少的诗也是直指人性的。人性不是抽象的概念,直指人性,我可以这样说,但具体到每个读者的人性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觉得这首诗击中了你,他可能觉得那首诗击中了他,这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诗人他的诗可以触动很多人,但是我不认为只能感动一个人的不是诗,我不这样认为,成千上万的人觉得好的诗才是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人性是非常具体,有时候这首诗我就是写给我老婆的,全世界的人只有她感动了,我觉得就够了,真的就够了。
韩:我个人感觉,从你早期的诗歌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境,比如说《横渡怒江》和《尚义街六号》,即便是长诗《飞行》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你是如何把握的?
于:这种情况呈现的是建立在诗人内部的矛盾,真正诗人的矛盾是内部的,矛盾的关系来自于生命的复杂性,诗人只能通过语言呈现不同的内部层次,呈现的越多越复杂,就越好。进入村庄的道路不止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可能习惯从这条路进入村庄,他可能习惯从另一条路,但不表示只有一条道路才能抵达村庄的内部。最可怕的是一个诗人只有一条金光大道可以进入,让人们欢呼而过,这是最可怕的。
韩:在《诗人何为》一诗中,伊沙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写诗为上”,你是否觉得这个答案真的就能够回答这个显得有些沉重的问题?
伊:我首先介绍一下我写这首诗的背景,诗人何为,是荷尔德林提出的问题,在90年代很多中国诗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办法写诗的趋势。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只要你写作就总会有新问题出现,你必须要穿过去,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甩过来的问题,我可以不经历荷尔德林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的诗人不是对诗歌与社会关系考虑的最清楚的那个人。诗人注重感觉。在诗人写作行为发生前、完成后你是思想家,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艺人,只是一个艺人,所以还是写诗为上。
韩:通过和你的交谈,我觉得你的书面语言比你交谈中使用的口语还要口语化,也就是说你的书面口语和你的口头口语是不一样的。
伊:实际上,你听到的并不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如果在家我跟我老婆这样“因为……所以┈”的说话,我老婆早就跟我离婚了。当然在写作中我必须用最纯的材料,去除语言中的结石,也不是裹着哈拉子的口语。可能为了写作你准备了一吨的材料,但最后使用的也只有几句。
韩:你为什么会把口语作为你的写作语言呢?
伊:因为这种语言与你的身体相通,是生活中就发生的语言状态。
郭:近几年看,于老师和伊沙在体裁上也都进行了扩张,于老师的散文非常出色,伊沙也转向小说方面发展。于老师让我感兴趣的还有摄影,我记得是不是有一家出版社还为你出过一本关于摄影的书,除昆明老房子外。能不能现在把诗歌放在一边,谈谈其它体裁,也就是副业。
于: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副业,一个农民他要把稻子、谷子、玉米都种好。如果一个人光种稻子,不种谷子、玉米,他在村子里是没有人能够看得起的。为什么有的人是富农,他就是把稻子、玉米、谷子都种好的人。我就是那个富农。
伊:现在这个时代对诗人的素质要求很高,要求必须具有全面的素养。“副业”是素质全面的产物,我的“副业”是言说,我可以不注重言说的质量,因为这是为诗歌准备的素质,我的言说只是素质带来的副产品。我是一个艺人,我觉得我的副业只能走向小说,因为小说与诗歌有相似之处。在同一时间内,我的诗歌和言说总有一个是二流的。我必须保持整体的自信,局部的警惕和怀疑,尤其是对思想。
备注:凡文中加小括号的部分是整理者根据谈话者的意思加上的 ,加中括号或下面划线的部分是在录音中未听清,无法确定的部分。
转自诗生活伊沙专栏: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art&id=38011&str=1268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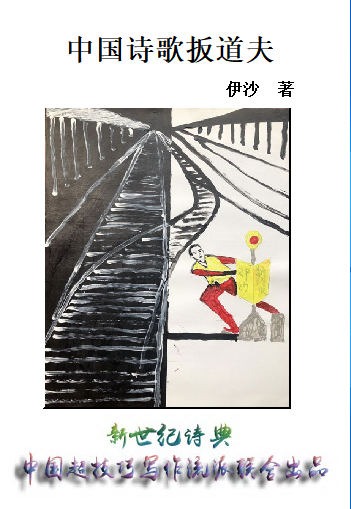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