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专论《伊沙这条“老狐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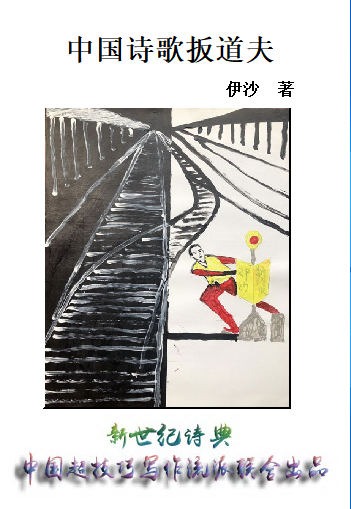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在整个90年代中,伊沙可能是被谈论得最多的诗人,无论是诗歌艺术方面还是世俗层面的影响,都不容忽视,然而好话坏话都为人说尽,我再插嘴,也说不出什么新意,因此也可以说,现在这篇文章是勉为其难之作。
大多数70年代初期出生的诗人是在1990年左右接触现代诗的——虽然有少数人80年代末期就开始写作,但那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涂鸦”,师傅不是席慕容就是汪国真——因此对于这一拨诗人来说,伊沙和“第三代”同时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尽管伊沙在“诗坛辈分”上比“第三代”小一级。这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伊沙的一大荣誉。但伊沙并不是“第三代”和“70后”或“中间代”(为了方便叙述,姑且用这个命名)的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甚至不是什么“代”什么“后”,套用他的诗,是“我是我自个儿的爹”。他像90年代诗坛的一块挡路石,虽不特别粗壮,但棱角分明,无论你是否接受它的面目,都能让你过目难忘。
伊沙的诗歌是“第三代”中韩东、于坚、李亚伟那一路的变种,坚持了反文化、反崇高的价值取向,接近日常生活的本真而多出了“身体”。80年代末的《车过黄河》有了隐秘的暗示,90年代初的《关于春天的命题写作》,“姑娘们露出了小腿”,《孤独的牧羊人》开始“少儿不宜”,不过之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见伊沙还是很清醒地把握着一个“度”的。这是伊沙较“第三代”高明(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堕落”)之处,也使伊沙理所当然地成为某些“70后”诗人最直接的“大哥”。
对伊沙诗歌最直观的印象字里行间充斥着的尖刻的讥讽、放肆的嚎叫、无所谓的嘻笑,他喜欢用文字干涉读者的神经,要你尴尬,要你哈哈大笑,要你暴跳如雷。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方式。某些诗歌砌满了华丽而优美的辞藻,通篇形容词,内容也不乏“春天般的温暖”和春风般的清新,但你读后总感觉诗人在做秀,它给你触动却不能让你思考。伊沙的诗不美,字句瘦骨嶙峋,甚至有些丑陋,但能够不容阻拒地刺入你的感觉甚至内心深处。两种诗歌让我想起了两个词,“春风扑面”,“寒风刺骨”,前者虽暖,却只能“扑面”,而后者给你一种直达骨髓的寒意。因此伊沙的作品既浅又深,浅在字面上,深到骨子里。它们融合了冷峭、尖刻、辛辣等因素,而幽默是基础。伊沙的确懂得逗乐,有的作品让你会心一笑,有的让你捧腹大笑,但更多的是让你笑得比哭还难看,笑出了眼泪,或者想笑也笑不出来。即使是那首“哈哈大乐”的《假肢工厂》,人们也不会觉得里面有什么玩笑的成分。这种幽默很阴冷,这是因为作者洞悉了假幽默的存在:“现在有很多假幽默的人,把‘幽默’当作行头穿在身上。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某某很幽默,会讲黄段子。我就很怀疑她说的某某是否真的幽默,因为据我观察,大部分讲黄段子的家伙其实一点都不幽默——因为缺这个,所以只好借助黄段子来显示一点什么。”(《伊沙VS赵丽华》)而“真正的幽默是很高的指挥和很真的性情在日常状态下毫不经意的自然流露”。(同上)在这里,伊沙给出了一个标准,读者完全可以依照这个标准去抽查他的作品。自然,抽查的结果不会完全合格,理论可以指导作品,但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优秀。连伊沙尚且如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那些自以为幽默其实仍然是黄段子和调皮话所组成的诗歌的大行其道了。
在我的朋友中,对伊沙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状态,有的佩服地五体投地,有的则不以为然。我相信伊沙对这样的反应不会惊讶,如果说《地拉那雪》中的伊沙尚未显露出“叛臣”的野心,那么从他写下《车过黄河》起,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与众不同。此后的伊沙不再是带着淡淡的感伤的抒情青年,而是以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饿死诗人》)的形象站到了抒情的反面,或者说,是站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的反面。《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结结巴巴》、《饿死诗人》、《狮子和虱子》等作品巩固了伊沙的这一形象。有人认为伊沙是中国后现代诗歌的肇始人,因为他的诗歌里具有许多“后现代特征”。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文学史家干的活,作为一个读者,我不关心诗人的“历史定位”而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作品上面。我自顾自地把伊沙当作思想者,在一篇文章里把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孟浪等人合在一起讨论,尽管他似乎很“讨厌”这些“知识分子”。
伊沙的诗曾经是独特的,难以复制,但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变,一些更年轻的口语写作者正在“蚕食”、复制着伊沙,几达以假乱真的地步。当然,这与真正的伊沙无关,何况那只是表面上的“像”,邯郸学步者永远无法掩饰住骨子里的孱弱。后来者的模仿和复制也像一条鞭子,不停地驱逐着伊沙创新的脚步,因此,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担心的是伊沙的自我蚕食、自我复制或者出现“变异”状况。他的长诗《风光无限》中的一节曾被诗人赵丽华盛赞:“我记得你写马克思那首,燕妮不在家,他乘机‘把女仆按在地板上/这算不算/一个阶级/在压迫/另一个阶级’。我想如果单纯写把女仆按在地板上而没有后面的两句,‘勇敢’是够‘勇敢’的。但充其量也就是一首‘下半身’了。但后面的两句一下子就扎到穴位上了。这就是巴乔那种在球门前的丰富想象力和致命一击的能力。”(《伊沙VS赵丽华》)我却不这么认为。它的想象力虽然“丰富”,却是虚空无倚的而不是基于现实生活,这一假设多少有些无聊和无事找事。从诗艺本身的角度而言,前边的铺垫和后边的总结,也给人“主题先行”、故意设置“诗眼”的嫌疑。因此,它充其量是“扎到”环跳穴、笑腰穴之类让人一跳一笑的“穴位”,而不是什么“致命一击”。我特别反感那些前边大肆渲染结尾小作总结或点题或升华的作品,作为一首诗,我希望看到的是整体的智慧而不是局部的亮点。这是我和某些诗人的分歧。另一个值得警惕的方面是,伊沙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有一种“快感繁殖功能”,读之很顺,很有感觉。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快感只是一次性的,“不能复制”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比如《告慰田间先生》。
我和伊沙有过两次见面。第一次是在2000年8月上旬的西安。见面前,我听到过太多关于伊沙的传闻,诸如嗜酒如命、放浪形骸之类,还有瘾君子,患艾兹病什么的,总之与当年美国那些“垮掉派”差不离。因此见面之前我有些忐忑,生怕闹出个不欢而散。孰知见面之后,印象大好——原来传说中的“黑道煞星”竟然是一个豪爽、讲话大声且自信得可爱的胖子!那次见面最令我意外的是伊沙竟然因为胆不好而不能喝酒,按照作品中的印象,这厮的胆子应该好到不仅能喝酒,就是吸毒也不过分的。当然,我也看到了他泼辣的一面,在与同城的一个相对传统的诗人一起进餐时,伊沙的话里常带些刻薄的调侃,弄得我总是担心那个诗人无法忍受而离席而去。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在由诗人吕叶主持的“90年代汉语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上见面。在那次诗会上,伊沙仍然是个“焦点”,但我更怀念会后一伙人横七竖八躺在房间里谈天说地的时光。
伊沙是个多面手,身上的“刀子”不止诗歌这一把。他的随笔读者比他的诗歌读者只多不少,他还写过不少小说,做过杂志,从2002年开始又到电视台客串节目主持人,据说干得还不错。英国思想家伊塞亚·伯林曾有“刺猬与狐狸”之说,“刺猬”专一而“狐狸”多能,两者各有长短。以此对照,伊沙无疑是一条“老狐狸”。
转自诗生活伊沙专栏: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art&id=15573&str=1268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