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季羡林对新诗的判断太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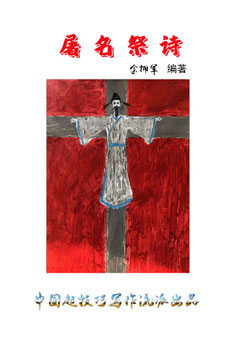
周伦佑:季羡林对新诗的判断太草率
混乱是当今文学的基本特征
周伦佑:季羡林对新诗的判断太草率
信报记者 王明明
一年初始,万象更新,刚刚度过90诞辰的中国新诗迎来了新的一年。
在诸多纪念活动中,诗人们在争论:评价新诗有没有标准,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新诗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普通人却说,“新诗让人看不懂”;甚至,季羡林先生丢下一句狠话,“新诗很失败 ”。
周伦佑,新诗重要流派“非非主义诗歌”创始人之一,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非非”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又是学术意义上的“非非”的理论源头和创作之源。
在记者面前,周伦佐是一个老头儿,55岁了,花白的头发,朴素的夹克,有些黄的脸,笑起来很有些皱纹。甚至,不久前,为了写一首长诗,他吃了好多天的方便面,得了900多块稿费,“生活的十字架”依然沉重。
写诗不是为了让人看得懂
《时代信报》:有人说,新诗让人看不懂,你怎么看?
周伦佑:懂与不懂,从来不是一个诗歌理论问题,甚至不是诗歌鉴赏的问题。因为诗歌从来不把通俗易懂作为自己的美学标准。
例如《星星》诗刊上的诗歌,基本上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写作手法和表达技巧,是不是好诗另当别论,但普通人是应该能够读懂的。
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因被人指为“看不懂”而著称,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现在很少有人说朦胧诗看不懂了。这是一个审美观念的问题。然后是第三代诗歌,我基本上没有听说有人看不懂,因为他们都是很口语化的。
而现在“流行”的所谓“废话诗”、“梨花体”、“下半身”的诗歌根本就不存在是否看得懂的问题,而是太口水话了,太看得懂了,因为那已经不是诗歌了。
《时代信报》:“看不懂”是不是表达了普通人对诗歌的一种抗拒?
周伦佑:我前面说了,“看得懂看不懂”,从来就不是衡量诗歌的一项美学标准。诗歌不是为了让人看得懂的。诗歌阅读的过程是与诗人的对话,注重的是感受和体验,是从诗意和词语的张力中获得一种阅读的新奇与快感。诗歌就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诗兴、诗意,一种词语的张力,一种阅读的快感。普通人能够在诗歌阅读中获得点滴的启示,就够了。
新诗一生下来就先天不足
《时代信报》:中国是诗的国度,国人从小读唐诗宋词,但现在大众很少去读新诗,你怎么看?
周伦佑:新诗的历史不到一百年,在文体形式和观念形态上都不成熟,它的艺术性永远达不到唐诗的高度。
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阅读方式、审美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它对国人精神的影响是深入血液和梦境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可以说是诗歌的历史。
而新诗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一生下来就先天不足,它与中国本土语境的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它在不断成熟,比较中国化了,但还没能超越传统的唐诗宋词。
我不主张将新诗神话,不应该将它的艺术成就无限抬高。
《时代信报》:那新诗是不是就没有前途?
周伦佑:新诗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出现,适应了中国社会转型和变革的需要,并已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要想倒退或者取消都是不可能的。我的主张是,旧体诗传统继续伟大地存在,新诗要在文体建设上更趋成熟,在观念表达上更加本土。
与旧体诗相比,新诗更适应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和情感方式,更适合现代人思想表达的需要。再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新诗将会确立自己的经典与传统,将会拥有更鲜活的生命力。
必须重建诗歌批评标准
《时代信报》:前不久,季羡林评价新诗,说“新诗很失败”,你觉得呢?
周伦佑:季羡林大概很少读新诗,估计也读不懂新诗。这位老先生经常说一些不负责任的大话、空话。他对新诗的这种判断是没有根据的,起码是轻率的。
《时代信报》:不久前,陈仲义提出评价好诗的标准是“感动、惊动、撼动、挑动”,引来争议。有人说好诗没有标准,也有人说“四动说”是废话。你怎么评价?
周伦佑:陈仲义是一位严肃的诗学理论家,他的这种努力是想为现代诗重新建立批评标准和尺度,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现在诗歌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批评的标准和尺度,包括“梨花体”、“下半身写作”以及季羡林的“新诗很失败”,种种乱象都是因为诗歌失去了标准和尺度,完全不知道怎么评价和如何讨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虽然“四动说”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还可以探讨,但陈仲义重建诗歌批评尺度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在我看来,他也是能担当此重任的人选之一。
混乱是当今文学的基本特征
《时代信报》:你怎么评价现在的诗歌界?
周伦佑:现在的诗歌界确实混乱。混乱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诗歌界的混乱则是社会转型期商业化、欲望化、娱乐化冲击的结果。中心溃散、价值颠倒、诗人静观、小丑登场,许多人都想乘浑水摸一把,于是有了混乱的场景。
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混乱正在澄清。坚持严肃的诗歌精神、关注和介入当下现实、关注底层民众、拒绝商业化、拒绝娱乐化,这样一种写作倾向,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方向性的潮流。君不见,连恶俗的“下半身”写作者,也在改变自己的形象,转而提倡所谓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吗?而“深入骨头与制度,介入当下现实”,是非非主义早在1992年的“红色写作”中提出来的。
《时代信报》:刚才你提到1980年代,你似乎对它情有独钟,回过头去看,你怎么评价当时和现在的文学界?
周伦佑: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至今我都对那段时光有割舍不掉的情怀。1985年,我和哥哥周伦佐到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举行讲座,学生挤爆了礼堂,进去不了的学生甚至用收音机在礼堂外收听同步广播。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对知识、文化的热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和人生轨迹。
80年代的文化精神点燃了人们心中理想的火种,这种希望至今未灭,给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想起来我都热泪盈眶。
而现在,由于社会的转型,商业、消费和娱乐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使这个时代成为了一个欲望化的时代。道德解体、价值崩溃,文学也跟着“失范”。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的痛苦更多一些。但是,我也相信,随着转型期的结束,一切都应该重新走上正轨。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学会在“失范”之后重新建立标准和规范,时间大概需要20年。
《时代信报》:你似乎非常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娱乐化和快餐化?
周伦佑:文学和商业化历来都是矛盾的,更不能被娱乐,文学是灵魂的事业,灵魂能市场化吗?我觉得,诸如郭敬明、韩寒这些快餐化的商业写作根本算不上文学。文学应该保持它对人的心灵、精神、灵魂以及现实生活的关照。
网络会使作家变形
《时代信报》:朱大可经常利用自己的博客发表对于文化事件的看法,可网络上却很少看到你的言论。
周伦佑:朱大可是个有才华的批评家,他写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文章是我所喜欢的,我曾从文体的角度给予过推崇。但他当前的写作,有传媒化和网络化的倾向。
有人说现在的朱大可走的是时尚精英之路,他经常现身网络和媒体,有作秀的嫌疑。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他太在意传媒和网络了。曾有一家媒体记者也向我提过同样的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像朱大可一样,把自己的观点,跟时尚的元素结合起来,通过大众媒体来表达?我表示了拒绝。我认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不应该跟网络有太多的关系。传媒与网络会诱惑和改变一个人——直至使其变形。
《时代信报》:你似乎很不喜欢网络,可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网络的出现使信息传播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周伦佑:我会使用电脑,也会用到网络。但我认为,网络只是一个了解信息和传输信息的工具,不能太迷恋它。网络以及它所产生的文化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混乱的表征:虚无、平面、耗散、膨胀,你看现在许多污七八糟的东西不就是通过网络搞得沸沸扬扬的吗?
“非非”也有电子版,但是我们坚持在一个特定的圈子内传播,而且主要是依靠纸质的内部刊物在发行,我们之间的讨论也基本上集中在这样的纸质刊物中。
《时代信报》:这不就成了圈子内的文学?
周伦佑:严肃的文学本来就是通过一个圈子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学进程的。文学什么时候成为大众的了?严肃文学的小众化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在国外,严肃文学有专门的出版社和特定的发行对象和渠道。我想再次重申,严肃文学一定是拒绝大众媒体和网络的,只有这样,文学才能保持它的精神性和纯粹性。
点评重庆文学
有点跟不上趟
《时代信报》:你怎么评价现在的重庆诗歌?
周伦佑:虽然我对重庆诗歌的现状了解不多,但我认为城市建设上现代化的重庆在文化上还比较淡薄,在文化观念上比较落后,比较体制,有点跟不上趟。如果把文学创作比作一辆火车的话,很多人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经先后到站下车了。
当前的重庆文学气势较弱,可能和许多诗人外流有关。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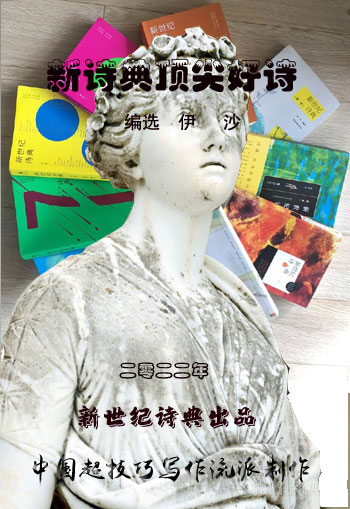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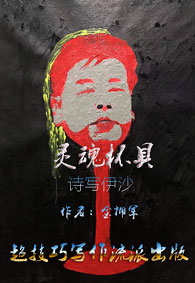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