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要说》(2014年之一) 伊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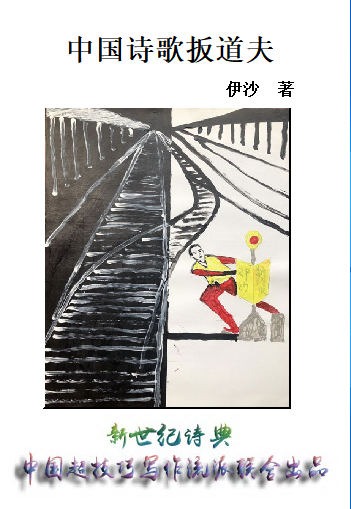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有话要说(2014年之一)
游若昕写的不是“儿童诗”,而是现代诗。《新诗典》没有儿童组,只有游若昕。
五四译风及其遗风,就像什么都要撒糖精——哦,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那玩意了,换个比喻——就像本帮菜,爱加糖。译大师,什么都别加,清炖,因为材质超好!
译作虽多,不过是“准资讯”的水准(准确性还大可怀疑),唯有我和老G(不加之一)达到了“译品级”(恐怕绝大多数译者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吧)!
来自敌营的总结《论《新诗典》为啥成功》,很有道理,留句话:不服者可以团结起来搞一个嘛。
《新诗典》最根本的就是天天好诗。
女人的特点就是善于发现可以插上一朵鲜花的牛粪。
在过去一年中,进入大学课堂不再是少数诗人的特权。凡我过处,不再是旧风景。
对《新诗典》来说,不主动投稿,等于自我放弃,更不要有怨言。再说一句得罪女诗人的话:你们与诗无关的心思容易比男人多,假男人除外。请大家记住:诗内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诗外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奖是个屁,这都是新世纪以后沉渣泛起,泛娱乐时代的症候。
我一年的成果顶我同事一辈子,可我年终考评是“合格”,他们是“优”,如果你告诉我这世界是公平的,我立马搧你脸,但好在我境界提高了,不拍桌子了,不指着鼻子骂人了,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回答:没有。单位如此,诗坛一样。
回想当年创办《创世纪》的过程,只剩下一个字:累!创意不难,说服人难!
横鼠犯了一个攻略错误:想以经常骂我吃利息,却被拖入泥潭。昨日听到久违的沙龙的消息——我的偶像提醒我:绝不放过一个邪恶的人,哪怕他已变作老鼠。
感觉李异不用想象,满脑子是画,当同代人还把文青当范儿的时候,李异直接做了艺术家。
长安诗歌节的照片都像地下电影——这一次是夸。
在中国做事情,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喽。所以,一定要有抢做意识。新老诗典,无不如此。
一方面女人是非多,一方面女人容易在男人之间引起是非。
这是从发诗到发照片、小档案间隔最长的一次,有原因:电话通知我到小区外的小肥羊门口取快递,我知道是《来自时间的大海》到了!现在它就在我手边,但我舍不得打开,知道无比惊艳,很久没有这样了,像面对处女作!我总是善于鼓励自己,而蔑视打击,遂成打不烂煮不熟的铁蚕豆!
千头万绪,复杂不过人心,如此而已。
看看《新诗典》三届获奖名单,绝大部分都是相对较少甚至从未得过奖的诗人,让我有一种替天行道替诗行道的欣慰和快感!
答横鼠:一、人不会跟老鼠比长相。二、屡创奇迹的翻译大师不会跟只会把湖南话译成普通话的外语盲讨论翻译。三、中国诗坛的“邪教”傻逼都知道是哭庙党,你在队伍尾巴上吹喇叭,《新诗典》最准确的定位是“航母”,你哭死也没辙。四、草泥马!
给横鼠伤口上再撒把盐:从《新诗典》跳出来看一下,理解了横鼠之流的愤怒与绝望:风景这边独好!其他地方事倍功半,意不在诗。
只要犯贱,随时打击,我崇拜沙龙(绝非曼德拉),以恶制恶。
我数度写歪诗咒国宝,我有罪。
用累累硕果砸死无能鼠辈=伊沙30年。
吴雨伦复制了我的声音,给来电话的老友们经常带来错乱,很欣慰!
在过去一年里,在我课堂上被讲评过的《新诗典》诗人将近两百,我相信超过以往出现在中国大学的当代诗人数倍之多!又一件伟大的事情默默完成——从点上击破!从个人做起!
读稿体会:中国诗歌,阳盛阴衰,健康极了!个中道理,仔细思之,竟然想起一句球评:别人把足球当游戏,德国人把足球当战争,岂有不赢之理?
接了一个活儿,是我此前从未涉足的领域,不为别的,只为鄙人“为《全集》写作”的理念,《听伊沙讲课》修订暂停一周,也许不需要这么长。
一专译,一泛译,均达极致,这不是得让横鼠死两回么?
无争,本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之类的自造问题。
湖北丑八怪,放过多少屁,却写不出一首好诗。中国诗坛有个现象:越没文化越爱造说法,臭诗人老一付真理在握的样纸。
快20年了吧?中国诗坛有一个越来越重的关键词:北师大。
有一次,我对首师大教授、著名诗评家某某某说:贵校搞了那么多活动,为何学生中不出诗人?对方一言不发,对我很有意见。
所有问题处理完毕,过去一年,课堂上讲读《新诗典(第一季)》,编选推荐第三季,刚才又回头看看第二季,感受有点小复杂:一、三本很不一样且越来越好,作为编者太高兴了!二、为过客们惋惜,向钉子户致敬!三年前,我一开始就说过:新诗典,是拉力赛。
应邀撰写十集航拍电视艺术片《大美陕西》第五篇章《地理陕西》解说词:片子拿到,拍得很棒,大手笔,其实就是洋手笔,只有我的词儿才能配得上!值得我再给他们加点力!
一年没太注意,昨夜把掉我粉的家伙(基本都是三流以下诗人或过气的前诗人)一次性全干掉,有一种钱被骗去又找回来的快感。公平,是人间最重要的东西!
徐志摩是小诗人,闻一多是伪诗人。
伟大的朋友在一起,就是不断刺激出彼此的潜能,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壮大!
感冒了,上午给自己安排写两首诗,连自己都觉得错了。写诗是轻活儿,连我潜意识里都这么认为——这是有害的毒素。
敲掉了!已作古!有些好人当时见不得我等开骂,那个庸诗榜如果做到现在,不得哭死一大串,一大片祥林嫂。所谓好人,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害到自己天塌地陷!
南京庸诗榜:一帮无德无道无才无知的小人凑在一起,就是为了制造笑话地!还记得吗?萨达姆被评为“诗性人物”!真尼玛用肛门想出来滴!
从小说到诗歌到编剧到导演到唱歌到……我所在的城市专出中国顶尖人物,难道不是吗?
因《新诗典》而被歹人骂者,我来报复,反正横鼠在我每日监控中,不得好死。
感冒不吃药,我只信姜汤,民间诗人嘛。
昨晚第N次看肖恩潘的电影,一声感叹:演得真好!再叹一声:布考斯基的知己该当如是!世界上所有美好的欣赏,都取决于欣赏者自身的美好。
《新诗典》快三周年了,总结起来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营盘”就是那些对《新诗典》怀有主人翁美好情怀的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与我一起参与《新诗典》的建设;“流水的兵”就是便宜要占、力绝不出甚至对《新诗典》未怀好意者(歹人攻击还暗中相助),其结果自然是各得其所。
译了《空心人》,预感《荒原》有大问题,有些晦涩是译者没读懂没读通造成的。汉译本普遍比原诗晦涩,像朦胧诗。
享受《狂欢》吧,敢跟中国任何一位当代小说家扳扳手腕。
幸福的一天:中学同学聚餐,见到我从少年到青春的50余位陪伴者(像一团火点燃我的《中国往事2》);心潮澎湃地看李娜捧起第二座大满贯奖杯;收到2014年第1期《红岩》杂志,以“伊沙诗集”为题刊出38首“《行》系列”。好,现在开始今晚的推荐。
办好《新诗典》,切莫有守成意识(事实上无成可守),不要有大国心态(美、中、俄),而要像以色列,面对哭墙,随时准备作战,要么生存要么死亡!
译出这一册——《来自时间的大海》,心里真踏实!
《来自时间的大海》:译谁是谁,绝不搞乱。
我的狄金森是有语气的,不是哲理诗。
这种人,其实是自卑货,他们关心的是不是,像不像,而非好不好。
去长安诗歌节某场之前,准备了三种酒、两种书、两月诗精选,如果我迟到,请大家原谅,费纳大战我怎么都得瞜几眼。
在长安诗歌节上将新老名言一起说出:把诗写得像诗是失败的(见1994年出版诗集《饿死诗人》自序《饿死诗人,开始写作》),把梦写得像梦是虚假的。
《鸽子》是本口语诗人气死意象诗人的佳例(还有很多啊)!
桂中水城文学沙龙年度大奖开启了我新的得奖模式:去年我和老G获得了首届年度翻译奖,是我们的第一个翻译奖;今年我又获得了新设的年度伯乐奖——我将此奖理解为编辑奖,也是我所获得的第一个编辑奖,当然是因《新世纪诗典》的编选推荐工作而获奖,这令我更感到高兴!能者多劳。
发布1月新作那天,忽然心生一念:从未在伊沙诗歌面前开心过一次的人,是怎样的人?
河南有位诗评家说我有名篇无名句,属于典型的“二流诗人”,我感觉他的脸都被事实打胖料。
2月已写三首诗,打破了我多年养成的每月10号前不写诗(憋着)的旧习惯,关键是好梦不等人,也许习惯就是用来打破的。
过年恢复了被雾霾吓退的每日暴走,街上行人稀少、店铺关门,像很久以前的长安城,只有个别大饭店宾客盈门,像《新诗典》。
为什么《新诗典》显得题材格外丰富?除了本主持选择上的自觉性,还来自于诗的及物所带来的丰富性,不及物的诗都一个球样儿:我怎么着,我以为怎么着——无非就这么着。
不能对着布考斯基译本亦步亦趋。中国现代诗积累到现在至少比他一个人的招式多得多。我的话最客观。
诗江湖时代,好多人说过这句话:“我很讨厌排比句,你写的除外。”——客气话,话中有话。
你写得太大了,应该学会写小诗。大不但是毛病,还是无能的表现。
上午选稿有感:个人心态、职业精神、写作现状,三位一体,一脉相通,绝无例外。
傻逼说完傻逼话,觉得自己倍儿牛逼。
选了一天诗,感觉到很累,比自己写累多了,我要是个自怜自艾自私自利之徒,绝不做《新诗典》。
马年一到,职业骂我者收声料,好清静啊,大悲悯如我者,想到的是:看客们没有过好年吧?
2月份,8天写了8首诗,立春了。
我见过的人渣比你见过的人都多。
《新诗典》的种种好处,要敢一一罗列出来,对于同类岂不是灭顶之灾?
我的选诗就是一首诗。我就是“诗人”这俩字。
做好一件事,仿佛做好1000道选择题,每种差1分,就是1000分,差2分,就是2000分,这就是《新诗典》与其他的差距,越拉越大。
中文里伟大的“装逼犯”的发明权在蒋涛,不过最先写成字的是我。
长安诗歌节某场有议论:徐江定在1991年以后编诗选,貌似要跟开始大面积下岗的“第三代”过不去,我答之曰:“我的两首超级名作也被卡掉了嘛!”
重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语熟了,莎翁活了。
校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新译本),就像把自配的营养液给自己注射进去。
继续校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新译本)。将莎士比亚打造成汉语的奇迹,我以后可以不必再翻译什么了,但是我还会译——我是我自己的奇迹,我对明天的我充满好奇。
你活在貌似繁华的凶险之中。
伪体育迷,一定会把体育转化成政治,就像伪诗人,通常对诗歌所做的那样。只要是伪的,就一定不敢直面,暗中偷梁换柱。
北京十日,我做了一天诗人(主持了一场长达9小时的诗会),做了9天父亲(陪儿子参加了6场艺考),是我25年前大学毕业后最长的一段北京时光,很美好,北京再见!朋友再见!
接到一本年选,唉唉唉!等着看《新诗典》(第二季)吧,这等于两个不同国家的诗歌风貌!
每月最幸福的日子到来了:整理当月诗。想起诗江湖时代的诗歌渣滓,将我每月雷打不动的准点发布称为“月经”。
呵呵,我所有的文字都可以拿到显微镜下去看。
中国足球,特爱拿自己当试验品。
看普京做事,有一种行必果的快感,纯爷们儿,废什么话,拿下!
高级的事物永远不是想当然的简单。
《新诗典》不会放过好诗,也最敢于对纸老虎们说:你什么都不是。
这些排名就是空洞的概念,对我来说西安最舒服——前者是理论,后者是诗。
多少同行,要成为一个自觉的好诗人,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新诗典》江油颁奖礼暨李白故里朗诵会拒绝并入文化部举办的中国诗歌节,你们喊“独立”,我自独立着。
邮箱里飘来一言,令我怦然心动:“问候伊沙。许多年许多年了。您一直在。”
《美文》杂志举办全国中学生散文大赛,现场写吴雨伦出了错别字,与特等奖擦肩而过,我说:“很好,年轻时不要太满了。”
是的,读别的诗选,你感觉中国是个圈,是个村,读《新诗典》,你感觉中国是个国——诗歌强国!
也不要夸大我的敌,哪里是敌?羡慕嫉妒恨的落后分子罢了。
《新诗典》没有信用卡,无产阶级。
普京在给全人类上男人课,真过瘾!
俄军在我心中依然是苏军——苏联红军!灵魂犹在!
总觉得普京该译成普金,是普希金的多少代孙。
我如果执意要沉默,会沉默得让你发虚、泄气。
我将《新诗典(第一季)》所收录的240位当代诗人带进了我的研究生课堂,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相当于以往在中国大学课堂上被讲过的当代诗人数倍。《新诗典(第二季)》出版后继续。
我是奇迹,可惜有人连奇迹的字面意思都不明白。
只有在自己的母语里,才能得到语言的全部奥秘。
《新诗典》注定将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面子。
100年内,休想超越我的译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据我所知:表演大师都是内向性格。
选《向仓央嘉措致敬》稿三天有感:两首莫名其妙流行的赝品,把一些同行带沟里了,赝品必带来浅薄,无知者行不通。什么“见与不见”,什么“那一天”,前者为当代某业余新诗作者所做,后者为何训田的歌词。
非自觉,不敢写。
就诗歌而言,写得好的就是,写不好就是业余,怎么着?你想干什么?
汉语,没有标签,怎么说怎么写。
诗人皆自恋,关键要有度,我的自治法:多关心他人。
你正处于以为拿把刀就是绿林好汉的江湖初级阶段。
一帮朽人,从心系“高大全”到心系“高富帅”,可以,关我屁事,非要拉上我当陪衬人干吗?他们可以自信一些嘛!
我也恶俗一下,说点恶俗的真相:中国诗坛没有商量好,各有各的正1号,我这个反1号是固定不变的,这让我得了大便宜,回头他们再来找我闹——这是我诗的原罪吗?所以呀,来一个操一个!
靠,我要是小清新,你们不就是婴儿肥。
如果我不站在先锋一边,中文现代诗该如何是好!
这个冬春,《新诗典》节点多多,此后将进入深海静流之夏秋!
《新诗典》第二季新增作者137人,第三季新增作者121人。以后每年至少新增120人(每月10人),不断加入新鲜血液。
我的诗给长心者读。
“战地记者就是冲在冲锋队的前面,回头拍他们的人。”——语出伟大的罗伯特·卡帕,多像在说我。
回答一位落选(《向仓央嘉措致敬——当代诗人笔下的仓央嘉措》)者:你想多了,有陈腔,且做作,在这个题材上,《新诗典》诗人毫无优势可言,因为你们不爱仓央嘉措(比起那些写抒情诗的仓央崇拜者),我除外,我爱。
《新诗典》诗人以为自己掌握了现代诗,于是便剑走偏锋,不敢正面强攻,于是便成了此书(《向仓央嘉措致敬——当代诗人笔下的仓央嘉措》)的配角,别以为手握现代诗就是掌握了真理的法器,说穿了诗歌还是抒情的东西。诗歌对追求真理的人最无情。
在对译本的选择上,你会发现有多少糙哥,中国只有极少的诗人有语感,所以翻译的窝头才有人吃。
个把伪诗人一到3.15就兴奋起来。
手拿《新世纪诗典(第二季)》,我第一感觉是肃然。谁若不服,有种来比,拿什么比?
有了《新诗典》这三年,腌臜诗人的事件少了吧?自我作践除外。所谓“庄敬自强”。
逼人太甚,结果一头狗血——我说谁,你懂的。
里尔克在李白面前,是个知识分子小诗人。
如此之书(《新世纪诗典(第二季)》),本来应该是社科院文学所之类的机构做的,却被一人挑了,在吾国,只能如此。
勤奋说我不甚恰当,热爱,爱搞,更贴切。
近日翻《新诗典(第二季)》,对比第一季,已经不在者,我不惋惜;两册都在者,我替他们高兴。
上《人民文学》算什么,一个85后,六上新诗典才叫牛逼。
用自己的译本上课,中国大学里有几个?
《新诗典》“李白诗歌奖”当面不发钱,随后会打款。
你攻击现代诗,我绝对没度量,你一个朗诵的,靠诗吃饭还骂诗,天下岂有此理!
去他的“把诗写坏”之说吧,我这人比较唯心,嘴里嚷嚷“坏诗”者必写坏诗,原本写的就是坏诗,譬如横鼠、湖北丑八怪之流,分行的混子。
“把诗写得‘像诗’是失败的”——这话是我最先说出来的,在1994年的文章里,也只能到此为止。二十年来,任何想突破我的努力都滚进了真正的非诗和反动,明眼人看得见。
长安-江油诗歌两会的每帧照片,都透着一股由衷的喜悦,与别的活动如此不同,请诗江湖望气之人察之!
从影响上讲,《张常氏,你的保姆》当算我的第五名作,前四名是《车过黄河》《饿死诗人》《唐》《结结巴巴》(以百度条数为序)。
一定要相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的力量!
到月底只剩下一件事:伺候好本月之诗,这往往是我一月中最幸福的几日。
从1910后到2000后,《新诗典》诗人年龄落差将近百年,九代同堂。
但凡骂我译作者,一定是世上最无知最无耻的人,比骂我诗还不要脸!不论人前还是背后!
韩磊,有嗓无心,挺像诗坛上某些挺能混的伪诗人。
“我付出的一切都来自于自然|所以我也不能得到它”(张楚)——任何人写出这两句,都不一般。
诗无定法,最关键一点:我闭上眼睛能想起来——是选与不选的决定因素。
我的感觉很怪异,四川人说话我全懂,也会说,但是不敢说了。他们也能听出来,我的四川话是普通话翻译过来的。
面对世界,不挑衅也构成了挑衅,我得罪人不过如此,没别的原因。
80后别把自己当80后了,别再轻浮地彰显年轻了,你们中出了大诗人(并不是我的学生)!
不断在老江湖的笔下看到我当年投出的手稿,或曰工整,或曰字好,向自己行个军礼!任何细节同行都看得见!
我是追求全面的诗人,但我做得最好的地方还是语言。
刚写了一首好诗(本月已四首,两首是好诗),不是写,是一把揽过来。
《新世纪诗典》是中文现代诗的面子和里子!
看看老《诗典》里一半作者,他们如今在哪儿呢?有多天才?有我一个脚趾头天才么?
对孩子除了爱就是爱,等他(她)长大了就是好人。
诗集《饿死诗人》收有163首诗,任何一首放在今天依然先锋。用塞尚的话说:“我生得太早了!”
啥叫好演员?他(她),就在那儿,不用演。
兀自伟大,无所抱怨。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登上珠峰的最后几步,无限风光在险峰,恭候从今天开始直到100年后的挑战者。有本事译,不要说。
《梦》至400首,用时4年零2个月,已写至勇不可挡神不可测的境地。
梦本身,就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今天午觉,梦见沈浩波现实中不存在的胞妹了,岂能不写!再说一遍,我的梦是真实的,真实的梦才有价值,编造梦我有病啊。
那只《凤凰》,我咋就看不出好呢,甚至很糟,就像《哭庙》!
自己写不出时,就说三流诗人还在写,硬糊出一只纸凤凰。
我跟你连手都没握过,你已经上过两回《新世纪诗典》了。
月底再发,我的诗需要沉淀。网络前是三个月,网络后是一个月。
我轻易不会让女人请我的,作为男人,我比较传统。
我不会请江南人士吃这个,他们是天底下唯一不喜欢羊肉泡馍的。
李白明显是道教分子嘛。
我,爱吵架吗?不,我爱还击。
以师傅的身份忍不住夸一句:我之第一代高徒马非,这马步蹲得多么扎实,下盘之稳,击掌之实,恐怕绝大部分50后、60后也不及也!
对我来说,巴萨赛季无冠的隐痛远超过马翁辞世;对我来说,这等作家(马尔克斯)无所谓死活,早已永生。
马尔克斯怎么能跟曹雪芹比?不带这么自轻自贱的。
有一次,一个货对我说罗曼·罗兰比曹雪芹“好多了”,我差点一个大嘴巴抡过去。
老天爷非要让一个没有理论癖的诗人出这么一本书《听伊沙讲课》,那就顺从天意。
感谢爹娘,赐我好声音;感谢自己,国语说得这么好;感谢诗神,给我做好诗人的一切!
休要轻狂。换个地儿可以,在《新诗典》面前你狂不起。
有人想当黑哨,有人想当哑哨,有人只是嫩哨,我只好做金哨。
倒是从此可以开启“特色联展”新模式,《新诗典》是会不断注入新元素的,所以必然长盛不衰。
有人说我“重男轻女”——不要污蔑我哦。《新诗典》迄今共推荐509位诗人,女诗人超过100人,是符合中国诗歌原生态的。
生怕《新诗典》落个重男轻女的骂名,宁可落个重色轻友。在性取向上,我可不敢跟金斯堡大师、奥登大师为伍。
小说家之常态,他们发言都像作协副主席或秘书长。
面对好诗不选出,选家等于坑自己;面对好诗不指明,论家等于灭自己——我有大自私、大功利,遂有大公心、大良知!
我做的,都是认为值得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没那么任劳任怨。
《新诗典(第二季)》中梅丹理就是美国诗人,他是全世界中文诗写得最好的老外,《新诗典》里学问多哦,不学习吃大亏。
我之原则供你参考:我从不主动骂人,我骂必是还击,有一句,还一句,有两句,还两句,你对这个女人还得过多了。
文明正确到丧失人性了!
孔庆东夸我翻译,教授之言让污我翻译成就的一些猥琐人士如同喝尿,事实是:孔教授读了,猥琐人儿没有读。自1990年代谢冕教授、王岳川教授之后,貌似就没有北大教授夸过我了。
去你妈的韵吧——裹小脚的贱货!
对于《新诗典》的计划,我总是守口如瓶,被称作“吴站长”。
这个晚上,前两小时,过得不快乐,因为在看学生毕业论文,所以骂了人;后两小时,已经开始快乐料,因为有诗要写,还要看《冠军欧洲》。
我捍卫我用心血浇筑的《新诗典》,形象毁了就毁了吧——不过,那不过是在你的有色老花镜中。
黑狗子,及一切狗儿们,都给我记住:《新诗典》不能骂,就像《诗经》不能骂,想骂,给我憋回去!
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从我做起,像普京那样,少说多做,迎头痛击!
我每次使用“诗人”一词,都当名词用,而非形容词。
口语诗是最先进武器,口语关没过或过得不彻底,会遗留很多问题,后患无穷。
这三年中国诗评的最高成就就是我《新诗典》上千条点评。
为口语而口语,把口语当概念,也是傻逼,你注意。
在会上我做了那么好的一个发言,我发言中最无聊的一句话被记了下来,所以会议摘要不可信。
好诗太多了,对得起母亲,对得起自己。但写母亲的诗,从不敢当做“系列”——这样的诗,都是不得不写。
好状态,是需要长年精心伺候出来的。
审稿时看见好诗迭出,心情愉快。
雨中入南山,摘取王维奖。在连领三奖的红五月里,看到还是有差诗人在获奖,但心情不一样:倍儿高兴!
关于我获王维诗歌奖,最懂诗的酷评出自《新诗典》诗人韩彬:“王维诗歌奖奖给了中国最有灵性的诗人!”
老天爷开眼了!一月之内,连领三奖,平生首个国际荣誉又从天而降!
把一本诗选带进厕所,我更大的兴趣是看看这些无名作的著名诗人们自我感觉良好的装逼,在文章里。
横鼠,你说任何事,都是一外行,上帝对你太过残忍。
湖北丑八怪,永远做开天辟地科,永远的拾人牙慧的牙慧!
在中国的大学里,没有人讲得过我——我把话撂这儿。
第一个“女诗人周”,意味着《新诗典》专题策划的成功开启。大家不要忘了,我可是当年的《文友》的策划、主编——媒体精英哦,招子多着呢。
这二年干得比较猛,也担心自己身体出问题,生日前夕体检一番,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反正谁骂口语诗,我都会站出来说不,不管是我的朋友、敌人还是陌路人,杜甫说“诗是吾家事”,我想说“口语诗——更该叫‘活性的现代汉语诗’,我来管!”,骂口语的评论家,就是自甘与庸众为伍;如果再让我看出是诗歌江湖的山头阴谋,我就更不客气。
口水诗也不能骂,因为有人是把口语诗先偷换成口水诗,然后罗列“十宗罪”(这是什么鸡巴词儿啊)。
我反对知识分子优越感,也会持续一生的——我身在学院这么干,更有说服力。至于“本土意识”,意识有啥可说的?关键在于我已经写出了本土质感、味道、气息、气象,而尔等边儿都挨不上,还是故纸堆+翻译腔的二尾子。
我总是被利用来衬托起某些废物。从小坛子到大坛子,多少年来皆如是。
看到这一本,我可以安心了,“狂译”两三年终达顶峰,我可以安心去写一部长篇小说了,以后在长篇与长篇之间,译一本,译什么,随缘。
这一伙是中国诗坛真正的底层,以为天下的诗歌奖都由我颁发,官方小爬虫可以耻笑之!
昨天接吴雨伦,将一本书塞他手中曰:“记住,你的父母是莎士比亚的译者。”
大师在当下,大师正值壮年——敢面对就面对,不敢面对就去死,一帮窝囊废!
来而不往非礼也:自以为被遮蔽,实为作品平庸,宁愿当将其遮蔽者的老狗,反咬为其张目者,只因嫉贤妒能,网络前装作谦谦君子,微博后毕露妒火中烧,毫无底线恩将仇报的下三滥!
我从小就学会了一个打架的逻辑:你先打我,我必打你,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我得让对方付出代价。满洲片儿警,每天在诗江湖上刷我一张大字报,坚持五年,已经付出了身体上惨重的代价。湖北丑八怪和混居津门下水道的横鼠,从开微博起,坚持日常骂我,不断造谣诽谤,故不放过。
横鼠,满口谎言的人,付了不少代价,你还得付下去,直到山穷水尽。遥想你这雏儿初微博,也只是想拿我一人讨彩,看今日却成过街老鼠,你的智商玩不转诗也玩不转江湖,就是给自己挖墓道的蠢货。
横鼠,你还忘记了,我每周还有6-10节课,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培养着祖国的未来,让未来不像你这么狗屎。
原始造谣者张羞,说我冒充杨黎;媒体造谣者董辑,说我冒充周伦佑。各为其主,口径不一。于是,我一人冒充俩,骗入荷兰王国,参加了鹿特丹诗歌节。
这件事我愿意天天说,谢谢给我机会啊——真相是:一个叫伊沙的人利用了吴文健的护照骗取了荷兰大使馆的签证,一个叫吴文健的人进入荷兰到达鹿特丹后又利用了伊沙的诗完成其精彩的表演。啊哈哈哈哈!
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世界上最好的诗歌节,有本事自己去。不要咬着我的裤腿蹭着去,出国不让带宠物。之后我又去了斯特鲁加——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节,还是不让带宠物。
一次次自取其辱,败絮其外,就是你的命,在你这个谎言传播器面前,我很想造一次假,让你们逮着一次,以显示我非圣贤,咱们试试看吧。顺草泥马。
伊沙、老G于1995年首译布考斯基,开启翻译生涯,那时候这些鼠辈还在后海子时代抬棺呢。大翻译家,有首译、有重译、有专译、有泛译,我们正是。
骂过诗坛渣滓,关注顿时增多,人民群众觉悟高。
对所有负能量迎头痛击是很重要的!
早餐,两个煎蛋、一块面包、一杯绿茶。餐毕,开始工作:继续为《新诗典》选诗。忽然想到:质疑我工作成果的那只横鼠,正在津门的下水道里干什么?宿醉?晨勃?
这是我的原罪。我今天为选诗和提前写推荐语已经工作了10小时——我的68本书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所以我必须操它们,并对某些不怀好意的看客竖中指。
想上《新诗典》,水平不够没上去,转而骂我……这也并非见不得人的事,说明很在乎诗嘛,无奈这些渣滓习惯于张嘴说谎,开口咒人,还勒令我必须拿出证据(否则死全家),那就拿吧!可惜我换过一台电脑,否则这个七窍生烟在我面前的谄媚还有很多可以展示。
选稿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发现优秀的新人,刚才看到一位特优的,中国在下边窝着的好诗人太多了——说一千道一万,发现他们才是《新诗典》最大的贡献和魅力,伪精英、名人录的偷懒选法哪里是《新诗典》的对手。
《被一代:中国新世纪诗歌档案》是小说家、出版蒋一谈先生邀我主编的,虽然最终未能出版,但为前两季的《新诗典》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我借此感谢他,所有入选过前两季的《新诗典》诗人都该感谢他!
这些整天盯着别人戳是弄非的懒汉、贱逼,特朗斯特罗姆获奖的那年,何其兴奋!向写多者兴师问罪,门罗获奖又向写长者兴师问罪,夹在中间的莫言反倒成了正能量。
明天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2周年,我想说的是:在《新诗典》,所有阶级都该并存并发出各自的声音,没有阶级的高低贵贱,只有诗歌艺术的各显其能。从宏观上来把握一部诗歌总集的编纂,恐怕其他编选者与我的差距更大。所以,我向来是反对“知识分子”、“博士诗歌”、“上游俱乐部”或者“草根”、“打工诗歌”这些劳什子的。都是对某种阶级或阶层的一种强调。
这只香港脚,就是臭诗人。贼一喊捉贼,装作不是贼——这叫“道德免己”。
转自诗生活伊沙专栏: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art&id=79114&str=1268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