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今日之诗坛》——伊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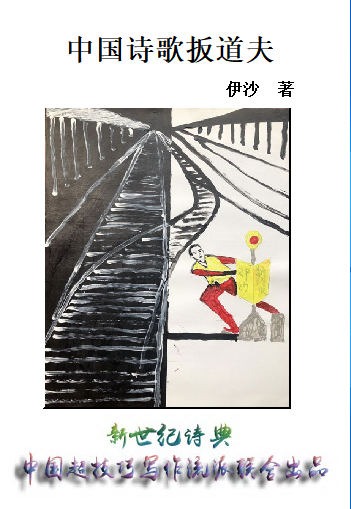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我看今日之诗坛
——在《诗歌报》“金秋诗会”上的发言
一、翻译界充斥着太多的译匠,无法宏观地把握国际诗坛的真实状况并替诗人做出选择。他们与国外的交流往往是旅游团观光客式的,手中的外国文学史是他们的导游图,接触到的都是学院和学会认可的一些“大师”。他们总是在译已经成为传统的东西,对正在发生的无从了解。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令人悲哀:中国的现代诗歌将沦为西方传统诗歌汉语译本的摹本。我怀疑那些非诗人的译匠,并对他们的译介保持警惕。在翻译界的选择之后,诗人们的再度选择又令人失望,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决定我们只会选择适合我们胃口的软东西,撞击和刺激便消失了,一切又回到原先的和谐之中。于是西方便成了我们重塑的西方,世界成了我们臆造的世界。
二、目前诗坛的泛道德倾向和狭隘的文本主义严重阻碍着现代诗的多元发展,十年前曾经显现出的多种可能性如今已变得非常单一。“非非”今何在?“整体”都跑到哪儿去了?“莽汉”还莽吗?如果说这是流派消失的结果,那代表上述写作倾向的个人又在哪儿呢?一个诗人的自杀竟会使以他为代表的那路诗一跃而成为诗坛的主流,这是新闻事件对诗歌发展的导引。世纪末的诗坛上充斥着现代面具下的低吟浅唱,诗人们嚷嚷着“词”、“词语”,却不知道如何去找它发生的所在。从文化到文化,从典籍到作业本,这一代诗人完成的极可能仅仅是过渡、文化的传承,难道一代书生的木讷面孔就是我们的宿命?创造力的丧失和生命力的萎缩比那令我们心猿意马的生存压力更加可怕,“挺住”绝不“意味着一切”!只有进攻的姿态才有创造发生的可能。不要一提“后现代”就哆嗦,我想对那些“恐后症”患者说句话:所谓“后现代”绝不仅仅意味着主义和流派,当一种思潮发生了,呈现在大家面前,而我们自身的环境也正在一天天的改变,我们的写作不可能毫无变化吧?这种变化难道仅靠意象的置换就可以完成吗?文本主义的时代正在过去,我们的身体渐渐暴露于词语的外衣被扒掉后的阳光中。
三、诗歌理论界的窘迫令诗人们难以获得应得的自足感。有人提到小说家们的从容自得,并不完全是影视光顾与市场挂钩的结果,在某种程序上它得益于小说理论界迅速的甚至是仓促的反应,你说它乱贴标签也好滥造新词也好,他们的工作起码是在进行之中。诗歌理论界像一张表情暧昧的脸,这种暧昧不知是有所悟还是有所惑,每个人都像是指点江山的战略家,诗人们在尔等眼中不过是一粒粒棋子,走不走你这个棋要看有没有战略上的需要(与你的诗写得好坏无关)。连总结都做不好的诗歌理论界更不要提预见和导引。诗人兼作的理论家们更多只是一些山头主义者,像“中年写作”的提出,难道几个人的写作方式和状态可以当作一种理论向诗坛推广?“中年写作”者们是否经历过他们指责的“青春写作”?从未“青春”过的人抱住了“中年”这个意味成熟的词。理论也是写作,理论家也是作家,成熟与否首先是要看他是否找到一种个人的批评文体,而不是靠说出什么可能是所谓“新的”见解。
(1996)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