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诗旅》伊沙

英伦诗旅
伊沙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
——[英]威廉•布莱克
一
此行缘起非常之早。
2005年5月25日——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记住这一天,是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好日子:在这天中午睡午觉的时候,我一连接到两个电话,全都是好事。其中一个电话是一家海外出版公司的女老总打来的,要一次收购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尚在写作之中),另一个是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已经不是)打来的:说澳大利亚翻译家西敏接到英国一个诗歌节的信,信中说想邀请我去英国参加他们的活动,西敏正设法与我取得联系。
很快我便收到了西敏本人的邮件,信中说:英国曼彻斯特诗歌节欲邀请我和他参加他们的活动,今年或明年,问我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西敏说他今年的工作已经排满了,那就明年吧。结果到了“明年”——2006年却没了消息,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敏在2006年底带给我的好消息是来自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这个邀请让我在2007年夏天独自一人成行了。一晃到了2007年底,英国那边又有了消息,很快正式的邀请函也寄到了,是向我们两人同时发出的,邀请我俩参加在2008年11月7-9日举行的第20届奥尔德堡国际诗歌节。
拿到邀请信,我才知道是奥尔德堡诗歌节,而不是什么“曼彻斯特诗歌节”,而西敏兄还糊涂着呢!他要再过几个月方才恍然大悟:我们将要参加的诗歌节跟曼彻斯特没关系!至于他脑海里怎么蹦出了一个曼彻斯特,他也讲不清楚。
西敏真是我的福星!
实际情况是:此次英伦之行、去年荷兰之旅、以及我的头一个正式的英译本诗集在英国的出版……所有这些好事的缘起都要归到西敏这里。2003年,我们在中国的西北相遇相识,我送给他新鲜出炉的《伊沙诗选》(青海人民版);2004年,他选译了其中的10首诗并挂在由他担任编辑的国际诗歌网上——我的上述好事便是由此而起,由西敏所译的这十首诗而起!
二
听说,英国的签证是最难拿到的(比美国还难拿)——当然,这是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而言。那么,我究竟要签几次证才能到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英国驻华大使馆所辖的签证中心位于东直门的东方银座大厦上,我在两个月中两赴北京三次进过那座楼,两次正式递交申请材料,一次拒签,一次获签。那种疙里疙瘩七上八下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伦敦希思罗机场五号航站楼的入关处,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的小姐看了我的护照问我:先生,为什么曾遭拒签?我用幼稚的英语回答:诗歌节要付我两百英镑,签证官认为这不对。制服小姐让我坐在英国境外的一张椅子上等待,她要去打一个电话——我不知道她是要给英国驻华大使馆打还是给英国诗歌基金会或奥尔德堡诗歌节打,只好老实等待,听天由命。还好,在五分钟漫长的等待过后,制服小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喊我过来,举起大印,在护照上狠狠地盖了一下,然后说:谢谢!再见!
真不容易——我是说:不论是作为一名中国公民还是一名中国诗人。过去是“这边”不让出,现在是“那边”不让进,东方亮了西方不亮。身为一名中国公民,我该承担别人对我所持护照的傲慢与偏见;作为一名其志也大的中国诗人,我应当承担得更多——对我来说,这毫无问题,早已想通,老子认了!
尽管此行,我比四年前申请赴美遭拒签的那一次想去得多:这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的诗歌节不说,对我个人来说具有突破意义的英译本诗集将在这个节上首发!还有便是:主人的热情让我感动,尤其是到后来,他们执着地提出:如果我最终未能拿到签证而无法成行,他们想让我以网上视频的方式“参加”这届诗歌节,朗诵我的诗!
这近乎悲壮了!
三
五年之中,我最大的变化是成功地减了肥,但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五号航站楼的出口处,西敏还是一眼便认出我来——他提前两天经过22小时的残酷飞行先到英国就是为了接我!西敏还像五年前那样高,略微老相了点,但却老得很有味道,反倒让五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显得有点生涩,那一个像博士,这一个像翻译家。西敏大我五岁,是1961年生人,他后来两次十分自然地说自己属牛,说得我直想乐:汉学家很难说是“老外”,他们的一部分意识与思维已经中国化了……
西敏的身后站着诗歌节的女司机,与我握手寒暄,她说经过两天刚跟西敏先生混熟了,但是一听他跟我讲中文,又令她感到很陌生——从此开始的两个多小时里,她的这份陌生感只会加剧。因为从希思罗机场到奥尔德堡的高速公路上,西敏跟我说了一路中文。
译者深知作者心——因为原本就同此一心,一上车西敏便说:书出来了!说着便从座位上操起一本给我看——我的第一个在国外正式出版的英译本就在眼前(西敏带着它来接我)!说实在的:我真想亲它两口!西敏说他很喜欢这个封面——布拉达克西书社的主编很喜欢英籍华裔画家盛奇的作品,向我提供了几张让我选定,我选择了目前这张相对平和不事张扬的《红喇叭》,因为觉得与书名《饿死诗人》(定此书名是西敏的主意)很合,可谓是:芸芸众生,饿死诗人!
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记得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家中翻箱倒柜大动干戈地将自己1988年正式创作以来的数千首诗全都找出重读一遍,重点是那些从未发表或出版的篇目,并从中精选出适合翻译的300首发给西敏,西敏与另一位译者陶乃侃(他是中国大陆出去的华裔)最终译成了120首,其中118首构成了手中的这本书。他俩用半年的时间就译成了,应该算快的;而布拉达克西书社在其网页上将本书的封面连同我的照片和评介文字挂了快一年了,所以让我觉得久。
我手摸英文版的《饿死诗人》光滑的封面跟西敏说话,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仿佛任何话题都会让我们兴奋得说个没够!
车内飞扬着中文,车外的天空已经全黑(这里的天黑时间是四点半),再加上又是在全球都一模一样的高速公路上疾驰,让我怀疑是否到了国外,只是迎面而来的车流在黑暗中形成的璀璨的“灯流”,是我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
汽车绕过一大片灯火,女司机说:这便是伊普斯威奇——我马上反应出这是距奥尔德堡距离最近的较大的城市了,在普通的英国地图上,是没有奥尔德堡的。女司机介绍说:伊普斯威奇的足球队不错,在1978年获得过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那时候还不叫“英超”)。开过伊市之后,她将车停靠路边,用手机发了一个短信,发完后再继续开车上路。
车子向前开去,女司机的手机上回过来一条短信——是诗歌节主任内奥米•佳法女士发过来的:她说她简直不相信我即将到达这事儿是真的!来之前,西敏曾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初遭拒签让主办方很是沮丧,再签成功则令他们非常振奋——当时我以为这更多说出的是西敏本人的心情,现在全信了!
说到便到了,车子穿过空无一人的小镇,停在白狮酒店门前——我在英国旅游网上已经查到了即将下榻的该酒店,看过它的玉照,所以一点都不觉其陌生,反而还有几分亲切!女司机在说吃晚饭的事,我说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晚饭,而是抽一支烟——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因为我的打火机在首都机场出关安检时被搜走了……
我们仨在酒店门前合影留念,用女司机的手机。就在一百米外的黑暗中,便是北海的涛声——此处有诗,在此不表。
女司机走了,西敏带我走进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他提前两天来,对这里的一切已经相当熟悉。他住28号,我住34号,我刚在房间放下行李洗了把脸,西敏便来告诉我说:大老板打电话来,说马上就到酒店门口,她说她要陪你抽支烟,然后带我们去吃晚饭。
几分钟后,我们便在酒店门口见到了热情洋溢的“大老板”——诗歌节主任内奥米•佳法女士,竟是一个美人儿!令我想起鹿特丹诗歌节的两位策划:帅哥安科尔和美人曼娜——在这些遥远的地方,天之涯海之角,喜欢我诗的都是一些美丽的人儿,叫我说什么呢?本来嘛!
内奥米为我点燃一支烟——是我到达英国之后的第一支烟,但却没有抽出滋味,因为忙于寒暄。主人忙于了解我在饮食方面有何忌口有何讲究,我的“我又不是穆斯林”的回答让她乐了,听她说诗歌节请到的某诗人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要吃全素,搞得他们有点头疼……
抽完一支烟,内奥米开车带我们去不远处一座叫作“诗人之家”的小楼中,几分钟便到了。那里已经聚集了几个诗人,专门聘请的厨娘已经做好了饭,厨娘用汉语的“你好”跟我打招呼,厨娘说了两种饭菜的名字让我挑选,我只听懂了鸡肉和米饭便要了,她将米饭和鸡肉盛在一个大盘里——这种吃法有点像中国的盖浇饭,鸡肉中加了些橄榄但并无奶油之类的怪味道,所以我还能接受,喝的是意大利牌子的啤酒。
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桌边吃饭,有一男一女两位美国诗人,他们是一对夫妻,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英国男诗人,有一位伊朗裔的英国女诗人,还有这项诗歌节的创办人和老主任,他也是个诗人,刚刚参加完一场朗诵,诗歌节的节目已经于今日白天开始了……伊朗裔的女诗人咪咪•科哈瓦提听内奥米说我抽烟,便邀请我到门外去抽一支。老太太1944年出生于德黑兰,十几岁便随家庭移居到英国,现住在伦敦,母语波斯语只会说不会写,她受的是完整的英式教育,自然是用英语写作的,得过前进诗歌奖,还进过艾略特奖的决选名单。抽着烟,她问我是否认识毕飞宇,我确定她说的是中国作家毕飞宇后,说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上个月在我母校北师大开会时见到过,就在电梯里。她说她在美国见过他,如果我再能见到他的话,替她问候他——那我就在这里替她问候了!
抽完一支烟,我们又回到了屋里,大家聊得很热烈,但困意却不断地朝我袭来,我偷眼看了一下我那在下机之前已经调成格林威治时间的手表:晚上九点,相当于北京时间凌晨五点——难怪!这本是我睡得最香的时刻!耐着性子又坐了一会,我和西敏便告辞了,老主任亲自开车将我们送回白狮酒店。
上二楼经过西敏所住的28号时我小停了一下,主要是向他发出一个请求:能否将他手中带去接我的那本英文版的《饿死诗人》借我一夜?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他手里仅此一本,他作为译者领到的样书已经被他从镇上的邮局寄回到澳大利亚去了。他满足了我的请求,将书郑重地交给我。我抱着书欢天喜地地回到了我的34号!
回到房间我却没有立刻睡觉,用酒店供应的咖啡袋冲的一杯咖啡不会影响我的睡意,都是这本诗集给闹得!我没法不想起我在14年前所出的那本中文版的《饿死诗人》(那正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那一本是从六年的诗中精选而出,这一本是从二十一年的诗中精译而成,我没法不回想自己走过的历程……
后来,我搂着自己的诗集睡着了。
四
第二天一早,正如我在几天前完成的《诗之堡》一诗中所写到的:
海鸥的叫声唤醒我
起床下地扑向窗棂
提起窗梁探出头去
却见一树乌鸦
我迅速起床,独自一人遛出酒店,大步流星地扑向北海……
沿着海边转了一小时回来,与西敏在酒店的餐厅共进早餐。餐厅里很空,没什么人来吃,更不见一个诗人。由于今日白天诗歌节无活动,我和西敏打算做一天“驴友”,早餐后便出发了。出门后沿着滨海路一直向着镇中心的南面走,我们冒着零星小雨来到奥尔德堡书店,在书架上看了看:还没有我的书。西敏说:布拉达克西书社已经发来几十本到这里。离开时我才注意到店外橱窗里摆放的是威廉•布莱克的精装诗集,格外惹眼,看来我在“细读”单元中选择布莱克的诗真是选对了!这时候,我们正好碰到伊朗裔的女诗人咪咪•科哈瓦提,西敏提议到前面一家挺好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她说对不起她还有事:她报名参加了诗歌节的“工作坊”,活动在十点钟开始。这个诗歌节的“工作坊”是干吗的?我始终没有搞懂。只记得鹿特丹诗歌节的“工作坊”是“翻译工作坊”,便觉得自己玩不了,“细读”还是他们通过西敏向我转达了期待的意思,我才决定参加的。书店和不远处基金会办公室的橱窗中还挂出了“诗传单”,出席诗歌节的每个诗人都有一首短诗被制作成这样的“传单”,我的是《生逢毛时代》:
我无法选择自己
肚脐眼的模样
并要求它
不要生得这么丑
我也不想老是
把肚脐眼里的
藏污纳垢翻出来
展览给人看
这完全是他们的选择——我也甚觉满意:它像是一则宣言,满含着一个中国诗人的尊严!既有中国的,又有诗人的!
在温暖如春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之后,我们俩继续上路,到小镇的各处去转。中午时分,我们刚好走到“诗人之家”吃午餐——奇怪的是:还有米饭,我就又吃了一顿鸡肉米饭。还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与早餐时的情景相似,仍然不见其他诗人!西敏说:难道诗人们都不食人间烟火吗?饭后,我们走回白狮酒店休息。我素有午觉癖,三点钟时,正睡得香,西敏来敲我的门,说:这个英国,四点半天就黑了,我们利用天黑前的时间再去转一转吧!
这一次我们向北走,走了一段路,便看见海滩上摆放着一个黑乎乎的玩艺,有人在其进前拍照留念,西敏说:那是已故的英国著名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的纪念钢雕——哦!我一下想起来了:来之前我在网上搜奥尔德堡的信息时搜到过此人:他于1948年创办了奥尔德堡音乐节,如今已经61届了,是世界顶级的音乐节之一,古典音乐的发烧友懂得:奥尔德堡音乐节是他们要收藏的版本。布里顿还是个同性恋者,于1968年在本地去世。哦!一个举办了61届的国际音乐节和一个举办了20届的国际诗歌节,恰好组成了一对翅膀,让这个地图上没有的小镇飞向了世界……
钢雕像贝壳,又像留声机的喇叭,用镂空的手法留下了布里顿的一句话——西敏给我翻了:说得很牛B,可惜我忘了。
在钢雕前互拍了两张照,我们便离开了那里,向着远处的一座美丽的村庄进发,走到半路,感觉天色渐暗,天边已是黄昏景色,怕天黑走不回来,便从另一条乡间小路折返回去……
六点钟,在“诗人之家”吃晚餐时总算见到了两位诗人:一位老先生、一位长得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老先生听说我从北京飞来,便说自己十天前还在北京,我问他是否受邀去参加某项诗歌活动,他说不是,他是作为游客自己去玩的。他问我对北京熟悉吗?西敏说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北京的楼盖得太西方化了——我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没说什么。
饭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诗歌节的活动:也没什么开幕式,各项活动就此全面展开,有一个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家庭朗诵”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们便去了七点多钟在皮特•皮尔斯画廊举行的“细读”活动,主讲人叫克里夫•杰姆斯,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诗人,算是西敏的老乡。画廊里来了40多名观众,从十分正式的穿着上看,倒像是他们要登台似的——我觉得这一点十分可爱!杰姆斯在讲一首诗——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是:他竟然把“细读”搞得十分幽默,画廊里不时响起观众的笑声……十五分钟的“细读”很快便结束了。
退场时有人走到我面前来打招呼,用汉语叫着我的名字,我定睛一看:是一张亚洲面孔的中年人(画廊里也就我们两张亚洲面孔),他一定是看了诗歌节的几种宣传资料,才知道我的,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孟元勃,是个画家,是德国出生的华裔,现在住在爱丁堡,他太太是位英国女诗人,他是专程陪太太来听诗的,我们寒暄一番,便道再见。
退场后我们随着人流来到同一条街上的银禧厅——这个能够容纳三百人的厅是需要买票入场的,每张票价14英镑。我和西敏作为受邀者都发有胸牌,凭胸牌可以免票进入诗歌节的各个活动场地。我想起来之前,诗歌节的组织者曾发给我一张节目表,问你希望观摩哪些节目,为的是最大限度的将座位留给买票入场的观众。我和西敏在靠后较高的座位上落座,眼见整个大厅很快便坐满了。
此处的主持人是诗歌节主任内奥米女士,她介绍了今晚前半场朗诵的两位诗人——正好是昨晚刚到时在“诗人之家”见到过的两位:苏格兰诗人格瑞•卡姆布瑞格和伊朗裔的咪咪•科哈瓦提。接着便是两位相继登台朗诵,每人25分钟。由于没有大屏幕出字幕,我比去年夏天在鹿特丹时更像个聋子,只能纯看人家的表演了,到后来竟然酣然入睡!直到中场休息方才醒来,邻座上的西敏很知道照顾我,说别听下半场了,回酒店休息。离开前,我们跟“主人”内奥米打了个招呼,我趁机将我从中国带来的礼物送给她——是一个十分精巧的秦代铜车马的模型,她问我可以打开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打开看过之后她显出很喜欢的样子,说她很爱骑马……
离开时我和西敏还在门厅的“诗人墙”前留了影,那上面贴满了所有受邀者的照片。
走在回白狮酒店的夜路上,路灯下西敏点评道:苏格兰诗人的朗诵有口音;咪咪的诗太甜了,写的是爱情,用的是古波斯的一种传统诗体,还是押韵的……
回到房间我便睡了——看来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
五
又是海鸥的叫声将我唤醒,又是窗外晨曦中湿漉漉的景色——但我深深地知道:今天不似昨日,因为今天是我的朗诵日。
11月8日——从三、四个月前我在诗歌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节目表的那一天起,这个日子就在我心里种下了,那时候签证还没影儿呢!我后来遇挫愈奋地再次去申请签证,就是为了通向今天!
早餐时的情景也和昨天不同:人很多,有多位诗人在此就餐,其中一位很招人,诗人们都纷纷起身过去跟他打招呼,我觉得他有点面熟,想起《诗报》上有他的专访:此人可是今年英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明星”:T.S.艾略特诗歌奖与前进诗歌奖的双奖获得者,就这两项重要的诗歌奖他都不是首次拿,名叫格奥格•斯兹尔特斯,我记得中国的媒体上也有关于他的报道……
早餐后,我和西敏到诗歌节办公室报账领钱。我的往返机票是由主办方提供的电子客票,不过钱,我报的是西安至北京的往返路费和签证费,除此我还领到了250英镑的劳务费——正是在邀请函上写明的这250英镑,叫我差点来不了!签证官认为这构成了一种非法雇佣关系,是他自己忽略了诗歌基金会乃非营利组织。
领了钱,我们便去同一条街上那家挺好的咖啡馆“喝一杯”。然后到银禧厅去听十点多钟开始的朗诵——今天和昨日不同:星期六,全天都有活动,节目表上密密麻麻排得满满的,是三天诗歌节里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将在今晚朗诵的最后一个出场——由此便可看出主办方对我们这个节目所寄予的希望。经过银禧厅一侧的停车场,见一辆有点眼熟的小车的门开着,透过窗玻璃正看见诗歌节的内奥米主任正在车内念稿子——她一定是在为今天的主持做着准备,看见我们,示意一下,继续准备……
果然还是内奥米主持,她介绍了上半场出场的两位诗人。首先出场的是一位叫做提法妮•阿特金松的高佻美女,从小册子上的简介上看:她1972年出生于柏林,生在军人家庭,1993年后移居到威尔士,在威尔士大学任职。她2006年出版的处女集为她赢得了杰伍德•奥尔德堡第一本诗集奖——每年一届的此奖的颁发也是本诗歌节的一项内容。她开始朗诵,每首诗前需要讲很多话,努力把观众逗乐,观众也就乐了。她在一首诗中忽然喊出一声“fuck!”,令我我感到十分突兀,西敏的现场小声评点是:不自然。第二个出场的是爱尔兰诗人丹尼斯•奥•德瑞斯考尔,他生于1954年,已经出版过八本诗集,我感觉他像是一个实力诗人,果然,西敏也喜欢他,说他的诗写得比较好,加上爱尔兰人讲的英语很好听,朗诵起来有优势。
中场休息我收获颇丰:内奥米提了两袋共12本英译本的《饿死诗人》给我——那是布拉达克西书社转给我的样书;我看到英语世界颇居权威性的《现代译诗》杂志上刊登了我五首诗作,便自己掏了9镑买下一本;我从大厅边门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发现男洗手间里贴满了“诗传单”,叫人边小便边读诗,我的《生逢毛时代》被贴在男洗手间的门上;在门厅的小卖部,西敏买了一杯桔汁给我,画家孟元勃过来跟我们交谈,并将其太太介绍给我们认识……
下半场的朗诵者是昨晚在“诗人之家”见到过的去过北京的老先生,基金会出的《诗报》和诗歌节印的小册子上都没有他的采访或介绍,西敏说他是顶替另外一位老诗人来的——那位老诗人临时因健康原因而无法到会。与昨晚所见迥异:出现在台上的老先生一下子变得话多而幽默,还是西方诗人的老一套玩法,在读每首诗之前都要插科打诨地说上很多话,都是一些故作幽默取悦观众的废话,诗到未必是幽默的……由于全能听懂,西敏的反感比我更甚,他质疑道:难道观众真的喜欢这种诗吗?一个老男人喜欢上了一个小女人,诸如此类的人生烦恼……
终于结束了。
西敏建议:不要去“诗人之家”吃那一成不变的鸡肉米饭了,回白狮酒店去吃。我坚决赞同,说最好吃点带有本地特色的东西。结果我们都点了鱼——百分之百都是从北海里打捞起来的新鲜鱼,只是做法不同而已。我的那份配有薯条、扁豆、沙拉酱,味道相当好,我们还要了本地盛产的苹果酒,想不到的是:这种酒竟然很厉害,只喝了一小瓶,我已经面红耳赤地有了几分醉意……这顿饭是我在此次英伦之行中吃得最满意的一顿饭!饭后是我结的账,两个人带小费,40英镑,贵是贵了点,但是很值。饭后,西敏要去听一位英国诗人同时也是英-法语的翻译家的一个关于翻译的讲座,我说我什么也不听了(反正听也听不懂),回去好好睡一觉,然后为晚上的节目好好准备一番……
回到28号,我一觉睡到四点钟,起来后沐浴、更衣,将晚上要朗诵的诗的中文部分一一找出来——今晚要朗诵的篇目是这么定下来的,我来之前选了20首,交给西敏定,让他从英译文的好坏以及读者的接收考虑,他经过一天一夜的考虑,刚才在与我共进午餐时,一口气给我报出了十首诗名,连顺序都排定了……我将原文找齐后,又逐首默念了一遍,一切搞定之后,我给西敏所住的34号打电话,他在,邀我过去坐坐。
在这座滨临北海始建于1563年的古老的小酒店里,我们住得很舒适,如果说我的房间像春天般温暖,那么西敏的房间则像夏天般火热——原因是这里的暖气片是可以调节的,他将温度调至最高,调到了可以穿衬衣的温度,他毕竟是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飞来的,那里正是盛夏酷暑,日最高温摄氏40多度……
我问他午后那个关于翻译的讲座如何,他说令人失望,又是插科打诨,一点实在的内容都没有。之后,我们便聊起晚上我们自己的节目,我发现他也是在做准备,便说我念错了都没关系,主要是把情绪传达给观众就可以了,关键在你,你可以读得慢一点,让他们把诗的内容听清楚。他说没问题。
六点钟我们去“诗人之家”吃晚饭,午餐吃得好,我什么都不想吃,只要了一小瓶意大利啤酒。餐桌边坐着三位年轻的女诗人,显得气氛都不一样。其中一位就是吃素的那个,她是今年杰伍德•奥尔德堡第一本诗集奖得主,吃素者总是爱宣讲吃素的好处,她吃的可真是“大素”:鸡蛋、牛奶也不进,但却喝酒,还说自己特能吃辣,显然不是皈依了佛教。我跟她讲了“食不过午”的好处,她听得很是专心,估计回去就照办。她人很瘦,头上戴了一朵小黄花。
七点钟我们到达了银禧厅,先到舞台上卖书处转了一圈,发现了我的诗集已经码了两堆在那里,然后照规矩坐在了头一排,与今晚的另外两位朗诵者坐在一起。出版我诗集的布拉达克西书社的人终于出现了,当面交给我四百英镑的前期稿酬,并让我在一个接收单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内奥米很可爱,她过来刚要跟我说什么,一看到我们正在接洽钱的事,便一声惊呼:哦,钱!然后马上回避。办完手续,布拉达克西的人说:去年诗歌节,他们在此首发了诗集的一位黎巴嫩老诗人很会朗诵,大受观众的欢迎。我明白他的意思,心说:您就瞧好吧!
今晚第一个上台朗诵的是坐在我左边的英国男诗人,他同时还是英-法语的翻译家——西敏午餐后就是去听他的讲座。从简历上看,他得过前进诗歌奖,还是英国一家著名文学刊物的编辑,但我感觉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诗人。内奥米在台上介绍他和另一位美国女诗人时,他老冲那个美国女诗人看,还扮鬼脸,好像他承受不起主持人的溢美之词似的。上台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西服内兜里取出一个扁扁的金属酒盒,拧开盖子,喝上一口,然后将酒盒搁在放水杯的桌子上,清清嗓子开始说话,照例是每首诗前都要说上很长的一串故作幽默的废话,然后开始念诗,西敏说又是老男人爱上小女人的烦恼。我刚想到:他肯定不会忘记酒盒这道具——果不其然,他就自己找过去了,再喝上一点酒,接着瞎侃、念诗,其实他的诗一点都不幽默,就靠这点小动作和诗前的玩笑,逗观众一乐了。他在另一方面倒是挺霸道的,那就是对时间的侵占,到最后我看了一下表:他超时了有十五分钟。下台时他自然不会忘记带走他的道具——那个酒盒一定陪他到过很多朗诵会……
第二个上台朗诵的是坐在西敏右边的美国女诗人芭芭拉•哈姆贝——她是我在抵达当晚就在“诗人之家”见过的那对美国夫妻诗人中的女方。从简历上看,她出生于新奥尔良,却是在火奴鲁鲁长大,现任教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她的诗人丈夫叫做大卫•科比。我感觉她女人味不足,有点中性,是个典型的女知识分子,叫人不由得不敬而远之。她那冗长的诗体在本届诗歌节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她的最后一首诗:几百行,写的还是日常生活——让我不免起疑:这是什么样的诗呀?我想起中国的“第三代”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那种“生活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天生“丑陋”的诗体,属于口语写作比较初级的阶段和比较低级的一类。她朗诵完下台坐到座位上之后,隔着西敏,我伸头看了一眼她手中的诗集,想看清楚她这种诗是如何排列的——分行还是不分行?如何分行?但是晚了,她合上了。
中场休息。
半小时的时间我需要做三件事:喝水、抽烟、入厕。考虑到门厅买饮料的小卖部前的小长队,只好取消第一项——我想:我等上了台,去喝专为朗诵者准备的水吧。上完厕所,我到边门外抽烟,见到伊朗裔的咪咪和德国生的提法妮,后者跟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在一起,很是亲昵……
抽完两支烟,我回到场内自己的座位上,将准备朗诵的诗稿和诗集拿出来,这时,孟元勃忽然浮现在我面前,用很激动的口吻说:伊沙,这是最好的观众!最可爱的观众!你不感到激动吗?你要为他们朗诵!我说:我为你和西敏朗诵,只有你俩听得懂中文,我会好好享受这个时刻!他拍了我一下,就到后面去了。
舞台上的格局变了,增加了两把椅子——那自然是为我和西敏准备的。我俩提前上台就座,都到这会儿了,都到舞台上了,我听见内奥米还在问西敏:伊沙喜欢朗诵吗?西敏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内奥米听罢很高兴。
时间到了,全场顷刻间便安静下来。
六
我想另起一节来写我们的朗诵。
既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又符合文章结构的均衡。
主持人内奥米再度上台,专门介绍我,她的话与她在《现代译诗》杂志上所写的一篇短文中的话大同小异——文中是这么写的:“我们于2004年首度发现他那惊世骇俗的作品(在“国际诗歌网”上),感到非常震惊,立即被他那出乎文化意料的诗作给迷住了。四年之中,在向布拉达克西书社做出一个成功的推介之后,奥尔德堡将举行伊沙在英国的首次朗诵——他将在他的澳大利亚翻译家西敏的陪同下——并且发布他在中国境外的首部英文出版物。”
在内奥米作介绍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的我得暇望了一眼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孟元勃所说的“最好的”、“最可爱”的观众!该厅能坐下三百人,其中二百五十人是买票入场的普通观众,今晚三位诗人朗诵的票价是14英镑,现在他们满怀好奇满含期待地望着我——望着诗歌节二十年来所请到的第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第一位汉语诗人……
接着是西敏讲话,他首先讲到了我诗集的翻译,特别感谢另外一位远在澳洲的译者陶乃侃先生。他还讲到了我的签证问题,台下的观众笑了——对他们来说,包括英联邦和欧共体国家的公民而言,签证也能成为问题?确实是可笑的!
然后朗诵便开始了。
这种形式包含了内奥米、西敏和我三人的意见:西敏先用英语报出诗名——譬如《车过黄河》:"Crossing the Yellow River";然后再说上一两句导读语——譬如:黄河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母亲河”,相当于泰晤士河之于英国人;再然后,便是我的中文母语朗诵;最后是西敏的英语译文朗诵。以此类推。
西敏很会选诗排序,让《车过黄河》打头无疑是高招,这既是诗集中我最早的一首诗,也是我最具标志性的一首诗(此时此刻我无从知道:就在同一天晚上,在遥远的祖国,该诗当选了深圳《晶报》评选的“30年30首诗”,后来又被影响更巨的新浪网读书频道评定为改革三十年十大“流行诗歌”),事实上这首诗在2004年昆明举行的“中国-北欧诗歌周”的朗诵中已在异国同行面前经受过检验,瑞典著名诗人斯蒂格嘎嘎的笑声犹在耳际!这一次,当我读完中文原作的时候,只听台下观众中喊出了一声汉语的“好!”——很像是京剧观众的吆喝声,那一定是孟元勃喊出的,台下的观众都笑了——轮到他们真正的为诗而发笑,是在西敏朗诵英译文的时候,在《车过黄河》的尾声,他们这一笑,我心里已经有底了。
紧接着上《结结巴巴》也是很对的——这首曾在去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开幕朗诵中大放异彩,也是我最有把握的一首,今晚的情况是:我朗诵中文的时候,观众就笑了,因为结巴,仿佛RAP。西敏朗诵英文的时候,他们就笑得更厉害了,搞得我也偷偷想乐,因为西敏对结巴的翻译和模拟都很到位,朗诵起来比我更结巴!
第三首《假肢工厂》:如果我的记忆无错的话,此前我从未在公开场合朗诵过该诗,是西敏把它选进来的,效果竟出奇的好,观众的情绪完全跟着诗句在走,在该有反应的地方全有反应,我想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是一首标准的“现代诗”,写的是异化内容,用的是荒诞手法,充满现实感,又具有超现实的味道。
第四首《星期天》的情况与上一首类似:从未朗诵过,是我自己将它选进来的——当时我看到诗歌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介绍我的时候选的是它,果然,现在它被印在诗歌节专印的小册子上,观众手里边有,可以对照着听。效果又是出奇的好,因为观众有文化——在对梵高、高更了解的深入上,非国内的读者所能比,还有一点: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喜欢!
趁西敏朗诵英译文的时候,我喝了一杯水,是因为在朗诵到上一首诗的结尾处,感觉喉咙有点干、声音有点涩,我这次的嗓音状况不如去年在鹿特丹的时候,是因为来之前去太原参加《语文报》的社庆活动,一不小心感冒了,到英国才刚刚好。还有就是,此次是和朋友在一起,说话多,费嗓子。
第五首《1972年的元宵节》是我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这是我作品中少有的一首玩意象与意境的超现实的“纯诗”——我想把这样的一首诗选进来,会取得意外的效果,也能向异国的同行们展示自己的功力。此诗写得静,也赢得了静!
第六首《等待戈多》是注定要赢得欢笑声声的:取自于西方的文化典故,又作了一番富有中国特色的恶谑。结尾处观众爆笑。我读之前,有个插曲:我忽然找不到这首诗的原文了——其实下午在酒店的房间里做准备时我就没找着,竟然忽略了,我急出了汗,端着青海人民版的《伊沙诗选》走到麦克风前,在开读前的最后一秒钟,才翻到印有此诗的那一页!
第七首《中国人的清明节》是我本来就选了的,是我对中国人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示与阐释,我不是文化符号贩子,我写的中国文化与当下有关与日常有关与吃喝拉撒有关,既不粉饰美化,也不故作姿态地做出一番浅陋的批判——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诗人起码应有的尊严!
说起第八首《自杀的小孩》,我首先应该感谢我优秀的译者西敏,2004——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二年,他最先翻译的我的十首诗中就有这一首,作为“国际诗歌网”的编辑,他在一篇评介我的文章中还特别评到了这首诗,让我在多次重读之中发现我自己对它认识不够——现在看来,这是一首被我自己忽略掉的力作!此时此刻,观众的反应先是震惊,后是爆笑,可谓“又惊又喜”——我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惊!内奥米所说的“惊世骇俗”的“惊”!
对于第九首《诞生的秘密》,下午我在西敏的房间小坐时曾有过犹豫,我问西敏:不会有小孩在场吧?前两场好像没见着(但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有孩子们在场的照片),因为这一首写到了孩子,但并不适合孩子听——
小时候我问父亲
“爸爸
我是怎么来的”
父亲回答说
“我吐了一口痰”
我记住了他的话
记住了这个有关
诞生的秘密
后来是儿子问我
“爸爸
我是怎么来的”
我也回答说
“我吐了一口痰”
我想起父亲的话
想起当年的他
不曾糊弄我
可是我的儿子
没有当年的我
那么朴实
听完我的解释
他立刻跳了起来
大着嗓门嚷嚷
“我们老师说了
不许随地吐痰!”
台下的观众笑疯了。与他们前面听到的那些庸俗浅薄的性玩笑相比,此诗可是太高级了,直指“生命的真相”——对了,西敏就是这么译的。
在读最后一首之前,我抬腕看了一下表:快到30分钟了——也就是说:我们略有超时,但我们毕竟是双语朗诵,容量折半,大家定会谅解!西敏的选诗之妙还体现在这最后一首《交流》上:
在奈舍的湖畔公园里
黑头巾包不住她的美丽
一位荡秋千的阿拉伯妇女
我走近她的时候
她开口和我说话
用的是英语
我听岔了
以为她是在催我远离
催一个无事可能
生非的男人
尽快远离
我正在迟疑
却又听明白了
她的后两句
她是在问我
荡不荡秋千
意思是她可以
让给我玩
我真想走上前去
搭把手
加点力
把这位荡秋千的
阿拉伯妇女
荡得更高一些啊
但想了想
又决定放弃
此诗首先感动的是正在读它的我!我确实是个“有话要说”的诗人——以上便是我对今日之世界想说的要紧话!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诗人们接二连三地撰文倡导所谓“中国经验”的时候,我已在“世界意识”的写作实践中走到了远处与高处,这就是我的特点:不理论,埋头写,出文本!我甚至有点感谢毛泽东,他教育我们那代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这种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被我用在这儿了……
当西敏朗诵完它的英译文之后,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将我俩送到了台下,在掌声中我向观众(我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最可爱的”的观众)鞠了三次躬——是一种不落幕的谢幕,我感觉自己都有点快像日本人了,这长时间的掌声才渐渐停止……
内奥米说:非常精彩!以前的中国诗我读不懂……主人的满意是重要的:观众满意了,主人自然就满意了。
孟元勃说:你的诗好,他翻译得也很好……同时精通中英文(还有德文)的他是全场惟一一位有资格对西敏和陶乃侃的翻译工作作出评价的人。
美国诗人大卫•科比在五米开外,先是冲我做了个伸出双手到处放枪的动作,然后再朝我伸出大拇指——不需要语言,我已经明白了:他是在说《自杀的小孩》好!
观众们涌到台上卖书处去买我的诗集……等我从洗手间出来,被两个手拿诗集的青年观众堵在洗手间门口签名——结果那里变成我的签名地点,一口气签了十几个。感谢第一名观众教会我签名的最佳方法:先签一个与书上作者名相一致的YISHA,再签一个汉字的“伊沙”,他们觉得汉字很好看……看着他们心满意足的离开,我也感到很高兴!回到场内,又遇到两位中年妇女索要签名,后面又跟了十几个……
签完名,我感到自己很需要抽一支烟,就跑到正门外去抽,在那里我目睹了观众退场的动人场面,看见一个年逾九旬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中,我一次次为老年观众拉门,他们发现是我——刚才台上朗诵的那名中国诗人,面露惊喜之色,要求与我合影……
做一名诗人的幸福感像北海一样汹涌澎湃。
在走回酒店的路上,还有观众在向我俩道贺,其中一位在赞美我们的同时还不忘批评今晚朗诵的某个诗人,看来“最好的”、“最可爱的”观众也是有好恶并且要表达出来的……此举加强了我近年以来的一大悟性:我追求做得好,是因为厌恶做得差……
回到房间我更加平静。对于今晚甚至不做回味。一切都是预料中的。西敏将我的自信总结为经验积累——此话并未触及本质:我知道“深通人性”、“直指人心”的好诗长得是什么样子!从今以后就更知道了!
七
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上午到中午,我和西敏还各有一个节目,需要连续作战。
西敏说:早餐应该多吃一点。
早餐时,诗歌节的专用摄影家皮特来找我们,说是要给我拍照。我早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事实是:从我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就盯上我了,端着他的大炮筒,在多个场合抓拍我的镜头,连我在银禧厅外抽烟的样子都没有放过,听西敏讲:他是英国有名的摄影家。我感觉他那白发飘飘风度翩翩的样子,更像一个指挥家。
早餐后,我们仨一起去到海滩上布里顿的纪念钢雕前去拍照。
十点钟,等我们来到镇中心的电影院,正好接上西敏的讲座。讲座被安排在电影院二楼温暖的小厅里,来了有四十多个观众,都是花了7英镑买票入场的——西敏讲座的题目叫《诗在中国》,公开印在小册子里的节目表上——也就是说:这些观众都是冲着中国诗来的。为了给我的“亲密战友”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我坐在头一排,开讲前西敏问我:伊沙,你能把“关关雎鸠”那首诗当众背诵一边么?我随口背了一遍,说没问题。看来,他要从古代的传统讲起。到底是昆士兰大学的职业教师,西敏滔滔不绝讲得非常专业,观众也听得很入迷。中间,孟元勃貌似抬杠的插话也搅活了气氛。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西敏很正确地给观众留了提问的时间,看着观众那么认真地就中国诗的问题向他提问,我作为中国诗人一时感慨万千:一个澳大利亚人不远万里来到英国,向英国的观众宣讲中国的诗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我还是那句话:汉学家不完全是“老外”,至少有一半是中国人,他们像爱着好吃的中餐一样爱着中国的文化!爱着中国的诗歌!
讲座结束后,一个谢顶的记者要采访我们,要对我俩做个录音采访,他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有点挑战性:是说昨晚朗诵的《结结巴巴》那首诗是否有讽刺残疾人的嫌疑?我的回答是:我写作当时没有这样的企图,现在读了也不觉得有。我还举了一个例子:我的一首诗(《阳萎患者的回忆》)因被认为有讥讽犹太人的嫌疑,那家发表它译文的澳大利亚英文刊物从此封杀了我的所有作品(某个一贯正确的中国知识分子诗人得悉此事十分委琐地说:我们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事实上,我非但没有讥讽犹太人,我还在批判希特勒法西斯对其身心的戕害!我说健全的社会应该对艺术家的创作应该给予更高的道德宽容度——我回答当时没有造出这个词,现在给丫补上:西方文明病——特装B!
距“细读”还有一段时间,我和西敏离开电影院,来到镇中心那家热闹的咖啡馆准备“喝一杯”。到了咖啡馆门口,从里面出来的顾客还不忘称赞我俩昨晚的表演,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问西敏为什么诗集中不印上我的中文原作,她并不懂中文却要看原作,西敏觉得她的意见有点奇怪,但还是给她写了“国际诗歌网”的网址,告诉她那上边我的诗是双语对照的。我记得我这本诗集最早说的是出成双语的,后因排版软件转换麻烦而放弃了。在此过程中,西敏给我的意见甚合我心:就是尽量多的收诗,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充分了解你。我老婆也是不赞成出双语的,觉得在经济上亏欠了读者,挺厚的诗集挺高的价码,但只有一半可以读懂。我不知道刚才那位读者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但她的意见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今后再出的话。
这家咖啡馆的生意真是太好了,里头人满为患没了座,我俩只好在门外的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在北海吹来的寒风中喝着热咖啡的感觉,我已在《诗之堡》一诗中写过了,在此不赘。
“细读”节目是在皮特•皮尔斯画廊举行,我们提前赶到那里,在那边主持节目的是诗歌节的副主任,他对我很友好,对我来说他可是在诗歌节发给我的两封邀请函上签字落名的重要人物。我在前面的文字中不厌其烦地提及“朗诵”、“讲座”的门票价格,我知道一些读到本文的中国读者,会对300人的朗诵会和40人的讲座撇撇嘴,做不屑一顾状,仗着自己是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里——那我想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收费,考虑到人均收入消费水平的差距,不说收14英镑就收14块人民币(讲座收7块人民币),还会有几人来听?这里老收观众的钱,我这个中国诗人有点不落忍(因为不习惯),所以听说“细读”节目免票时,我一下变得很高兴,反而想更加认真地去讲,作为对观众的回报。
组织者将我要“细读”的诗印成传单散发到观众的手中——那是威廉•布莱克的《天真
的预示》的英语原文,宗白华先生的中译文如下: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
副主任主持节目,宣布开始。我和西敏同时上台,各拿厚厚的一叠资料,我一看他资料的首页心中便暗笑了:那是我上个月写给他的一封信,全信如下:
西敏兄:
这里是这段时间以来,我在网上搜集到的布莱克的相关资料。
我想“细读”这个节目可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一、 请你先用英文朗诵布莱克这首诗的原文(前四句),我再朗诵中译文的几种版本。
二、 我来做讲解,请你来翻译。
三、 最后,请你再朗诵一遍原文。
我的讲解部分会涉及到以下几点:
1、 布莱克的这首诗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情况,我会提到资料中上海地铁对它的展示。
2、 布莱克为什么会在中国的同行与读者中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喜爱?一首130多行的诗为什么会被翻译者与读者留下四句来传播?在这里我会从两个方面分析:(东方)诗学、佛学。
3、 这首诗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笔名“伊沙”是从祖父起的名字“一砂”谐音而来的,在我诞生的“文革”那年,祖父一定没有读过布莱克,但他一定知道“一砂一世界”的佛语。
4、 总结起来:一个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近现代浪漫主义(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诗人,却用现代诗歌的形式说出了佛语,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它说明:文学艺术与宗教的相通性,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通性。这个结果当然更能反证出布莱克的杰出,是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因为他像佛陀一样说出了真理。
情况大致如此。
至于讲解方式,我会沿用自己的讲课和说话方式:深入浅出,绝不引经据典,翻译起来不会太难。这些资料,你浏览一下即可,不必细究。
祝好!
伊沙
2008.10.6
信末的日期提醒我:给西敏写此信正值我首次申请签证遭拒签再次申请尚未去的那段时间,尚不知最终能否成行,却有着如此认真细致的准备,在一瞬间里,我有点被自己的执著所感动……
但此刻却没工夫感动。我要给观众讲讲布莱克。
此信也是提纲。我就照着早就想好的思路在讲。
讲一段,西敏译一段。
有一段讲多了,西敏就打断我,惹得观众发笑。
观众真是太好了,我每讲一段,他们脸上都有掩饰不住的兴奋表情。
我注意到美国诗人夫妻双双到了,坐在观众中——他们真好!
一刻钟的时间转眼就到了,该讲的差不多都讲了,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时间请西敏领着全场观众将《天真的预言》齐诵一遍——那是我们事先想好的绝妙尾声!那会是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可惜未能实现!
“细读”结束后,皮特又在现场给我和西敏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女司机用车将我们带到“诗人之家”吃午饭。
这天中午,“诗人之家”很热闹,餐桌边坐满了诗人,已经没有座位。我端了一盘鸡肉米饭,坐到隔壁客厅的沙发边用餐,其间,爱尔兰诗人丹尼斯和美国女诗人芭芭拉先后坐过来称赞我的诗,后者用到了“力量”一词,可惜我有限的英语不能与之作深入的交谈,而西敏正在与别的诗人交流……
我的毛病是一吃饱就晕饭,便不辞而别地回白狮酒店睡午觉去了。下午还有三位诗人的朗诵,我已没有精力去听了……
八
告别从晚上开始。
其实下午就有人走了,那个有点男孩气的青年女诗人已经提前返回伦敦去了。
八点钟,“诗人之家”有个闭幕晚宴,我和西敏准点到场,发现里面已经人声鼎沸济济一堂。几乎所有的诗人与诗歌节的工作人员都聚在这里。正式邀请来的诗人都坐在餐桌边,有点正襟危坐,还在讨论着什么,工作人员和一些有点陌生的面孔都在隔壁的客厅里,沙发上地板上坐得东倒西歪非常随便——我选择了这一边。
有红酒、啤酒和蛋挞、布丁之类非常好吃的甜点,我取来一些。皮特的太太是两位厨娘之一,她是葡萄牙裔,正宗的蛋挞便是她的杰作——她特别提醒我要享用她的杰作,我告诉她我已经吃下两块了,她听了非常高兴。
有位中年妇女,也是诗歌节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我的诗——不仅仅因为她告诉了我,是我在气氛中明显地感觉到了……我说不出更多的话,便主动提出与之合影留念。
副主任、还有皮特,大声叫着我的名字——也没什么事儿、什么话,就这么叫上一声,表示一下:我们是哥们儿!奥运会一办,搞得人人都会说汉语的“你好”——发音则千奇百怪,要多怪有多怪,笑破我肚皮!
那几张陌生的面孔十分年轻,像是“80后”——我猜测他们是“新声音”那个单元请来的诗人们。诗歌节正式邀请的22位诗人年龄都不小,1966年的我在男诗人中要算第二小的。于是便给年轻的诗人们另辟了一个单元,可惜我无暇去听他们的朗诵。其中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特有意思——
那个女孩会说极少的一点中文(肯定比我会说的英语还要少),但她却在顽强地说着(真值得我学习),一个词想半天才能蹦出来,她给我写名字时,我发现她芳名中间有个VAN,就问她:你是荷兰人吗?她说:我爸爸是荷兰人、妈妈是英国人。她告诉我:在中国诗人中,她喜欢韩东,她在2006年的鹿特丹诗歌节上听过韩东朗诵。我告诉她:韩东是我的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到门外去抽了一支烟,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我们边抽烟边聊天,一个长得像中年金斯堡的男孩过来了,将一瓶喝了一半的意大利啤酒非要塞给我要我喝,盛情难却,我就喝了,然后我俩用英语好一通狂聊,我感觉他的发音有点怪,不大规范,但是却说得很溜,到后来,他竟然对我的英语水平大加赞赏,说我应该说得更多一点。抽完烟,我们几个又回到屋子里去,聊得更加热烈,我告诉他:你长得像金斯堡。小哥们儿听罢,做出特愤怒特绝望的表情说:我长得像垃圾!——这哥们儿是在诗歌节上所见到的诗人中最像诗人的一个,人的状态很high,我很想知道的是:这些年轻的诗人们在写什么?从小册子上看那22位“正式代表”的简历,职业几乎全是教授或大学教师,一方面说明大学是能养诗人的地方,另一方面就存在着一大问题:他们是我这种对教授和学院充满警惕与自我批判的人么?还是以为知识多就有优越感并为此而沾沾自喜的“知识分子”?我还有一个发现:他们中很多都是移民(尽管是用英语写作),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上述各堆的交流活动,都是伴着美妙的音乐进行的——这音乐出自西敏的吉他弹奏和苏格兰诗人格瑞•卡姆布瑞格多种乐器的吹奏,后者是个吹奏能手,正如我在《诗之堡》诗中所写的:“苏格兰高地来的诗人/未穿裙子/擅长吹奏/他像变戏法一般/变出了随身带来的所有乐器/逐个吹奏它们/都能吹出风笛的味道/将所有的曲子/都吹成了天籁般的《一路平安》/吹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吹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吹得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把离情吹成了爱情/把爱情吹成了伤情……”——这种特别小资的沙龙场景,如果移植到中国去,就会显得很酸很装B,但是在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美好,叫人心旌荡漾,陶醉其中而无法自拔!真是什么土地长什么东西!
每个人对于别人对他的态度都是敏感的,但有时候却未必正确,我刚想到:这个格瑞可能不喜欢我的诗,从第一晚的见面开始,他就没有跟我说过任何话……西敏却告诉我:格瑞买了我的诗集,他想请我签个名……话音未落,格瑞已经拿着诗集过来了,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诗人,吹奏是他与大家在交流!
诗歌节的老主任也坐过来与我交谈,我向这位奥尔德堡诗歌节的创办者请教了两个问题:一、奥尔德堡诗歌节是不是英国历史最久的?他回答说是,他说伦敦还有一项比较久的诗歌节,但是双年一届的。二、我是不是奥尔德堡诗歌节邀请来的第一位中国诗人?他回答说是,他说他们以前还邀请过东欧的诗人。我笑了,看来中国和东欧是一类的。
后来,我去上洗手间时,看见内奥米正在门厅与人交谈,便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与她告别——我的方式是不提“告别”二字,过去跟他们再热乎一阵子,照几张合影,然后兀自隐退……内奥米,希望你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哑巴在跟你告别!希望有一天,你能读懂我留在送你的诗集扉页上的那一行漂亮的中文题字:有缘千里来相会!
走到门口,借着路灯的光亮,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十点多了……再见,“诗人之家”!
第二天吃早餐时,已经看不到任何诗人了,我和西敏吃得很慢。十一点,会有人来送我们去据此最近的萨克斯门德哈姆镇的火车站,搭乘开往伦敦的火车。我想买一只船模带走,带回西安去装饰我的新家,但卖船模的那家店十点半才开,所以在早餐以后我们还有时间再去看一眼美丽的像梦一样的奥尔德堡小镇。我俩在周一早晨空无一人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转着,无意之中竟走到了基金会的办公室,透过窗玻璃看见他们坐了一圈正在开会(估计是总结会吧),我们只好进去再向主人道一次别——一步跨入温暖的屋子,竟然踩响了一片掌声——他们全体起立为我俩鼓掌,于是便寒暄一番,再次道别,离开时透过窗玻璃,还在挥手……
西敏说:我们有点太受欢迎了!
我说:是啊,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西敏说:本来已经告过别的。昨晚,我十一点才回来,路上已经没有人……
我说:你肯定告别得很充分,我知道你们西方人的告别是很仪式化很繁琐的。
西敏说:咱们怎么转着转着就转到了这里?没说要来啊!
我说:这就是命!命中该来!包括刚才我们走到银禧厅的背后,看了一眼曲终人散后空旷的大厅……
——这是此次英伦之行中我第一次说到命,第二次说起时已在伦敦——那是在伦敦三日中唯一一段与诗有关的旅程:诗歌节的另外一位女司机最后送我们上火车的时候,送给西敏一册非常详细的伦敦地图——正是在那册地图上,西敏查到了布莱克的墓地,他说:我们的诗之旅应该在那里结束。正好我也是一个喜欢仪式的人,于是便去了——
这是一个冬阳暖暖的上午,我们先步行走到头天曾来过的圣保罗大教堂,在其附近有一片看似普通的公墓——一身黑色装束的上班族赶着匆匆忙忙的脚步从中间的小径上穿过,我们走进去,最终来到一高一矮相对孤立的两个墓碑前,其中高大的墓碑是小说家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的,矮小的墓碑则属于诗人威廉•布莱克,布莱克的墓碑上写着:此处躺着一个人的骨头和灵魂。我们没有带花,我将一支点燃的香烟放在布莱克的墓碑顶上,等它燃尽……
后来,我们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我再一次说起命:这就是命,让我们“细读”过的布莱克来结束我们的诗歌旅行。我还说到:金斯堡肯定来过这里,身为美国人,他到英国很容易,来英国必先到伦敦,不会不来拜谒他私自认定的诗歌导师……
我话音未落,墓园里一个巨大的橡树枝上忽然飞起了一大群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在我们头顶盘旋了一圈,向着伦敦少有的晴空深处飞去了……
我说:我们感动了布莱克,他显灵了!
西敏没有直说,但他肯定是在认同我的说法,他说:在他做《诗在中国》的讲座的时候,他提到有一本书,介绍了一百种敲钟的方法,他在讲敲钟的方法与诗歌写作的关系,这时候,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观众发出惊奇之声……我想起这个细节来了,当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作此反应。
2008年11-12月
转自诗生活伊沙专栏: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art&id=50722&str=1268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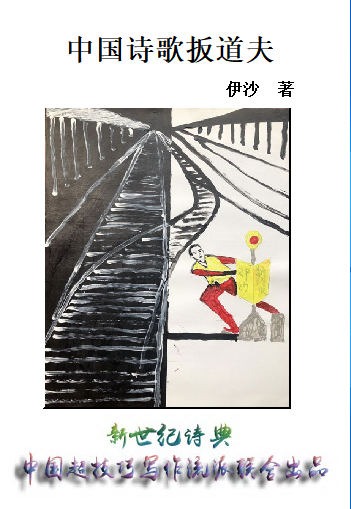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