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发:困境与特例(节录)创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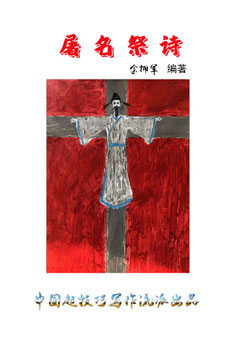
困境与特例(节录)创作谈
文 / 陈先发
我愿意给出一个最直白的阐释:诗,本质上只是对“我在这里”这四个字的展开、追索而已。对于诗,没有任何准则是必须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个排比句式,可以像风中的涟漪,无穷地铺展下去,诗所掘取的,也正是不竭的可能性本身——它永不会遭遇一个“不可以”。而就写作者个人,只需往“我在这里”四字之后,附注上不同符号:问号、破折号、省略号、感叹号、句号,大致就可传递不同写作阶段、各自境界的微妙之味了。诗,因为发乎性情、又无法定义而成为一种永恒的文体。这些年,我听到的最无知又哗众取宠的说法,就是“诗歌死了”。
“我”和“这里”,不断往对方体内注入某种复杂性。一个伟大的诗人,天然地要求自己理解并在写作中抵达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抵制、和解。概括地讲,中国古典诗歌系统有个显见的缺憾,即对人本性的光影交织、对个体心理困境、对欲望本身的纠缠等掘进较少、较浅。或者说,多数时候,仅仅将这种掘进,体现为了一种“哀音”。对“我”与“这里”两者的质疑、冲突,呈现得远远不够充分。哪个时代的人能逃脱掉这种质疑与冲突、矛盾与变形呢?我相信,在所有时代生性多敏的诗人身上,这种撕裂都会有,而且会有许多歇斯底里的时刻。只是古人所谓修身,讲求的是祛除这种质疑与对立,而非是去理解它、表现它、加深它。似乎山水真的能够缝合一切。我觉得这种状态下所获得的超越,其实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臆想中的超越。诗歌作为一种心理行动,本该拥有的混沌、复杂、不可控的内在酿变过程,在写作中被弃置了。
所以,当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年)说“旁观他人之痛”、世界每一角落中他人受刑的镜像会“像照片一样攻击我们”时,我在想,这正是“这里”对“我”发起的一种攻击。我们何以产生被攻击感?因为我们身上,储存着无比充沛的对普遍性正义法则、良知和美的感受力,对爱的感受力。惟此感受力,才配称得上是艺术的源头。然而吊诡的是,真正的艺术,永不会诞生于这种攻击处在最大强度之时,诗也永不会站在情绪的峰傎上——因为人在应急中,无法到达艺术创造所必须的高度专注、高度凝神状态。由此,我们不妨认为,诗,本质上是一种回声、反光、余响。或者说,是一种偿还。是“这里”之锤砸过“我”的磬体(或者正相反)后、因撤离而形成的空白,被低沉回声渐渐占据的状态。是疾风拂过湖面后,涟漪向远处无尽移动的状态。是影子向光源追溯,在我们心上构筑起的光交影叠的多空间状态。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桑塔格再往下掘进一层:不仅“我”与“这里”可以互相发起攻击,“我”对“我”本身也会发起攻击——这才真正是困境的起源,也是艺术的根本。2009年8月7日下午,我父亲崩逝的临终一刻,我跪在他的轮椅前,紧攥着他干枯的手,在他瞳孔突然急剧放大、鲜血猛地从鼻中眼中涌出的最后一瞬,我的内心处在被攻击时的瓦解状态中,此刻是没有诗的。我纪念他的诗,全部产生于对这一刻的回忆。换个说法,我父亲要在我身上永远地活下去,就必须在我不断到来的回忆中一次次死去。而他每一次死亡的镜像,都并非简单的复制,因为对应了诗的创造,这镜像自身也成为了一种创造。诗,在对遗忘的抵制与再造中到来,是对“现实存在物中不可救药的不完美”(普鲁斯特语)的一种语言学的补偿。
或者说,现实存在物中有着完美的不可救药。扎加耶夫斯基(1945——,波兰诗人)说:“你必须尝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他所讲的残缺,本质上不是世界本身的残缺,而是我们认知的残缺。在“我”与“这里”的关系上,显然,桑塔格的“攻击”一说,比我们耳熟能详的石涛(1642—1708年,画家)“笔墨当随时代”,更为精辟、有力。一个“随”字,令“我”在“这里”前,显得过于被动与疲弱,也缺乏我上段所言“偿还”的意味。
不论是“我”,还是“这里”,它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各自困境中。对于“我”,一个伟大的缺憾始终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写作者:即他们竭尽全力地在阐释诗是什么。面对存在,再强力的诗人也会发现自身的弱者之境。无论怎样的阐释,听上去,都无异于一个弱者的自我辩护。事实上,阐释得越清晰,把诗的边界描述得越清晰,笔下的丧失也就越多。哪里有什么界线?甚至在所谓“非诗”与“纯诗”这些概念间,划条白白的石灰线,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笑谈。最终,即便是诗人,也会带着对诗的无知而死去。如果说写作的本质,正是企图以言说的方式突破言说的边界、抵达无碍而自在的寂默之境,那么这个过程的美妙,正在于它是矛盾和充满悖论的,也恰因它包含了抵达的无望、方法的两难、写作者强烈的情感灌注而显得更为动人。写作的有效性正欲体味在这一过程之美、对立之美,而非一个结论的呈现。
正如量子世界和它的“测不准原理”一样——所有诗论,反映的其实是这么一种困境:重要的不是诗人阐释了什么,也不在于那些阐释中是否存在灵光四射的思之矿藏,而在于阐释的冲动生生不息。凡被阐释的法则本质上都是陈旧的,只有这阐释的冲动本身,因混合了生之盲目、词之盲动而永远新鲜动人。
似乎成熟的诗人更乐于承认:一切不凡的写作都与困境有关。这种困境,不是才思昏聩、笔下无以为继的烦恼。它跟枯竭无关。我在《菠菜帖》一诗中有句:“我对匮乏的渴求甚于被填饱的渴求”。没有哪个时代,是什么最好的或最坏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独一无二的困境,等着被揭破。一个平庸的时代,平庸就是它最大的资源。当平庸被捅破,它所蕴含的力道,甚至比另一些时代的饥馑、战乱、暴政所蕴含的更多。以诗之眼,看见并说出,让一代人深切地感受到其精神层面的饥饿感——正是一种伟大写作所应该承担的。当你看到的桦树,是体内存放着绞刑架的桦树,你看到的池塘,是鬼神和尺度俱在的池塘,一切都变了。新的饥渴就会爆发。诗是对“已知”、“已有”的消解和覆盖。诗将世上一切“已完成的”,在语言中变成“未完成的”,以腾出新空间建成诗人的容身之所,这才是真正的“在场”。我们这个时代,为诗人提供了一个幸运:当科学洞微烛暗,结束了世界原有的神秘性之后,又以在量子领域的新探索靠近了新的更强大的神秘源——世界的神秘性,成了唯一无法被语言解构的东西,也因之而永踞艺术不竭的源头。
当然,完全有必要将诗之思,与哲学之思切割开来。我们不能将一种揭示时代困境的诗歌,归结为思考的结果——或者说,诗之感受远胜于诗之思考。诗的肢体必须是热的,哪怕它沉睡在哲学冷漠、灰色的逻辑系统之下。诗的腔调,更接近于孔子将其从《诗经》中删掉的那些“怪力乱神”的腔调。它时而清晰,但它本质上不清晰,它保留着人之思在原始状态的恍兮惚兮。以此恍惚,而维持对纯粹哲思的超越。也以此恍惚,偶尔获得神启,向着我们这个时代因诸神缺席而造成的空白中弥漫过去。
转自潜溪文学:http://www.qianxiwenxue.cn/qxwx/vip_doc/5570879.html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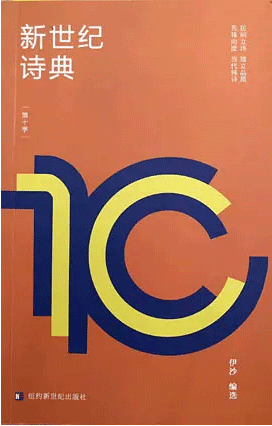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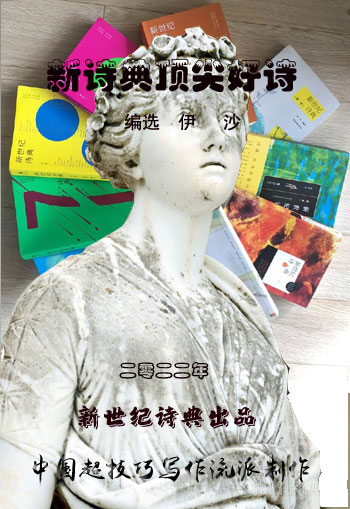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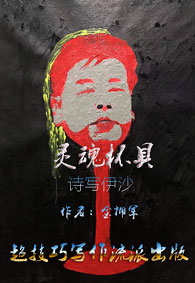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