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失语与命名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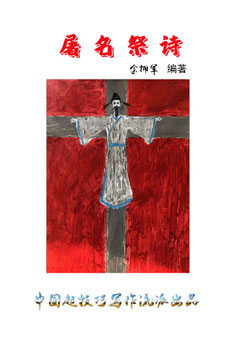
失语与命名的困难
作者:谢有顺
写作,是一种命名,一种呈现世界图景的精神方式,同时,它也是对真实的一种艰难确认。我们可以在作家与世界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触摸到一个时代或一代人的精神状况,原因就在于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贯彻着这种命名、呈现、确认的努力,它使作家在以前的时代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然而,写作到了二十世纪,真实与命名都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与作家认识世界的信心有关。由于一系列内在与外在的精神悲剧对人性光辉的粉碎,大部分作家认识世界的眼光变得极其灰暗(它从卡夫卡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没有信心再说出任何有崇高价值的事实,文学完全失去了颂扬的力量。一些作家转而表达颓废、游戏、黑暗的精神经验,沉湎于毫无盼望性的生活图景当中,写作成了一种哭泣。他们在世界面前没有信心,意志消沉。
这决非小事,它首先表现为作家对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失去了信心。这个世界是物质主义的,非理性的,缺乏明朗的秩序,是难以把握的。于是,作家或者认同这种物质的或非理性的现实,或者将这个世界解释成迷宫,在一种智慧的限度里出示自己的无力性。一旦作家不以信心的方式接触世界,世界在作家眼中就是模糊而散乱的,它无法结构和再现。这种世界秩序在作家眼中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一段时间来艺术秩序的混乱,如,一些作家长期湮没在非理性的否定与狂乱的文学游戏中而乐不思返。其次,失信还表现为作家对自身失去了信心。作家在写作中必须面对人类,面对基本的人性景象,在自我存在的自觉上,出示自己的人学立场。艺术世界与我们的生存世界是互相映射的,人的精神到了什么程度,外面就有相应的艺术诞生出来。卡夫卡有了像虫豸一样脆弱的体验,才写下了《变形记》、《地洞》这样的小说;毕加索有了人被现代文明技术割裂的深刻感觉,他才启用立体法则来作画。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史,事实上是人自身颓败的历史,正常的人性在作家眼中已经瓦解,他们亲见的更多的是人性阴暗的一面。在人面前失去信心之后,作家就必须转身来到非人性的领域里,以获得一个向自身逃亡的空间。这也就是当下的文学越来越不注意从人出发来洞察世界的根本原因。在我们这个技术主义时代里,人的存在正受到许多非存在物的威胁,人在世界里的存在地位,不断地被语言和技术理性所取代。写作中人本与文本之间的错位,就是作家对人失去了信心后的产物。
然而,写作并非简单地表达人或表达世界,它更重要的是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如同加缪说荒谬不在人,不在世界,而在人与世界之关系上一样,文学的失信也是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人接触世界的理由、方式和根据。人接触世界很难再以人为根据,因为人是绝望的,人性的正常标准早在卡夫卡那里就已经死去;人接触世界也不能以世界为根据,因为世界是非理性的,带着堕落与罪恶的性质。那么,在人与世界之间,一定还有一个新的标准来审视人与世界的悲剧处境,我们把这个标准称之为终极实在,它是人与世界原初的规范,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和解的唯一根据。作家的写作首先是以信心的方式企及终极实在这一目标,然后才能以信心的方式描绘出人与世界的基本图景,并不致迷失其中。
终极实在所代表的正是信心所需要的神圣事物,如圣洁、公义、高尚、光明、爱和最高的善等。信心不可能建立在恐惧、绝望等黑暗事物上,也不能建立在日常性的形而下事物上的,它只能建立在神圣事物上,因为神圣事物能给人的存在一个本质。当信心接受了这些神圣事物,就可以在信心里生出盼望来,而后,在盼望中就会产生出一种悲悯与爱的情怀。悲悯与爱正是有使命感的作家共有的写作态度,它贯彻出来的是作家的艺术良心。中国作家在这点上相当缺乏。当悲悯与爱这盼望性的一维缺席之后,作家就只能同那些绝望、阴暗而潮湿的事物平面生成、同构在一起了,自然,由此派生出来的价值态度也是绝望的,充满无意义感的。
一旦作家无法用信心的方式肯定一种神圣事物时,他也就无法为人存在地位的确立找到一个终极标准。这时,自我的有限存在就无法与人类的普遍性的存在发生冲突,当下的在与我的在也无法相联,于是,与存在有关的事物都被下降到非存在的领域来展开:写生存成了写生活的遭遇,写精神成了写情感的一咏三叹,如此而已。在这样的作品中,只有固定的死去的现实,缺乏的是现实内部所具有的活力与精神警觉,以及将这种现实转化成新的存在、可能性的存在的能力。
这也就是表明,作家在存在面前失去了命名的能力。命名能力的丧失,正是作家失信的一个严重表现,他无法再有效、准确地把握对象。一个作家的全部困难,就在于他必须以自我的方式来确立自我的存在,在一种自我循环里面,试图作出一种假想的命名,这让人想起一个人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比喻。在作家与对象之间,因着有一种命名与被命名的关系,于是,就产生了写作。命名(写作)是一种创造,它可以使命名者与命名物有效地分离开来,为命名物的存在作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定位。然而,命名来自于信心,而信心则来自于正确的理性和对神圣事物的肯定。神圣事物一缺失,就失去了命名的内容,像当下的一些小说,只有调侃、讽喻、奚落和自嘲,只有低俗的感叹与肉身生存的烦恼,作家已消失在对象当中,根本谈不上命名;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作家知道有一种人类生存所不可少的神圣事物,也有一种想企及它的愿望,但因着他无从获得命名的能力,使他能从对象中有效地分离出来,那些神圣事物便成了他的幻想与乌托邦。
在这样一种失去了命名内容与命名能力的写作困境面前,作家面对这个贫乏的世界几乎是一筹莫展,这时,他就必须创造一种艺术现实作为无力表达生存现实的代偿,在虚构中来亲近一种假想的现实。许多作家所择定的历史与语言的乌托邦,就是逃避现实压力的两条重要途径,这种艺术现实的真实性只存在于作家的观念中,它在叙述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找到终极价值的作家,是宁肯相信自己的叙述,而不愿相信现实的。作家在写作中沉迷于追忆,冥思,玄想,都是无法对现实作出满意的倾听之后,所渴望实现的一种代偿:试图创造一个世界图景,以反抗那个无法确认的客观的世界图景,并通过假设来接近一种世界真实,它是世界本质失落后每个说话者都要面临的隐蔽的困境。
失语是作家失去命名能力后的一种结果,它在当下的写作中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停止写作,我们注意到有许多作家走红几年后就一言不发;二是继续进行失语的写作。在这种失语症面前,写作又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闲谈,表明说话丧失了中心内容。海德格尔将不着边际的闲扯、流言蛮语、包打听、疑神疑鬼、见风使舵等,看作是闲谈方式的具体内容,其突出特点是非本真的日常生活对本真生存的蛀空与替代,像一些过日子小说家所表现的那样,写作成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闲谈,对存在拒绝作出价值追问;失语之后还继续写作的另一种形态是:聒噪。聒噪是言说无法触及对象的一种无意义的言说行为,是能指与所指滑脱之后制造语言泡沫的写作方式,它只出示意义的空构。北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聒噪者说》的小说,就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失语后的困境。人在语言面前失去了主体地位,语言自身的明晰性与统一性遭到了瓦解,人在言说的时候,却被语言所变乱,价值感建立不起来,言说方式便成了作家唯一可以用力的地方。当一个作家无话可说了,却还要将这种无话可说的境遇说出来时,这是最大的荒谬与痛苦。
闲谈是对世界的失语,聒噪是对意义的失语,这都是命名的困难,而命名的困难就是存在的困难,表明作家对世界、语言和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所以,真正成功的写作,就是重新争取一个终极实在作为信心和命名的根据,并在写作中实现命名者与命名物之间的有效分离。然后,通过命名者(作家)实施对命名物(人或世界)的批判,建立起批判的自我人格,这是写作中的第一次否定;接着,再在对命名者的自我人格的批判上,确立一个高于人的实体存在的写作的中心指向,这是写作中的第二次否定,在这种否定之否定中,写作成了对一种可能性空间的肯定,意义就在这种肯定中出现。这样,就可能在命名里达成和解,这种和解既不偏向前者也不压制后者,而是出现了第三者——对命名者的命名。前二者是说与被说的关系,属现实的维度,第三者则属于为何说与为什么说的范畴,是在意义的维度上,只有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才是完整的。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杰出的才华,如博尔赫斯,他在解构的同时,也出示了一种新的结构,意义的维度就是建立在这种结构里面。
强调信心的建立,强调对神圣事物的肯定,强调对存在的价值追问,将一种有立场的否定力量贯彻到底,以重新获得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新时代的写作。也只有这种写作,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突破当下因失信所致的失语的困境,亲见一个新的写作节日。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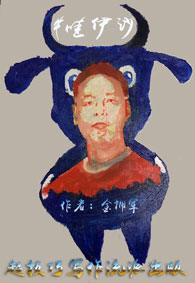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