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创造传统 —话说伊沙 》——于坚

在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诗歌体制中,要否定伊沙这样的诗人很容易,并且可以由此获得“诗歌正确”和道德的优越感,甚至可以拉近你和海子这样的诗人的距离。但是,要肯定他却需要勇气和创造力,伊沙的诗不仅是对体制化诗歌美学的挑战(我指的不是文革时代已经死亡的诗歌体制,而是最近正在中国大学与全球化弹冠相庆的现代派诗歌体制,这个新体制的合法性从未被怀疑过。)也是对正人君子的道德感和意义系统的挑战。承认他,你必须把自己的阅读趣味置于一片荒野之上,在此地没有诗歌美学的安全灯为你照亮道路,你必须自己独立对诗或否做出判断,它考验的是你的阅读趣味的生殖力,与海子式诗歌不同的是,在那里,你会获得找到队伍回到高雅的美学之家的幸福,在这里,你受伤、受辱,流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霸道的诗人的很难苟同的世界观,也是他粗鲁地呈现在你面前的身体。此时代文化氛围的虚弱就在于,遑论尊重,它连容忍伊沙的存在的气度都没有,它用腐朽的诗歌教条来攻击伊沙、却总是自取其辱,无可奈何,乘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多年前有一个晚上我在北师大的礼堂目睹伊沙的诗歌朗诵,这个虎背熊腰、肌肉结实的胖子朗诵时整个身体就像一门前挺的炮,双腿微微叉开,身体前倾,每念一首,感觉都是发射了一枚炮弹。激起激烈的掌声或者尖叫。不断有眉清目秀的青年男女愤然离去,用手帕包着破碎的心,用写诗的右手猛力摔门,但总是没有发出那种区待中的愤怒巨响。门一次次软绵绵地关上,那个不争气的门。走掉很多人,但留下来的人热烈鼓掌。这才是诗歌朗诵。我们时代那些可怜的小人物的可怜梦想,不过是在课堂和咖啡店谈谈诗,他们受不了伊沙。有一天伊沙和我说到,金斯堡在某个新年之夜在数万人的广场怎样嚎出他那些令美国学院发誓永不原谅的诗歌,我可以想象那些长得像布什先生的教授是怎样斯文地悄悄揩掉眼镜上溢出的鲜血,怀着永生的仇恨。爱伦·金斯堡死的时候,《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这个老家伙终于死了”。马雅可夫斯基是怎样把他的诗歌砸出去的,那些石头可是一个就是一个,会令人头破血流的。蓝波在巴黎诗坛的绿呢长桌子上,当着那些感伤、浪漫、教养良好的诗歌鹦鹉把他的鸡巴掏了出来。这个名字如果译成狼勃就对了,那些翻译者一定要阉掉它,在法语里做不到,在汉语里可是手到擒来。我从前不喜欢蓝波,就是因为这个名字。狼勃从来没有进入汉语,进入汉语的是他赝品,蓝波。那个夜晚我参加的是中国最牛B的诗歌朗诵会,伊的朗诵总是令我想起今天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发生的巷战,兴奋,已经到了要离坐手舞足蹈的地步。但伟大的“嚎叫”并没有出现,而是“结结巴巴”在激动人心。已经相当不错了,诗人终于可以在他的时代不必借助默许的象征系统,可以结结巴巴地吐出自己深藏多年的舌头了,“与舌共舞,与众神狂欢,与自由的灵魂同在”,不只是修辞学的自由和解放,也是世界观和身体的自由和解放。
伊沙在一个僵硬的意义世界里开始他的挑战,他是一个直截了当地喜欢释义的诗人。这种挑战包括两个方面,摧毁僵硬死板的意义系统,把意义从单向度的死胡同里解放出来。回到原始的意义创造和宣泄的狂欢中去。伊沙的诗是解构的也是建构的。例如《车过黄河》对“黄河”这一僵化的国家意象的解构中,复苏了个人与这条河流的身体关系。例如《结结巴巴》,主流文化对身体的暴力统治被解释为一种个人话语的生理性表达障碍。
二十世纪的西方先锋诗歌的主流是拒绝释义,当尼采说“上帝已死”,他宣告的就是“深度”“逻格斯”“作者”“本质”等一系列西方古典意义系统的末日。在我个人看来,无论卡夫卡的格里高里、海德格尔的“存在”还是罗兰·巴特的解构或者苏珊·朗塔格的“拒绝释义”都是尼采发起的超人反抗物质主义的空心人、塑料人、橡皮人、技术奴隶的大规模统治的现代圣战的一部分,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界。在对“意义独裁”造成的窒息和压抑上,世界各地的诗人颇有同感。解构的愤怒其实来自生命的具体的压抑并非抽象的纸上理论,为什么罗兰·巴特、苏珊·朗塔格的理论刚刚进入汉语,就能够在诗歌界获得知音,就是因为意义的暴力统治乃是生命的悲惨事实。世界各地的诗人面对的“意义”暴力不同,在“拒绝释义”的悲愤高呼后面,站着西方诗人的普遍恶梦——本质主义、深度、逻格斯和交通规则等等。中国诗人的噩梦不同,一方面它是二十世纪拿来的“本质主义”与“诗言志”相结合的“政治正确”的高音喇叭式的抒情狂,文革时代的单向度“意义独白”。另一方面,它将中国古典世界的意义系统全盘摧毁,一张白纸,犹如荒原。最可怕的是,汉语不再表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存在的意义、道德的意义和人的意义。意义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更广阔的意义领域在20世纪的汉语意义系统中要么付诸阕如,要么被泛政治化。“诗言志”的空间越来越窄,最后只剩下令朦胧诗人绝望的、特征为“我不相信”的一志。其后海子(高雅的但是空洞的乌托邦意义世界)、汪国真(“校园青春”式肤浅媚俗的乌托邦意义世界)诗歌的泛滥,表明,中国世界的意义焦虑和渴望有多么强烈。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力量的文化精神之一,“拒绝释义”在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歌中表现为两个方面,其温柔的部分是与道家思想暗合的“诗即废话”,其潜在立场是中国传统的“玩世不恭”,“道在屎溺”,无意义的语言游戏。没有意义的语言从不存在,否则如何界定何者为“废”?“废话”的消极出世态度同样是二十世纪“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对立物。另一方面,则把“拒绝”作为一种立场,拒绝但是要入世。伊沙试图广泛地进入生活世界释义,摧毁并重建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他在这几个方向上出击:有时候,他俨然是一个纯诗作者,他深知攻击对象的不二法门。伊沙式的机智,短平快式的重磅出击(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意义的快感式的转瞬即逝,而且会在记忆里再次重现),语速风驰电挚,直扑核心,杂文风格,无休无止的批判、武断、直截了当、以我观物、投枪、匕首。相对被新潮美学津津乐道了二十年的“朦胧美”,伊沙露骨流血无耻的诗歌一点都不美。谈论伊沙,你必须用那些正确诗歌美学词汇中的贬义词,否则你无法谈论他。在细节上,伊沙诗歌中的观念并非普遍性的所谓真理,是非,而是他个人的观点,个人的是非,他自己发明的意义,有的与普遍价值吻合,有的则不。在一个被单一意义统治因此对意义的创造已经普遍麻木的世界中,他的诗歌振聋发聩。他属于波普时代的诗人,恶作剧般的写作速度取消了诗歌王国的尊卑等级,天才的民主化(丹尼尔·贝尔语)令每个人看到他作品都在诗歌建树上跃跃欲试。这种么,我也可以来一首,令人想起安迪·沃霍的丝网印刷。在诗歌现场,自由诗歌的正常气氛应该是使所有人从天才诗人的作品中获得天才的自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比我做得更好”“每个人都有一刻钟”(安迪·沃霍)但在诗歌历史博物馆中,等级制度,诗歌地位的高低是无法避免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诗经以降,中国古典诗歌一直有着天才民主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今日西方被作为“后现代”热情欢呼。李白的一首《静夜思》,唤起了多少人的天才梦啊。也有曲折,例如宋,诗歌一旦在写作的当下现场贵族化,少数化,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献给无限的少数”,是诗歌的穷途末路。伊沙诗歌出现的地方,意义碎片飞扬,春风吹又生、有的一闪既逝,有的震撼心灵、石破天惊。伊沙的存在是对海子、汪国真和他们的大量追随者为大学和高中一年纪学生准备的正确诗歌王国的严重挑战,当代诗歌教育以接纳这些诗歌为荣,并证明他们可怜的“思想解放”“与时俱进”,但界限到干净、卫生、高雅、博学、正派、天天向上为止。“政治正确”的新标准像贸易协定一样,参照的是美学上的国际惯例。伊沙将当代诗歌的意义疆界扩大到更辽阔的中国经验中去,他的诗歌映衬出那个合法的美学王国的寒酸和假惺惺的崇高感以及藏在“现代派”面纱下的卑微的媚俗。他因此非常危险,或者说,写他那样的诗歌必须在一切方面都豁出去,舍得一身剐。他勇敢地拒绝不朽,他快乐地希望人们把他的诗歌快餐吃下去,哪怕只是带来一个心情愉悦、茅塞顿开或者恶心呕吐的中午。他的诗歌激发的是生理反应,思考的刺激,NO或者YES。诗歌有那么重要吗?一定要穿着晚礼服,在八点半的沙龙里把智齿绊飞的语词游戏?诗歌非常重要,有一回伊沙在某个机场出现的时候,有人要求他把他的诗写在自己圆领衫上,说是伊沙的诗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血性诗人,铁肩担道义,他不只是要当个诗人,他是要获得并向世界散播诗歌之心。
伊沙诗歌的基调是批判而不是怀疑。他来自一个批判一切的时代,而在我看来,否定之否定对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来说,恰恰是最有力和罕见的。诗人们用纯诗来与时代妥协,诗人们自我安慰地相信“象征暴力”与诗歌无关。诗人们共享着“全球化”的各种好出并把自己的诗歌做成锦上添花的“接轨牌”奶油,诗人们绝不敢拿自己的才华与时代和文学史开非诗的玩笑,宁愿在诗歌的象牙塔中,自我戏剧化,在中国矫揉造作的诗歌酒巴里获得一个优雅的蹲位。在我看来,恰恰正是伊沙,而不是那些把“知识分子”写在旗号上招摇的人们,坚持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如果知识分子指的是“没有定则可以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对于真正世俗的知识分子而言也没有任何神祗可以获得坚定不移的指引”,就是“对权势说真话”“不对任何人负责”(引自《知识分子论》爱德华·W·萨义德)。在中国,我相信,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会出现在当代文化以为应该出现的地方,具有如此挑战性和批判精神的诗人伊沙,被诗歌知识视为“诗痞”,正说明这个国家的知识和理解力是多么愚蠢而虚弱。伊沙正是那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诗人,但他对他自己负责,他要创造他个人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不是虚构,而是来自他的身体和心灵对存在的理解,感受。我把1966年的文化革命看成一场灭心的运动,我们的努力正是要重建中国世界的心灵。我们拒绝“站在虚构一边”的死魂灵,并不意味着诗歌就只是废话,只是“到语言为止”的“毫无意义”的空心橡皮擦头。在我看来,今日中国诗歌缺乏的就是立场、灵魂和对人生意义的创造与复活。伊沙的诗歌正是对死魂灵的批判,在这种充满创造力的批判中,诗歌具有了可以尊重的重量。
伊沙诗歌的危险性在于,他总是在非诗的匕首刺刀与纯诗之间创造他的诗歌空间,“有创作能力的人是能在有意识的、令人宽慰的、放心的、文化标准,与无意识、千年岩浆、黑暗、夜晚、海底之间泰然自若的人”。(见费里尼《我是说谎者》)如果这个诗人不是天生我才,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口气和语感、语言和话说到什么程度该转弯、停住的独特机智,他的诗歌就会成为雪莱说的“议会发言”。他是批判的,但不是标语,他是非诗的,但具有非凡的语言魅力。伊沙的天才就在于他唤起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写”的“非诗”的幻觉,却刷新了当代诗歌的标准。在诗歌概念上他是非诗,但在作品事实上,他激发的恰恰是诗才能产生的感动与顿悟。伊沙的诗歌非常风格化,实际上只有他可以这么写。别人无法模仿,他比“废话”有力的地方还在于,我们无法说出,在诗歌上,谁是伊沙第二?
作为诗人,伊沙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正是一个既有个人语言魅力而又可以将这种魅力在纯文学的疆界之外自由驰骋的作家。鲁迅在他的时代倍感孤独,这个诗人气质的作家从未在诗歌队伍里面发现与他旗鼓相当的同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诗歌是贫血的,说它是“花边文学”并不过分。鲁迅的影响经文革被歪曲也更深入,杂文性格造就了一代人。红卫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深远的影响是,在诗歌里出现了伊沙这样的诗人,他的作品不是所谓的纯诗,但也不是杂文,它是一种具有杂文风格的诗歌,独创的、具有魅力的,充满攻击性的和相对于我们时代的诗歌体制——它总是造反的。当然,伊沙的出现与鲁迅时代不同,当年鲁迅在上海呐喊,金斯堡在旧金山嚎叫,而50年后,诗人伊沙只能结巴。从呐喊到结巴,这就是历史。当纯诗提倡者对伊沙不屑一顾的时候,他的诗歌正在丰富改造着纯诗的标准,诗歌是不知道的,谁是纯诗,不是由那些自以为掌握着尺度的国家文学史教材编写者说了算,谁是纯诗?还不知道呢!这是一个“礼失而求诸野”的时代,而伊沙的诗歌,天然就是在野。
我生也早,伊沙还在襁褓里吃奶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昆明街头好奇而兴奋地望着1966。我旁边是失学的少年、小偷、流浪儿、二流子,我年轻时代的朋友将来长大后成为吸毒者、失业者、劳改犯、出租汽车司机、叛国者、会计和工人阶级,我在工厂的同事包括锻工、翻沙工、右派份子,鸡奸犯、造反派、工人纠察队员、国民党将军的二少爷……我的血液里天然与金斯堡的朋友有着血缘关系。回想起来,我与《他们》的联系并不是完全是文学方向上的,有一点,主要是无法忍受的孤独感,拔剑四顾只茫然。1983年,《他们》酝酿创办时,我热烈地取了十多个名字,包括“牛仔裤”“翻毛皮鞋”之类,都是野蛮愤怒粗糙具有戏剧性的自我表现的夸张风格的单词。但最后南京方面用了一个看起来比较清高、旁观、神秘而且温柔的“他们”。后来我得知,这是因为那些朋友都喜欢一部叫做《他们》的英国小说。我是在什么样的人群中成长起来的?听听这些名字,黄毛老大、老和尚、钢水、李猫、瓜、排骨、老歪师、大猪、邱座、匪连长……我怎么会认同那些温柔雅驯的语词,《他们》缓解了我青年时代的孤独。1985年金斯堡来到昆明,就在距我的房间500米的一家旅馆里色迷迷地望着那些陪同他但不知道他为何物的小生,他的身体比他的诗歌更具威胁性。我们的感觉是相通的,如果二十年前,他反抗的是麦当劳式美国文明的暴力,故意和底层阶级混在一起;那么我本来就出身工人阶级,我反抗的是文革暴力。殊途同归,今天我和老金在对席卷全球的物质主义世界的恶心和绝望上已经没有多少距离了。伊沙还没有出现,孤独。我俯首,很有礼貌地向诗歌同行微笑,对那些可以流芳百世的小诗有所保留地表示赞赏,因此给人好大喜功的印象。在早期《他们》里面。伊沙的长安同乡,前黄河机器厂的技术员丁当是一条汉子,我们曾经在陕北高原骑马,在昆明滇池游泳,在文庙门口为朋友兜售舞会的门票,甚至为他批发海边运来的发臭的带鱼,度过了许多心心相印的美好时光。在《他们》那边,丁当被叫做小丁,丁当其实从来不是“小丁”,他的真面目被“他们”式的幽默、刻薄和酒巴间里的温情脉脉的坐而论道式的嚼舌给遮蔽了,否则丁当怎么会在多年后,真像毕露,成为保险界的巨孽。
1993年我在北京和牟森一块搞残酷戏剧,玩的就是今天令那些行为艺术家身价百倍的那一套,不同的是,今天他们是为了玩到威尼斯的什么双年展上去,我们当年则是一个独立于那种统治着中国剧院的戏剧主流的一种立场。就在这期间,我首次读到伊沙的作品。印在一份语气嚣张的地下报纸上。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存在着无限可能性的诗人。我们已经有过联系,他在大学时代为我的一首诗写了一个辞条。通过信,我不知道他也写诗。90年代初我有意疏远诗歌界,那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弱不禁风的地方,第三代土崩瓦解,我听到的都是,某某出国了、某某写小说去了,某某卖皮鞋去了,某某发誓从此搁笔不写了。人们不会背叛自己的银行、老婆、汽车、自鸣得意的先锋派意识形态,不会背叛小说、不会背叛散文,但有多少前诗人作鸟兽散,弃诗而去啊,我经常有天地之间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的感觉,前不见来者,后不见古人。写诗不是一个时代的事情,是一生的事情。《菜根潭》说,看人要看下半截。我太怕孤独,我太希望我的时代有几个值得我尊重一生的诗人,不只是几首传颂一时的作品,而是作为没有工资的职业诗人。
在九十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失去了早期的清教精神,成为许多在我看来在诗歌方面毫无前途的作者们的极乐园,《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可以镀金的地方。我心向往之的是西安,偶尔收到的《葵》,令我看到创造的激情、批判、尖锐、立场、八十年代的责任感和罕见的尊重,我感到吾道不孤。九十年代,是伊沙诗歌写作的井喷时期,正是他的写作,使九十年代的诗歌继续着创造的活力和锐度,使八十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最有价值的部分作为一个新传统得到有效的延续。
伊沙同样得忍受孤独,与南方和内地、首都不同的是,在中国封闭的西部,孤独不群、古典式的单枪匹马走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一个真诗人的基本气质。这种传统历史久远,在唐随处可见,在近代我们会立即与尼采、鲁迅在心灵上触电。我们都不习惯圈子,活得很累,自命天降大任。诗歌不只是眉清目秀的白面书生的语言学小游戏,也是英雄种族“打造中国脊梁”(伊沙语)的庄严工作。我们对文革式的国家英雄嗤之以鼻,但不意味着英雄种族从此就必须绝种。“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狼被漫天飞舞的羊毛遮蔽着,产生自个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总是被解释为一只队伍的旗号时才被容忍。
“我的诗集
侥幸出版
《饿死诗人》
是我硬塞给
世界的一份
礼物”
“他暗自决定――
“死后我再和
芸芸众生为伍”
他其实远不像他的诗歌给人的印象那么入世,他也是一个绝望的诗人,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命。这种孤独不是这时代是否接纳你,它今天拍马屁都来不及。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长着“上船”的那条腿。在诗歌上,我们必须保证自己的“不成功”,诗歌是一次次冒出水面和重返地下的自我搏斗,因为令我们绝望的不只是庙堂也是江湖,诗人在他的时代已经没有寓所,他只能是他自己的寓所。
“三十年前
我的祖父被红卫兵小将
强行剃成
一种奇特的发型
不阴不阳不人不鬼
颇似今天流行的那种
中国朋克:三十年前”
我曾经亲眼目睹时代如何在大街上灭唐。那还不仅仅是让郭沫若之流出来宣布李白杜甫的罪行。而是,把唐从小学生的教科书中删去,再也不准汉语的童声从“床前明月光”开始学舌。我永远记得我小学五年级开始下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我的全部教科书只有一本,那是一本红色的语录。作为此时代的诗人,我们不仅要创造自己的诗歌传统,而且,我们没有正常地延续下来的诗歌传统,我们必须非法地为自己接上一个传统。你当然可以说你是重新开始,你是喝狼奶长大的,在1966年以后,一个诗人可以如此说,在合法公开的方向,汉语的乳房已经成为一只长着狼毛的东西。但在非法的、在民间,汉语的血脉暗中延续,这也是事实。1972年我开始学习诗歌的时候,没有老师,我从民间留下来的禁书和故乡父老们的母语中,为自己寻找并创造了传统,我在诗歌标准上自己为自己写了一部精神上的汉语文学史。1979年,我首次看到《今天》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母语已经具有强大的自信,在汉语中做一位诗人,并且将被它成就出不朽的作品,对此我一点也不心虚。这一点,从出生那天我就没有怀疑过,1966年的历史无非导致我必须自觉地去验证这一点罢了。我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今天》,但在我的语言立场和身体上,我不喜欢《今天》,我的工人阶级感情和文化源头令我不喜欢那种享受着特权并因此叛逆的干部子弟诗人的“比你较为神圣”的优越感和“生活在别处”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喜欢《今天》领袖对古典文化的红卫兵态度。《今天》不是地方性的,没有身体,它是国家的、时代的、政治的、普通话和国际的。那些诗歌的作者就像米兰· 昆德拉小说里面的人物。他们的惊人创造是把某种波西米亚的沙龙气氛、中学生的意象游戏与一个严峻的铁血时代结合起来,既是隐晦的诗歌抗议,又呈现出优雅的风格。老芒克是一个例外,这个真正的诗歌天才是多年前《今天》油印本令我失眠的唯一原因。
在《他们》那里,地方性出现了,但身体的到来遥遥无期。“诗到语言为止”相对于意义独白的70年代和八十年代是有力的,但相对与历史、文明和诗歌古老的使命,它只是诗歌常识之一,把它奉为诗歌真理,导致诗歌成为语言的智性游戏,恰恰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修辞游戏殊途同归。伊沙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不是语言游戏,而是生命力的释放。他令我们看见了有血有肉的身体而不是可怜的自我和语言才华。从国家到地方到身体,从普通话到方言到口语,诗歌一步步重返它的基点。
“像农民爱他的村庄似的
我爱我的城市
我爱
本城的下水道
就像农民爱他的地窖
虽然今晚
我躲在下面不是为了偷情
而是为了藏身”
我在1989年出版的《诗六十首》的前言中就申明,“如果我在诗歌中使用了一种语言,那么,绝不是因为它是口语或大巧若拙或别的什么,这仅仅因为它是我于坚自己的语言,是我的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口语诗并不像普通话那样,有共同的发音标准、语法、词汇系统、行政范围和试卷。口语是没有疆域的、没有标准的、无法定义的、自由的、无法无天的、由无数嘴巴组成的汪洋大海,当你说一个人在用口语写作的时候,你不是指他在用某种共同风格、流派语言写作,而是在用一个人在用他自己的身体语言写作。抽象的可以界定的口语、作为语言学规范对象的口语并不存在,你必须具体到某个活口,才可以指认口语。任何对口语的理论概括都是对口语的本质的歪曲,口语就是“不可说的就保持沉默的”那类东西,就是“无意识、千年岩浆、黑暗、夜晚、海底”。口语不是一种,而是日夜滋生着的亿万种。可以指认的口语是什么?口,谁的口决定一切。口语一词空洞无物,可以确认的只是某个人的口,如果他开口了的话,而比起写作来,开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伊沙开口了,他的结结巴巴,伊沙语,独一无二。口语给予诗歌无限的自由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伊沙不仅是一个可以用伊沙语写作的诗人,并且伊沙语在无数口语精子般的自由竞争中,成功地进入了经典诗歌的子宫,他因此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记忆。
伊沙在他的诗歌国土上建立了矛与盾的关系。很难想象《野种之歌》的作者同时也是《唐》的作者。
“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
仍然是我所见到的最简单的情景
它不是一座雕像
也不是一面旗帜
是我们高高蹶起的臀部
制造的声音
意思是:“不!”
1998年,就是在念这个诗的时候,无数读者离座而去 。
那么念最近写的《唐》里面这些诗句的时候,他们是否应该回来?
“兰叶在春天葳蕤
桂花在春天皎洁
林中的风吹生了
一个隐者的喜悦
以草木自比的人
成了幸福的人
自比为美人的人
就是堕落的男人”
他是他的盾,同时他也是他的矛。自在的诗人必须在自己的作品内部建立这种关系,你的写作攻击的对象不是时代,不是另一个诗歌派别,而是你自己的另一部分作品。这是诗歌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优秀的诗人在他的作品内部总是矛盾的,我们只有在他自己的内部才可以比较他,把握他,而不是把他与他之外的时代、流行风尚对照才可以辨认他的方位。当然,开始的时候,攻击对象总是世界,但最终你得自我攻击,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世界。
伊沙高举他的诗歌之矛向唐冲过去,他的盾是大逆不道的《野种之歌》,我们时代的知识以为唐只是木乃伊一个,结果在伊沙的诗歌之矛刺过去的地方,我们发现那是活生生的肉体,鲜血从诗歌里流出来。他用身体而不是用古典文学知识与唐对话,这是《唐》的力量所在。唐需要的不是木乃伊式的束之高阁,它其实是深宫美人,它需要的是刺它,搞它,干它,它活着,并且风情万种。伊沙在《野种之歌》中攻击了这个时代的小传统,在《唐》,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
《唐》的意义在于复活历史于当下,把唐的身体从线装书里解放出来,通过我们时代与历史在最基本方面的联系,肉体上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是身体性的、人生的,这是一个传诸后世的基础,它特殊的话语方式,风格、格律、美学成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旦进入它,就会产生身体冲动,生命的激情。唐,不只是一种诗歌、一个朝代、而是一种中国世界的永恒生活方式,与“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有关,与英雄刘关张美人金瓶梅有关,与堕落有关、与装佯有关、与乖戾有关、与“仰天大笑出门去”有关与“携妓东山下”与“把酒白云边”有关,“与天子呼来不上船”有关,与母亲妻子女儿朋友父老乡亲有关,与君子小人有关,与故乡方言有关,与“长河落日圆”“杏花疏影里 吹笛到天明”有关,而这些,一度被当代文化传统所遮蔽。
“唐时的朋友
我已经了解了你的心情
干吗要了解你的抱负呢”
我们发现,在内在节奏上,伊沙快车慢了下来。
在一个知识分子普遍放弃文化立场、民族精神、生活传统、故乡、大地和心灵世界,向全球化平台全面缴械投降的时代,《唐》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化最重要的迹象之一,《现代汉语词典》自1840年以来形成的与《康熙字典》的停尸房与解剖学的关系在诗歌中被更坚决、更鲜明、更直接地改变了,诗人找到了进入一个贴着僵尸封条的黑暗世界的通道——他自己的活生生的身体和心。而同时,先锋派诗歌一贯朝西的单一方向也被改变了,100年后,汉语诗歌已经可以在重返自己古老传统的时候,坚持的正是先锋派的基本精神。
他将更加孤独,因为对于适应了野种和结巴的读者来说,他无疑在宣布那种他自己创造的他自己诗歌的先锋派阅读趣味为主流,而他则跟着堕落、腐朽、过时的“印在宣纸上的”唐,以右派的姿态,重返地下。“现代人的傲慢就是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地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丹尼尔·贝尔)但伊沙的悖论是,他既是野种,也是一个相信神灵的诗人,他举着矛向唐冲过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承认有限。
2003年7月至8月2日星期六
转自诗生活伊沙专栏: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art&id=16796&str=1268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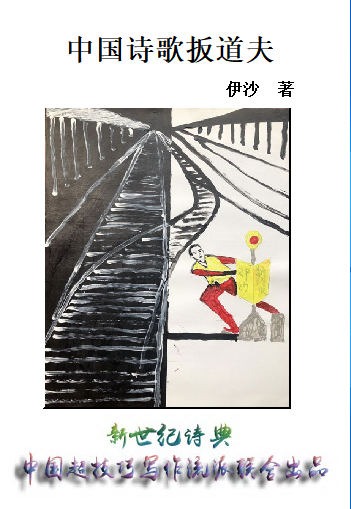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