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醒来了—伊沙访谈录》谭克修

采访人:青年诗人、《明天》诗刊主编谭克修
时间:2004年10月
谭克修:祝贺你获得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展的重要奖项——“双年诗人奖”。由于“双年诗人奖”和“艺术贡献奖”的奖品中有200亩草原私人牧场,一直被广为关注。你怎么看诗歌双年展,以及“诗歌与草原的浪漫结盟”(《南方都市报》标题)这段佳话的意义?
伊沙:谢谢你的祝贺!其实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评委会能够将此重要奖项授予我的过人胆识!
我确实很少获奖,也几乎从未获得过一个像模像样的奖。在这次之前,我获得的最重要的一项诗歌奖是2001年初《诗参考》颁发的“十年成就奖”——那是一项纯荣誉性质的奖励,没有奖金、没有奖杯、连个荣誉证书都没有,更没有颁奖仪式,但我相当看重这个奖,因为这是对我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成就和所做贡献的一大肯定,而且是由现存的一本最重要的民刊发给我的。
而这一次——是你,是《明天》诗刊和额尔古纳人民政府给了我一次获奖的全面享受:那么华丽的一个颁奖晚会,马蹬形的奖杯是一件漂亮的艺术品,别致的荣誉证书是白桦树皮做的,一万元人民币的税后奖金,还有那200亩草原的私人牧场……我确实很少获奖,但这一次却是在正确的时间、地点获得了一项正确的奖项——是我心中的诗歌大奖!
离开额尔古纳,从海拉尔飞到北京,在等待去美国使馆签证的那几天里,所有到招待所来看我的朋友都要看看那尊奖杯和那本《国有土地使用证》,回到西安的这些日子,到学校上课时有领导和同事向我祝贺,去太白文艺出版社送那部刚编完的《被遗忘的经典•诗歌卷》的书稿,那里的编辑朋友也在向我道贺,前天去赴《女友》老板王维钧先生的宴请——席间遇见作协体制里的几个农民小说家,也是在问“你的地”如何如何……什么叫“大奖”?这就叫“大奖”!广为人知,广泛传诵,具有专业内部的说服力和对于外界的号召力,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发给了谁?这些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一项真正的大奖并不是由主办单位的“级别”所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奖金的数额所决定的,还需要一点专业的意识和特别的创意,这便是“诗歌与草原的浪漫结盟”——确实太浪漫太诗意了!西川说你“玩大了”,我说“玩得漂亮”……
在打造一项中国的诗歌大奖的意义上,这次无疑做得相当成功了,但如果说到“展”,因为那本作为“中国诗歌双年展”惟一载体的2期《明天》没有及时出来,在现场的活动中,“展”的味道就没有出来。我想两年后再搞的时候,可以在现场搞一个展室:两年中的各种诗歌出版物、诗人图片、手迹、录像带、录音带……可以将刘福春、世中人、阿翔这样的版本收藏家们请去搞,让他们贡献一点资料出来,还有就是我们在旅途中谈到的:让“双年展”尽快呈开放性,愿意自费前往的,网上提前报名,把大家组织起来……真正把它办成一个两年一届的诗歌盛会,一个诗人狂欢节。
谭克修:看过你的一些简历,有时候会特别标明自己的“哈萨克”血统,这与你的诗歌似乎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伊沙:这个话题可以扯到很远,那是我1980年代末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新街口的书店里翻到一本刚出版的《青年诗选》(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当年推出的),其中杨炼的小传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他先是说自己生于瑞士伯尔尼,然后说自己有蒙古族血统。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他为什么会生在瑞士伯尔尼——父母一定是外交官吧。至于他的蒙古族血统,是后来在他的另一篇文字中得知:他奶奶是蒙古族。在当时我觉得这些小节很牛B,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杨炼在那儿玩装B——80年代的文化空气就是这样的,诗人以装B当牛B,也有像我这样的诗爱者专吃这一套,我见顾城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就给自己买了同样的一件穿上,就在那一本《青年诗选》中,还有于坚——你知道照片上的于坚那时是什么形象?头上还有毛,一把大胡子!还在那儿做拳击手状!我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也是一副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形象,放假回家看父母才不得不理发刮脸,这才露出一张在那时还很清秀的小白脸,并深以为耻。80年代就是这样的,我在小传中写自己有哈萨克血统就是受到杨炼老兄的影响,也想装B,当然我的曾祖母也确实是从新疆走出来的哈萨克。至于说到与诗歌的关系,我想首先是这点不多的血统和我这个人有关系,说豪放、说激情、说原始生命力都未免有点太夸张太简单了,总之它部分地决定了我这个人,然后由人再去决定诗。
谭克修:你是怎么走向诗歌写作道路的?你最初好像是一位抒情诗人,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突然转向,成为一个彻底反对传统诗歌美学的先锋诗人?
伊沙:我早熟,在别人成为“文学青年”之前,我已是一名“文学少年”了。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大量地阅读中外小说——我在小说方面所做的准备既要比诗歌早,又不比诗歌少,所以发誓要用后半辈子做点偿还。我在初中时作文已经写得像小说了,那个没见识也不善良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还在家长会上对我父亲说我“这孩子不诚实”,写的不像是自己的生活。到高中时我的作文水平跟同龄人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去市里参加作文比赛老是轻松拿奖。有一天,和我一块在市里的作文比赛中得过奖的一位同学在《语文报》上发表了一首六行小诗,令我既羡慕又嫉妒,觉得自己也能写,就写了还投了,结果也发表出来了,这事让我干得上瘾,就用课余时间,老写老投,在中学毕业前也陆陆续续发表了二十首诗,就这么开始的。
要说最初,我连抒情诗人都算不上,写的所谓“诗”,也就是一些“青春小语”之类的幼稚玩意。进大学之后,开始全面接触“朦胧诗”,自己的诗也一步步走过了舒婷式的抒情、顾城式的感觉和北岛式的意象,在开始个人风格的口语写作之前,北岛这个土摹本,还有艾略特这个洋摹本,已经把我培养成训练有素表现不俗的意象派诗人了。
突然转向的最大内因,是来自对意象诗表达上的不满足,觉得还是被什么东西捆住了手脚似的,外因则是我看到了于坚、韩东、李亚伟等“第三代诗人”所创作的口语风格的诗歌那生机昂然的表现活力,还有一大背景——在此之前,我还读到了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美国》,幸运和幸福地适时找到了“我的大师”。
谭克修:看起来,你的诗歌受到过美国诗人金斯堡、布考斯基的影响?影响你最大的诗人、作家(或者其它艺术家)究竟是谁?
伊沙:我的诗肯定受到过金斯堡和布考斯基的影响。但对我影响最大时间持续最长的却是李白。我怎么形容这种影响呢?那两个美国人只是“我的大师”,李白却是“我的神”。那是一种内在的根子上的影响!有人觉得我写了《唐》是个意外,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怎么可能不写《唐》呢?我写了那么久就是为了到达《唐》!“我的神”一直在暗中看着我,他给我的精神覆盖和气质感染如滔滔江水,他启迪我自由的创造活力让我怎能不干点什么……
谭克修:影响你诗歌写作最大的因素是什么?你的写作你通常在什么情形下进行?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伊沙:是生活,和我的人生状态。
我的写作从外在看是说来就来可以随时发生的那一种,但从内在来说却是十分讲究,当心有所感时,我对什么时候立刻写出,什么时候等等再写,什么时候放弃不写都很有经验和判断力,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戒律:比如,就算灵感多多,从天而降,我也从不连续在一个时间段里写出第二首诗,要写,也会休息一下换个时间再写。所以,我很少因为气弱而失败的文本范例。
到今天,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写作的动力是对写作本身的热爱和酷爱——我在四十岁不到的时候,幸福地重返了自己年少时的初衷。
谭克修:我看来,你本身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在诗歌写作上,你主张的去“知识”化,不担心会给大量初学者以误导?
伊沙:说到底,我当然也肯定是一名“知识分子”——甚至比那些将此名号常挂嘴边的人更是一名“知识分子”——这毫无疑问。
在诗歌写作上,我反对围绕着“知识”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一切标榜和故做的腔调。严肃的诗人,心里没有初学者,也就没有正导、误导之虑。
谭克修:网络上,那些不得要领、毫无难度和千人一面的口水写作已有泛滥成灾之势,可能也有你个人的功劳——因为你的写作样式,看上去大大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门槛?
伊沙:关于写作的“难度”问题,从门里看和从门外看是完全相反的结果。从门外看,我们所理解的“难度”永远都是语文层面的——是小学生识字阶段所理解的那种生字之难,就是越用生僻字,越用形容词,越用复句,越用修辞手法,就好像越“难”;从门里看,完全就是另一回事,前者所理解的那种“难”其实是最容易的,即便是毫无诗才的人通过语文课的学习也可以做到,所以里面藏着大量的骗子,而写作真正的难度永远都在一件看似最简单的过程中:如何将你个体的人生经验运用自己的语言转化为诗。想要写好,就会很难。高僧说的“家常话”和市井中长舌妇说的“家常话”——能是一样的吗?而那种看似有“难度”的写作不过是小和尚用诵佛经来唬百姓的假招子罢了。
谭克修:你怎么评价“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你比较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些诗人?
伊沙:“朦胧诗”——专制年代的地下写作,现时期的“侨民文学”,中国的意象派。上不接传统,下不接地气,前景堪忧,或已终结。
我比较喜欢的诗人是严力、北岛、芒克。
“第三代”——开放年代文化先行得以膨胀,诗歌成为群众运动的产物,全民写诗然后全民弃诗,充满青春和业余气味的集体写作,日常主义的初级口语诗,彗星诗人云集,幸存者廖廖。
我比较喜欢的诗人是于坚、韩东、李亚伟。
谭克修:在“第三代”诗人以后,也有过“第四代”、“新世代”、“晚生代”、“中间代”、“70后”、“80后”等等提法,但都未被普遍接受,这是由于命名本身的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伊沙:我认为不是命名的问题,是命名的对象已经不成其为“代”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之后,诗歌降温,回落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上,与此相映的一个现象是:不再有“第三代”式的群众运动发生——而所谓“代”不过是运动的产物,没有了运动就没有了“代”,所以后来的诗人都不是以“代”而生,命名者则怀着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代”情结来继续做点事,基本没有文学上的严肃意义,但却有着世俗策略上的某种针对性,也避免了一些漠视与无视的发生,起到了“以俗制俗”的作用,所以也不是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
谭克修:你如何评价当前的汉语诗歌写作?你认为目前汉语诗歌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伊沙:二十多年以来,在世界面前,我们总是习惯于低头,老老实实地做学生状,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说:以诗歌的现状而言,当代汉语诗歌比这个地球任何一个语种的诗歌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分壮观,正在一步步重返它曾经有过的伟大!这是盛唐重现的前夕,没有这点历史敏感,也就意味着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目前汉语诗歌最为紧迫的问题正是我们在写作中已经或正在改善和解决的问题,在上面的一个问题,你已经谈到了那种在网上人人都可以来一手的景象,不要仅仅从消极和负面的意义上去看这种现象,古诗时代这是不可能的,贺敬之、郭小川的“十七年”是不可能的,“朦胧诗”时代是不可能的,“第三代”那时候也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一个小的性冲动者和老的性饥渴者可以用外在成形的“诗”来表现他们的冲动和饥渴,也可以借助这样的“诗”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一般看法,所以,尽管他们很可能制造了很差的“诗”,但也是有感而发的……为什么会这样?那是汉语诗歌的表现力和承载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又大大的强化了——我为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我为什么写《唐》?就是想看看我所参与改造过的现代汉语在与最好的古汉语的碰撞中会是什么结果?谁托起了谁?谁又把谁吃掉了?谁比谁更无所不能?
谭克修:你怎么看待汉语新诗的传统问题?
伊沙:虽然短浅,尽管薄弱,但也够了,摆在惠特曼面前的美国诗歌传统有多少?何况再生于我们心中的屈原、李白的传统并未远去。在我们的努力下,汉语新诗与古诗间的那道鸿沟已经基本上被填平了。
谭克修:作为90年代末那场震动国内诗坛的“盘锋论争”亲历者,你现在会怎样去看那次事件?
伊沙:虽然石家庄的陈超教授说我是因为很少参加诗歌会议的孤陋寡闻的缘由,才在自己偶得机会参加的“盘锋诗会”后大叫大嚷(我很高兴!这恰恰是我非“会虫”的最好证明)——但是,到了五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并且要用更足的底气再喊一声:“盘锋论争”是新诗百年历史上最伟大的诗歌事件!
我也还是要对那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论敌们说:五年过去了,作为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推杯换盏、化敌为友,但我当年会上笔下骂你们的话,全都有效,无一字可以作废,为了中国诗歌的建设需要和健康发展,我是骂得其所,你等是被骂得其所!
看看中国诗歌这五年吧!还用得着我在这里废什么话吗?不服,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谭克修:依然有一些人不承认你的诗歌,你估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什么情形下可能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伊沙:我真得感谢这些人,正是这些人把我先和平庸的人群区分开来,再和功成名就德高望众的“名流”区分开来,我估计这样的局面不但会维持下去,时不时还会有所加剧,甚至激化,因为很显然,我不是正在走向完结开始变得心满意足心平气和的诗人,做人做诗都不会就此消停,所以对这些天然存在的反对者来说,我会不断给他们以“旧伤未愈又添新恨”的痛苦。至于什么情形下可能会得到根本性改变?我想那是当你更多的作品成为强制教育的内容的时候,当你的名字越来越符号化而这个符号越来越有压迫感的时候——我倒是希望这种情形永不改变,死去多少年之后你还是个“问题”,那样的话,你就是一直“活”着的!我会为此而加倍努力的。
谭克修:你的诗歌数量之多令人惊奇。除了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结结巴巴》、《车过黄河》、《饿死诗人》,你自己满意的作品还有哪些?
伊沙:我对2002年编定2003年出版的四年诗选《我的英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编定2003年出版的十五年大选集《伊沙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以及2001-2002创作2003年改定的长诗《唐》(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这三本诗集里的所有诗都很满意。
我有“名诗”——我为我在“名诗”如恐龙般绝迹的年代里能够拥有它们而感到洋洋得意,在很多时候,“名诗”就是硬道理;但好在我不是只有“名诗”和躺在“名诗”之上混吃等死的人,我的“名诗”也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当然,这很正常),我有至少三本比这三首要好的诗(今后还会不断增多),这让我感到踏实。
谭克修:能否谈谈你的一般生活、你的兴趣、你的阅读习惯?诗歌在你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
伊沙:我经过十年在外兼职打工所做的物质积累,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一位职业作家的生活。每天要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用来写作,每周八个课时(两个整半天)的授课量可视为这个作家例行的“文学讲座”,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前天,和一个跟我同过小学又同过中学又一起在北京上大学(他在北大、我在师大)的故人一起吃饭,他跟我老婆讲我从小就是体育狂,能够玩到的球全玩得精熟,不能玩到的球也想办法玩——我哈哈大笑,明白他指的什么,那年头还没有条件玩网球,我拿把扫帚在教室里打扫卫生时给大伙表演博格、麦肯罗击球的“商标动作”,学得惟妙惟肖。现在这些年轻时代的业余爱好几乎全都放弃了,我不是一个刻意地要给自己安排业余生活的人。说到读书,十分惭愧,我不太热爱读书,读书很少,而且毫无系统,但书读得质量很高——悟性高,没办法,近一年来,我利用蹲厕的时间读了不少当代中国人写的长篇小说(其实是片段)……
诗歌,怎么说呢?是我的理想、事业、宗教、价值和生命——这绝非虚言。
谭克修:站在额尔古纳河畔,看到对岸辽阔的西伯利亚,我几乎同时想起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他们都给我一种强烈的俄罗斯精神气质。这里离你的私人牧场仅有十余公里距离,不知道今后你准备给我们带来什么?
伊沙:我还记得,你在美得醉人的旅途中曾给我们讲起过这部电影。进一步了解你就会知道,我实在是一个在物质方面缺乏感受力和想象力,相形之下却比较看重荣誉的人——这来自于李亚伟兄在饭桌上所指出的我的“毛病”,他说:“你太在乎诗了!”所以,去看牧场那天,站在自己的牧场上,那么大的一片牧场并没有让我很激动,后来在宾馆的房间里拿到那一万元的奖金也没有激动起来,但是在颁奖晚会上举起奖杯、致受奖辞、朗诵《唐》片段时,却是high极了!你当看得出来,我喜欢在有诗的场合用诗来表现自己,并且喜欢表现得尽量完美。回来之后,在网上看到小七(七窍生烟)拍的那些照片我就笑了:拍得很好,很真实,真实记录了我在那一时刻的喜不自禁。我记得我曾当面对你说过:“这一次获奖鼓舞了我的士气!”——这话是特别真的心里话,“宠辱不惊”更像好玩境界的人说的姿态性的话,我是宠辱皆惊,刺激写作。
中俄边境上的那块美丽的牧场——重要的是:它在我心里。重要的是:我把目光留在了那里。比把它奖给我更为重要的是:你和额尔古纳的朋友们把我带到了比两百亩辽阔得多的地方,隔着额尔古纳河,面向广袤的俄罗斯,我脑中浮现出的是“大陆”这个词,我们心向“海洋”太久了,曾经一度,我们甚至想要放弃祖先留下的土地而改去打渔,海岛与海盗都变成美妙的童话,现在,我们终于回头凝望这片“大陆”了,从我们的脚下开始的这片“大陆”,一直延续到天尽头……你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串俄苏诗人的名子,我还想到了一串叫人心跳的小说大师……这会给我带来什么,我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我心里知道……
转自诗生活伊沙专栏: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art&id=22910&str=1268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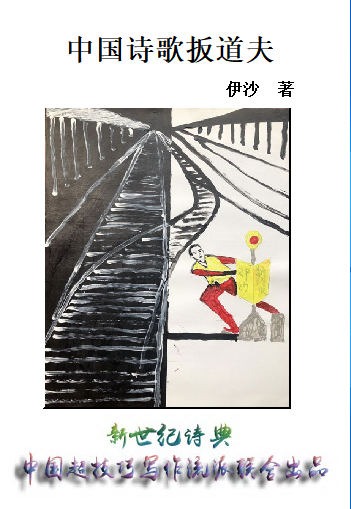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