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飞檄文+伊沙驳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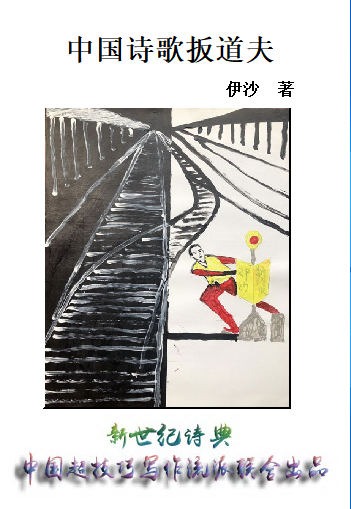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历史的美丽与诗人的春心
——观察被历史搞得心神不宁的伊沙、伊沙们
姜 飞
1
历史在众生的意识里,基本上是个老东西,从时间深处蹒跚走来。培根先生讲,跟历史对话之后,人会荣获智慧加持,像被黄教法王摩了顶,而法王在我们的想象里,大抵比较老迈。但历史未必真的那么老迈,尤其在感情丰富的男性诗人眼里,估计历史跟缪思是姐妹,但又比缪思长得更显年轻,甚至相当性感,只是不够嗲。
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20世纪的诗坛,留下了一些遗老,他们常常把傲慢的眼球用火箭发射到蓝天去,一览众山小,而对历史女士,他们却是另外的样子:个个摩拳擦掌,撒娇、撒狂,展示诗意气质或者语言肌肉,欲行护花使命,个个希望被挂在历史女士的心里,好像历史女士的心是个凌烟阁,钉满了等候已久的钉子,而诗人们个个都想着身后的遗像事宜,最好高挂、挂得显著,当然,最好只挂自己——激动的时候,好像他们真的已经挂了似的。
于坚、杨黎、伊沙、周伦佑,还有很多诗坛老手,虽然年辈不同、形态各异,但看他们在历史女士面前的表情和表演,显然都属于深情款款的“同情兄”,不妨从他们对历史女士做的各种“工夫在诗外”的工作中展开外缘研究,借用周伦佑的学术成果(“现代成名学”之类),这属于诗歌成名学,或者诗歌政治学。站在历史女士面前接受面试的这些扬名江湖的诗坛耆宿,他们现在最伟大的事业是捍卫各种来历或明或不明的荣誉证书,单方面宣布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春潮汹涌,搓手搓脚,涂脂抹粉,心神不宁:“啊,我年青的历史女郎,我为你燃到了这般模样!”
在此,谨以伊沙为标本,略事观察。
2
许多人都认为伊沙比较狂,但实际上他不是本质意义上的狂,他是有目的的狂,他的狂直奔历史而去。为此,他不仅狂,而且偶尔还会诳。
先做一次钩沉。
伊沙有一首对他而言非常要命的重要诗歌,叫做《车过黄河》,大致是讲,“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流远”。这是一首诞生于1980年代末期的诗歌,有显而易见的后现代气质,他将黄河以及附丽于黄河的各种伟大、壮美、深情的印刷体歌咏都用一泡尿打发了。这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次行为艺术,地位本来可以非常崇高,如果没有此前韩东写作的《有关大雁塔》的话。韩东那首诗,遂行的是同样的后现代修辞策略,他让寄生在大雁塔上的所有莫名其妙的文化想像和抒写显得可笑。在历史女士的编年记忆中,韩东居前,伊沙落后,而从对中国传统的宏大叙事、文化元素的解构而言,从在中国诗坛这种写作策略的创造性而言,这种时间先后的分辨并非没有意义:韩东已经给诗歌读者造成了这种类型写作的新奇之感,并且有意义增殖的效果,他还有《你见过大海》之类巩固其成果,而伊沙的跟进,在中国诗歌的历史格局中,不是质的跃迁而是量的累积,其实价值已经不大,何况,从诗歌阅读的消费感受而言,还有所谓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
本来,伊沙在时间上处于劣势,这是很难改变的事实,但是伊沙对历史女士又极端痴情,于是情况就变得微妙。2001年,出现了一本《十诗人批判书》,其间,伊沙写了一篇《扒了皮你就能认清我——伊沙批判》,虽然他一度宣称“我是我自个儿的爹”,但是谈到《车过黄河》,伊沙自己的供词却是:“这首写于大四,在我女朋友宿舍完成的诗作完全是对韩东那首《有关大雁塔》的仿写”,“我把韩东的‘大雁塔’置换成了我的‘黄河’,这也不算多大的灵感”。说出这话,足见那时候的伊沙还老实,不仅老实,而且自信:“但这个纯系偶然的置换却让我得了利,作为解构对象,‘黄河’似乎比‘大雁塔’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还有那一泡尿——我用身体语言代替了韩东的诗人语言(我得声明:此点无错)”。伊沙的老实和自信如果能够贯彻始终,也是可以赞赏的,但是,多年以后,他在接受一个叫做张后的人访谈的时候,却完全篡改了对《有关大雁塔》和《车过黄河》的叙述——“在此我想澄清一个机械解构主义加别有用心者炮制出来的伪问题,《车过黄河》的写作没有受过韩东《有关大雁塔》的一丝一毫的影响,我初读韩东的诗是在1986年《新诗潮诗集》上,我一直不喜欢他的这首《大雁塔》”。前面讲“完全是仿写”,后面讲未受“一丝一毫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因为伊沙的记忆出了问题,也不仅是因为他跟韩东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而主要是“影响的焦虑”,于是他打了诳语。伊沙是会计算的,如果坦然承认两个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车过黄河》似乎就不那么值钱。但是,当伊沙会计算的时候,他曾有过的自信“已经流远”,面对强势的历史女士,他企图遮掩一些遮掩不了的细节,由此暴露了某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虚弱。
伊沙最初却不虚弱,他在1990年代是一个精力弥满的强悍战斗者,诗与杂文都是头角峥嵘。直到1999年,两帮诗人,据说分别代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京郊做逐鹿之争,史称“盘峰论剑”。当事人各有叙述,历史隐藏于烟云深处,旁观者可以对他们间的具体是非存而不论。此间主要观看伊沙,伊沙的叙述重心是他在历史女士心中的地位,所以他对“盘峰”的回顾也就非常注意历史性角度,在十年以来的多次叙述中,伊沙的重点是两条:一,当时的“知识分子诗人”编选的“90年代诗选”《岁月的遗照》,“竟没有选伊沙的诗——我读到这条消息,心中蹿起了火苗”,以此为契机还发生了一些事,这便“构成了‘盘峰论争’的导火索”;二,“会议组织者是真希望双方争,双方火气是真大,吵得很真实,争什么呢?谁来代表90年代诗歌?为什么要争90年代呢?它是20世纪的高峰”。伊沙也许揭示了论争的部分真相,但更是逻辑性地呈现了他内心的部分真相:伊沙自认为是中国1990年代诗歌最杰出的代表,而1990年代的诗歌是20世纪的高峰,因此,伊沙所争就有了价值,他希望被确定为20世纪盘踞在诗坛高峰的那个诗人。高处不胜寒,而伊沙那时候不怕冷,他比较强悍。但是这样的强悍太执着于外在评价,而太容易受外在评价影响的强悍其实不是真正的强悍,他的虚弱在那时候就开始潜滋暗长了,于是有了后来对《有关大雁塔》和《车过黄河》的罗生门供述。
3
文学史自古以来就是“录鬼簿”,但是热爱声名的诗人总想在盖棺论定之前偷窥身后的“谥号”和“乱曰”。由于这些信息的确很难在生前预知,诗人就按捺不住,提前抢夺文学史叙述的权力,自我加冕,舍我其谁。这就出现了问题:一个真正的后现代诗人绝不应该屈从于文学史的叙述权力,他们解构一切体制,自然也解构了文学史这种可疑的学科体制。伊沙却表现得比文学史更加可疑,他一方面宣扬其“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解构、身体写作”,宣称“你要的后现代汉诗的特征全在我的诗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自我经典化、自我体制化。伊沙编选《现代诗经》,将自己的《结结巴巴》、《饿死诗人》和《车过黄河》作为经典供起来;伊沙还动辄回顾诗歌史,认定新时期以来30年的诗歌“全面超越了五四以降现代文学的那个30年,也超越了台湾诗歌五、六十年代的繁荣,并且初具了某种‘盛唐气象’”,而同时,伊沙又指出,“我使我的祖国在20世纪末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之诗、城市之诗、男人之诗,我的先锋与前卫由姿态变为常态,汉诗和后现代由我开创并只身承担”——此间的“只身”二字已经是“山高我为峰”的颠峰体验了,其在“某种‘盛唐气象’”中名列前茅的座位显然已由他自己提前预定;伊沙热爱小圈子内的评比,曾居所谓“‘中间代’十大杰出诗人”之首,他指出,“我不第一,谁敢第一”,不断自我强化其板结的“第一”意识形态;同时,伊沙还望着一个“大师”的尊号,“马铃薯兄弟”在访谈中问,“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歌”,“是否贡献出了自己具备大师资格的诗人,谁离它更近”,伊沙回答,“我看我最像”。似乎伊沙在上个世纪的革命已经获得绝对的成功,其内心已经相当地“执政党”、相当地体制,打江山的革命者开始坐江山了,于是宣扬自己的杰出、光荣和正确,宣布自己为新一代经典、第一和大师。
由此可见,反体制的伊沙在肩膀上装置的其实是一堆相当体制的思维。在伊沙那里,反体制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的“民间写作”形象,而在所有的所谓“民间立场”或者“民间写作”者中,伊沙最为热衷于强调自己的“民间”身份和“口语”方式,扛着大旗,很像宋江李逵混合体。“民间”和“口语”是不断诉诸观众视觉并且不断强化观众记忆的标签,相当于机巧的CIS设计,不但有效地用于啸聚和斗争,而且可以引起历史女士的充分注意。的确,“真诗乃在民间”,是中国诗学的传统认知,元好问和李梦阳都有所表述,韩东也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过:“诗歌在民间,真正的诗人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伊沙从前人和韩东那里得到了“民间”的灵感从而努力发掘其生产力和标识价值。但是,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里根本不是“民间”与否、“口语”与否的问题。
实际上,民间本身有多重性:不仅有乡村的民间,也有市井的民间,还有知识分子群体构成的民间,“民”与“官”对举,民间是与官方对称、有时候甚至是对峙的社会构成;同时,民间还可以分为话语模式的民间,生活方式的民间,经济地位的民间,政治立场的民间,审美方式的民间,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民间约等于底层。那么伊沙是什么民间?民间是压抑的,也备受侵犯,但是伊沙可曾站在民间立场真诚地控诉,可曾像他口头上“热爱”的鲁迅那样激烈地批判黑暗和不义?伊沙不会那样做,并且,他似乎还认为鲁迅那样做损害了鲁迅的文学前程,其实,伊沙是世故地躲在“文学”的修辞下面安全地对付诗歌领域里他那些没有多大权势的持不同诗见的同行,如果他跃出文学的战壕代民间立言,批判黑暗和不义,他就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了,而“知识分子”的标签却又是他所轻蔑的——当然,他也不是真的轻蔑“知识分子”,他是不希望自己与“知识分子”混为一谈之后模糊了自己的“民间”身份,失去了在历史女士眼里的“企业形象标识”。伊沙也并不真的认同民间的口语和表达方式,这从他对陕西某些作家的挖苦可以看出:“我只知道有那么几个进城的农民蹲在这个地方写,写下了一堆趣味低下、腐朽透顶的东西,令我无法卒读”,“我确实很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他们这些人的东西了,那种可笑的农民语言和弥漫在文字间的陈腐气息实在让我无法靠近”(《无知者无耻•身在“文学大省”》)——高高在上相当学院相当“知识分子”的伊沙,其实对真正的口语是叶公好龙的姿态,面对粗砺和锋利的真口语,他像个文弱书生那么虚弱,捏着鼻子转身就跑。
清理伊沙的诗歌和表达,姿态和立场,可以看出,在伊沙那里,“民间”的意义只剩下了“口语”,而别人的口语他又害怕,从而伊沙的民间自任就并不真诚,因此,与其强调自己的民间性,不如强调自己的个体性。只是,一旦真正地强调个体性了,则“伊沙体”、“民间写作”等集合性的所指也就被解散了。不管是不是“民间”的“无产者”,伊沙必须和江湖兄弟们团结起来再说,团结起来好对付诗歌领域的任何敌人,在“民间”、“口语”的旗号下集结、战斗,此呼彼应,势如破竹,然后一将功成,身登“历史人物”之列。
4
熟悉中国当代诗歌的人大概都愿意承认,伊沙的确是一位很有成绩的诗人,但是,对文学史过分念念不忘,凭着历史女士从前的一次青睐就不断夸大跟她的情分,却足以令其在过度的自我想像中失去重心,在喋喋不休地计较过去成就及其地位的过程中失去未来。实际上,伊沙晚近的诗歌已经是陕驴技穷的自我复制,甚至,还大量涌现了好汉不及当年勇的迹象。近20年前,伊沙的写作几乎随手就兼有田间的短促有力和充满当代欢乐的解构精神,譬如《事实上》、《命名:日》之类,而今的写作,则是无力和无趣,是《给当人事处长的老婆所定的几条家规》(“钱不能收\坚决不收\一分也不收\如今变成卡\还是不能收”——老干部的教诲,相当于陈毅告诫家人的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廉政教育的传统,跟“永远先锋”无关),是《我被穷人闪了腰》(“我傻了\原本以为\我和他是一样的穷人\属于同一个阶级\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知识分子\在妄图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时\应有的一次闪腰吗”——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诗人的“民间立场”),是“一列停在中途的火车”(《无题92》,大约可以改成“无力,since 1992”)。富态的伊沙早已丧失了上个世纪的所有力量,在每况愈下的平庸重复之中,满足于“工资够高了\钱也够花了\应该知足了\让我们时刻牢记\胡大汉奸之名言\‘岁月静好’”,诗艺的进取、后现代和先锋,早成隔世的旧梦。
即便是伊沙自视甚高的《唐》,也不过是体积宏大的又一次自我复制而已,摆一本《唐诗三百首》于案头,唐诗一首,自己一首,一一对应,次序不乱,且抄,且操,要么像余光中那样拙劣地断句加楦甚至还不如余光中(余光中是“当真,露,从今夜白起的吗\而月,当真来处更分明”,伊沙则是“兰叶在春天葳蕤\桂花在秋天皎洁”,除了比古人罗嗦,呈露的基本是自己的笨拙),或者文白夹杂不知所云(“齐鲁青未了\帝国的山川青未了”,《唐》这锅夹生饭也是“青未了”),或者也沿用伊沙式陈旧的解构模式故作“湿润”,整体观之,不过是机械、笨重而无趣的改写,语言能力远不如柏桦的《水绘仙侣》,像极了一场将其耗尽的漫长劳改。伊沙的语言能力在《唐》中表现得非常可疑,甚至出现“巨制完成的黄昏\是爱子雨伦\放假回家\的第三日\下午以后”这样的上气不接下气的笨重分行并以之终结其“巨制”。新世纪的伊沙,在事关地位、座次的口舌之争中,在徒子徒孙四世同堂的幻觉中(参阅张后访谈),成功地实现了能力退化,当然,他对自己创造能力的退化并非不觉,比如他自己选编的所谓《现代诗经》,就不收他1990年代以后的作品。
5
伊沙曾经参与过对诗坛腐朽体制的解构,小成之后,就转身迫不及待地解构自己,解构了自己开辟新境的后续可能,除了争取和捍卫历史地位之外别无实质性的诗歌行动,躺在用上个世纪的诗歌做成的床垫上,身后的殊荣已经在梦里天花乱坠。
其实,伊沙并非个案,从被历史诱惑而不思进取甚至误入歧途而言,伊沙是当代诗人的重要标本,甚至是个复数名词,伊沙们。周伦佑在《反价值时代》之类的大杂烩文本后面罗列一大堆所谓专家学者赐予的“文学史”地位,大有盖棺定论的暗示,他也曾经宣扬对体制的“大拒绝”,现在他则是投身体制并发明不着边际的“推倒或重建”说、“在场散文”说借助体制的力量延续似曾有过的荣誉;杨黎发明“言之无物”的“废话”以再造名声,而他的写作路数其实跟1980年代完全一样,换个标签,独立成家,再以自己的过往和今天的行踪为主干写成一本《灿烂》,代言“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于是自己的历史地位似乎也基本上是“第三代人”的主干甚至主席;以往和现在都经常口头“反体制”的于坚则对“代表”和获奖很有兴趣,地位日隆,渐有国史馆钦定的大师之尊;……。
但是,以前的干部经常讲,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吃饭的;现在的诗人应该说,我是来写诗的,不是来争当大师、大师兄的;我是来写诗的,不是来从良的,也不是来立高耸入云的牌坊的。说到底,这是个常识问题,也是个心态问题。何况,历史女士美丽、性感,却也矜持,估计也不是谁想怎样就能够怎样的。
“看谁更有饥饿感!”
——与姜飞同志商榷
伊沙
师兄李怡向我推荐了一篇向我开炮的檄文,还在信中向我预告:“文字有刺激性”——我以为是网上常见的那路满嘴喷粪的东西,读过之后才发现是一篇文绉绉甚至还有点酸溜溜的批评文章:大标题是《历史的美丽与诗人的春心》——哦,好酸啊!副标题是《观察被历史搞得心神不宁的伊沙、伊沙们》——哦,好卡通!通读全文,隔了些日子又重读一遍,我觉得该文作者姜飞同志并无恶意,写作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遂决定认真地回应一篇,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有一个细节上的因素:我对“姜飞”这个名字有亲切感,因为最初刺激我走上诗途的中学同学名叫姜雁飞——对此我一直念念不忘。
上个月,我刚在一首新作中写道:“不敢正视历史当然没有灵感/不愿反省罪恶当然没有灵感/不具忏悔意识当然没有灵感/生在一个欠缺精神生活的/不高贵的民族而不能/超越其上的诗人/还写什么诗啊/不灵感枯竭才怪”(《无题(169)》)——说的是日本及其诗人,难道与我无关吗?既然我已经写出来了,便该对自身生发一点作用,哪怕是在一篇反驳性的文章里面。所以,我在通读该文的两遍中一直在想:哪些说的事实?哪些说的有道理?如果说的是事实并且有道理,那么对我来说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认!并且接受!并且加以改进!——好心得好报,本文的结构也就有了。
A、 认!
a\姜文写道:“20世纪的诗坛,留下了一些遗老,他们常常把傲慢的眼球用火箭发射到蓝天去,一览众山小,而对历史女士,他们却是另外的样子:个个摩拳擦掌,撒娇、撒狂,展示诗意气质或者语言肌肉,欲行护花使命,个个希望被挂在历史女士的心里,好像历史女士的心是个凌烟阁,钉满了等候已久的钉子,而诗人们个个都想着身后的遗像事宜,最好高挂、挂得显著,当然,最好只挂自己——激动的时候,好像他们真的已经挂了似的。”姜文又道:“于坚、杨黎、伊沙、周伦佑,还有很多诗坛老手,虽然年辈不同、形态各异,但看他们在历史女士面前的表情和表演,显然都属于深情款款的‘同情兄’,不妨从他们对历史女士做的各种‘工夫在诗外’的工作中展开外缘研究,借用周伦佑的学术成果(‘现代成名学’之类),这属于诗歌成名学,或者诗歌政治学。站在历史女士面前接受面试的这些扬名江湖的诗坛耆宿,他们现在最伟大的事业是捍卫各种来历或明或不明的荣誉证书,单方面宣布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春潮汹涌,搓手搓脚,涂脂抹粉,心神不宁:‘啊,我年青的历史女郎,我为你燃到了这般模样!’”
呵呵!时移世易,沧海桑田,一转眼我已经变成了“遗老”(我还没来得及当“遗少”呢)。还与另外三个“遗老”“同情”(都想插入历史的阴道)。甭管姜文描述的多形象多花哨,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历史情结、历史崇拜、企图强行进入历史。
那么,如此这般的“历史癖”我究竟有没有呢?
我承认:我有,而且比较严重。
1992年冬,萧开愚从上海回四川在西安转车,我受孟浪之托接待他,我与萧兄性情迥异,诗风相去甚远,但也有三点可聊:一、都喜欢美国诗歌;二、都支持AC米兰队;三、都主张为文学史而写作——我忘了萧如何理解“文学史”,我所理解的“文学史”不是狭义的:譬如当代人撰写的文学史。我所说的“文学史”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史——其实是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我记得当时我们聊这个话题时还有一个回避不开的时代背景:那就是1989-1992我称之为“真空时期”的软着陆的商业文化现象(现在回头看来那是一个起点),譬如汪国真现象,我们说绝不为大众写作,所以才说要为文学史而写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萧被划归了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诗歌阵营,不知他现在如何想,我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商业文化愈演愈烈甚嚣尘上,内心的这个朴素的意念反倒有增无减,那便是:为永恒的文学史而写作。
这便是我的“历史癖”。
至于说到“工夫在诗外”——姜文中没有具体所指,我自然也不置可否。
b\姜文写道:“许多人都认为伊沙比较狂,但实际上他不是本质意义上的狂,他是有目的的狂,他的狂直奔历史而去。”
尽管,我没有搞懂什么叫“本质意义上的狂”(希特勒算不算?),什么叫“有目的的狂”(希特勒最有目的!),但是可以认,谁叫你有“历史癖”且还比较严重呢!
c\姜文写道:“文学史自古以来就是‘录鬼簿’,但是热爱声名的诗人总想在盖棺论定之前偷窥身后的‘谥号’和‘乱曰’。由于这些信息的确很难在生前预知,诗人就按捺不住,提前抢夺文学史叙述的权力,自我加冕,舍我其谁。这就出现了问题:一个真正的后现代诗人绝不应该屈从于文学史的叙述权力,他们解构一切体制,自然也解构了文学史这种可疑的学科体制。伊沙却表现得比文学史更加可疑,他一方面宣扬其‘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解构、身体写作’,宣称‘你要的后现代汉诗的特征全在我的诗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自我经典化、自我体制化。伊沙编选《现代诗经》,将自己的《结结巴巴》、《饿死诗人》和《车过黄河》作为经典供起来;伊沙还动辄回顾诗歌史,认定新时期以来30年的诗歌‘全面超越了五四以降现代文学的那个30年,也超越了台湾诗歌五、六十年代的繁荣,并且初具了某种‘盛唐气象’‘,而同时,伊沙又指出,‘我使我的祖国在20世纪末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之诗、城市之诗、男人之诗,我的先锋与前卫由姿态变为常态,汉诗和后现代由我开创并只身承担’——此间的‘只身’二字已经是‘山高我为峰’的颠峰体验了,其在‘某种‘盛唐气象’‘中名列前茅的座位显然已由他自己提前预定;伊沙热爱小圈子内的评比,曾居所谓‘‘中间代’十大杰出诗人‘之首,他指出,‘我不第一,谁敢第一’,不断自我强化其板结的‘第一’意识形态;同时,伊沙还望着一个‘大师’的尊号,马铃薯兄弟在访谈中问,‘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歌’,‘是否贡献出了自己具备大师资格的诗人,谁离它更近’,伊沙回答,‘我看我最像’。似乎伊沙在上个世纪的革命已经获得绝对的成功,其内心已经相当地‘执政党’、相当地体制,打江山的革命者开始坐江山了,于是宣扬自己的杰出、光荣和正确,宣布自己为新一代经典、第一和大师。”
白纸黑字,都是我说的、我写的、我做的,认!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我就是认为《结结巴巴》《饿死诗人》《车过黄河》皆是现代汉诗的经典之作,而我是它们光荣的作者;我就是认为自己是“第一”,不光是“中间代”的“第一”,还是整个现代汉诗的冠军;我就是认为自己是个大师,我说“我看我最像”——那不过是谦辞,实际上已经是了。我有无必要提醒姜飞一点:这只是我本人的看法?不可以么?不允许么?犯了罪么?
d/姜文写道:“在伊沙那里,反体制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的‘民间写作’形象,而在所有的所谓‘民间立场’或者‘民间写作’者中,伊沙最为热衷于强调自己的‘民间’身份和‘口语’方式,扛着大旗,很像宋江李逵混合体。‘民间’和‘口语’是不断诉诸观众视觉并且不断强化观众记忆的标签,相当于机巧的CIS设计,不但有效地用于啸聚和斗争,而且可以引起历史女士的充分注意。”
没问题!认!我是自觉的(当年自发的诗人已经开始反民间反口语了),“民间”/“口语”就是在我自觉的努力之下于近十年来被越放越大终成浩荡主流的(感谢历史这个娘们儿对我们的垂青和青睐)。但说我是“宋江李逵混合体”——这话有点说早了,刚巧这二位都是我不喜欢的《水浒》人物,我最喜欢的是林冲和武松。
e/姜文写道:“熟悉中国当代诗歌的人大概都愿意承认,伊沙的确是一位很有成绩的诗人……”
这还不认吗?赶紧!
f/姜文写道:“伊沙曾经参与过对诗坛腐朽体制的解构……”
当然!这是谁都抹煞不了的!不只是“曾经”。
g/姜文写道:“伊沙是当代诗人的重要标本,甚至是个复数名词,伊沙们。”
这话我爱听,满足虚荣心,认!
h/姜文写道:“历史女士美丽、性感,却也矜持,估计也不是谁想怎样就能够怎样的。”
这话是对的,难道我不晓得么?我就是教文学史的!在此全文录下我去年写的一首诗:
《授课》
“中国文学史
是一部贬官的花名册
和不得志者的难民营
由是推之
今天在我们眼前
晃来晃去的这些角儿
将无法构成
明天的历史……”
话说到此
讲桌上的麦克风被震哑了
而教室里的灯一盏盏亮了
空旷的教室——没有人听
B、 不认!
a/姜文写道:“……为此,他不仅狂,而且偶尔还会诳。先做一次钩沉。伊沙有一首对他而言非常要命的重要诗歌,叫做《车过黄河》……”——在此之后,他用不少篇幅掰扯了一段“公案”:即伊沙《车过黄河》有没有受到韩东《有关大雁塔》的影响?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做了“罗生门供述”。
为了他所使用的一个关键性的字:“诳”,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我儿子使用的《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版),“诳”字其义为:欺、骗、瞒哄。作为“黑泽天皇”(这么叫可以表现我的“体制化”)的铁杆影迷,《罗生门》我自然是看过的,也知道他所谓“罗生门供述”的意思——那么,我的态度是:坚决不认!
鉴于姜文对我在与张后的对话录中的原话引用得顾此失彼、丢三落四,我将其中两段关键性的“供述”粘贴过来,希望没有再“诳”姜飞一次:
在此我想澄清一个机械解构主义加别有用心者炮制出来的伪问题:《车过黄河》的写作没有受过韩东《有关大雁塔》的一丝一毫的影响,我初读韩东的诗是在1986年《新诗潮诗集》上,我一直不喜欢他的这首《大雁塔》,觉得很观念,很图解,是在说明什么,属于解构手法比较笨、不巧妙的,我喜欢的是他的《我们的朋友》《你见过大海》等诗(注意看:我的三大选本都是这么选的,既无“阴谋”且很严肃)。如果要说影响,我在思想意识上受的是当年热播的《河殇》这部电视专题片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决定不了这首诗或者我的诗,它必须有一个真实的灵感——这个灵感发生在这年夏天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借返校之机带着两位中学同学去北京玩,上车前在火车站附近的餐厅大吃一顿吃坏了肚子,上车后三人轮番抢厕所,灵感便来了——是大便带来了小便的灵感!那个灵感便种到了我心里,到了冬天破土而出!
你读到的那篇文章(应该叫做《伊沙:扒了皮你就能认清我》),不要全当真,那是来自张小波为《十诗人批判书》所做的策划:就是定好了要来一个自我批判的,惟一的人选是伊沙。
请姜飞注意以上第二段引文,我想说的是:当年,领了张小波的任务,既然是“自我批判”,我就惟恐不能把自己批得更臭,信不信由你。
姜文写道:“这当然不是因为伊沙的记忆出了问题,也不仅是因为他跟韩东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而主要是‘影响的焦虑’,于是他打了诳语。”
姜飞此话倒有“诳语”之嫌:我和韩东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我的记忆既出不了问题,还是诗坛有名的好(所以才可做小说嘛)。“影响的焦虑”更是从何谈起,从文章看,姜飞也是很关注诗歌江湖的,那么我想问问: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在我之前有没有公开说自己“师傅”是当代某某的(说他“洋外公”是谁的倒是人山人海),在我之后又有几人?我要“焦虑”会这么做吗?
把话稍微拉远点:2004年,我应韩国汉学家金泰城教授之约为韩国《诗评》杂志撰文《朴素抒情——韩东〈你见过大海〉简论》,我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
笔者近译美国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发现在布氏诗作中也有一首以非传统的方式写到大海的,题为《遭遇天才》,全诗如右:“今天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天才/大约 6 岁/他坐在我身边/当火车/沿着海岸疾驰/我们来到大海/他看着我/说 /它不漂亮//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 /这一点”——此诗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汉语世界中出现已至目前,所以它不可能“影响”中国诗人韩东,而这种不谋而合正好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联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外表所谓“思潮”的“影响”上的,而是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创造者在不断深入地表达人性的探索上所达成的异曲同工——这种努力从未停止。
这段文字或许会帮助姜飞在对诗对人的理解上提高一步。
中国诗坛的很多佳话是通过我的文字传播出去才得以成立的(因为我爱将朋友的牛B之处见诸文字),尽管我后来发现有人在利用这一点(装作无意地说他的牛B之处让我替他传播),但还是本性不改善良依旧,在此再说韩东一个:有一次荷兰汉学家柯雷教授为了他的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关于中国诗歌的专著请我问问韩东:他那句“诗到语言为止”的名言最早说在何处,我打电话问了,韩东回答说:“那是叶芝说的。”——我听罢觉得老韩很牛B,心态真好!所以有些事,原来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大太监不急小公公急”!
b/姜文写道:“那么伊沙是什么民间?民间是压抑的,也备受侵犯,但是伊沙可曾站在民间立场真诚地控诉,可曾像他口头上‘热爱’的鲁迅那样激烈地批判黑暗和不义?伊沙不会那样做,并且,他似乎还认为鲁迅那样做损害了鲁迅的文学前程,其实,伊沙是世故地躲在‘文学’的修辞下面安全地对付诗歌领域里他那些没有多大权势的持不同诗见的同行,如果他跃出文学的战壕代民间立言,批判黑暗和不义,他就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了,而知识分子‘的标签却又是他所轻蔑的——当然,他也不是真的轻蔑‘知识分子’,他是不希望自己与‘知识分子’混为一谈之后模糊了自己的“民间”身份,失去了在历史女士眼里的‘企业形象标识’”。
姜飞勿急,我在与马陌上的对话录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
永远不要拿我跟鲁迅比,我连他的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我甚至可以接受在诗歌上去跟李白比,但我不能接受在杂文上去跟鲁迅比。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投入!49后,哪里有鲁迅式的真正的杂文?谁敢写?不要命了?年代不同了,平台不同了,杂文死去了!“90年代”也没法跟“五四一代”去比,小平南巡一讲话,文人丢笔下了海,当年的景象却是:第一拨现代精英取经踏海归来,哪一个不是专心笔墨著作等身?怎么比?没的比!我个人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在向那一代精英看齐罢了——放眼当下,文坛之上,有几人有此意识和作为?再说鲁迅,我以为在当代写作,只有学习鲁迅然后避开鲁迅,方可有所作为,我庆幸我的主攻方向是诗歌和长篇小说——这是先生留给后来者的仅有的两条活路!其他路皆被其盖上盖子封了顶!
可以补充的是:别把鲁迅卡通化地描述成荆轲,当年在日本准备回国刺杀满清大员,事到临头打哆嗦的正是鲁迅——哆嗦得好!“壕堑战”、“韧的战斗”都是他老人家说的——说得好!一有风吹草动就往租界跑——干吗不跑?对“投枪与匕首”式的杂文的贪恋、过于关注中国的时局当然影响了他的文学格局、气象与成就——大文豪竟然无长篇!中短篇也太少了一点吧?那你放在世界的平台上,就不是重量级的大师。另外,“公共知识分子”是件戏装,想穿者大有人在,不差我这一号。至于“企业形象标识”就是顺嘴跑舌头的屁话了,既然如此关注诗歌江湖,难道你不知道“民间”是盘峰诗会上主持人吴思敬教授临时指定的?写文章,功课没有做充分!
c/姜文写道:“伊沙也并不真的认同民间的口语和表达方式,这从他对陕西某些作家的挖苦可以看出:‘我只知道有那么几个进城的农民蹲在这个地方写,写下了一堆趣味低下、腐朽透顶的东西,令我无法卒读’,‘我确实很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他们这些人的东西了,那种可笑的农民语言和弥漫在文字间的陈腐气息实在让我无法靠近’(《无知者无耻•身在“文学大省”》)——高高在上相当学院相当“知识分子”的伊沙,其实对真正的口语是叶公好龙的姿态,面对粗砺和锋利的真口语,他像个文弱书生那么虚弱,捏着鼻子转身就跑。”
在此,姜飞将本身乡土小说中的语言(对话部分吗?)认为是“真正的口语”、 “粗砺和锋利的真口语”,那么我就无话可说了。只好说句:不认!并且认为你侮辱了中国的先锋诗歌。
d/姜文写道:“清理伊沙的诗歌和表达,姿态和立场,可以看出,在伊沙那里,‘民间’的意义只剩下了‘口语’,而别人的口语他又害怕,从而伊沙的民间自任就并不真诚,因此,与其强调自己的民间性,不如强调自己的个体性。只是,一旦真正地强调个体性了,则‘伊沙体’、‘民间写作’等集合性的所指也就被解散了。不管是不是‘民间’的‘无产者’,伊沙必须和江湖兄弟们团结起来再说,团结起来好对付诗歌领域的任何敌人,在‘民间’、‘口语’的旗号下集结、战斗,此呼彼应,势如破竹,然后一将功成,身登‘历史人物’之列。”
这是在说“民间写作”在专业上的成熟与完善(“口语”)啊!这是在说伊沙的独立啊!OK!
e/姜文写道:“实际上,伊沙晚近的诗歌已经是陕驴技穷的自我复制,甚至,还大量涌现了好汉不及当年勇的迹象。近20年前,伊沙的写作几乎随手就兼有田间的短促有力和充满当代欢乐的解构精神,譬如《事实上》、《命名:日》之类,而今的写作,则是无力和无趣,是《给当人事处长的老婆所定的几条家规》(‘钱不能收\坚决不收\一分也不收\如今变成卡\还是不能收’——老干部的教诲,相当于陈毅告诫家人的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廉政教育的传统,跟‘永远先锋’无关),是《我被穷人闪了腰》(“我傻了\原本以为\我和他是一样的穷人\属于同一个阶级\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知识分子\在妄图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时\应有的一次闪腰吗”——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诗人的‘民间立场’),是‘一列停在中途的火车’(《无题92》,大约可以改成‘无力,since 1992’)。富态的伊沙早已丧失了上个世纪的所有力量,在每况愈下的平庸重复之中,满足于‘工资够高了\钱也够花了\应该知足了\让我们时刻牢记\胡大汉奸之名言\‘岁月静好’‘,诗艺的进取、后现代和先锋,早成隔世的旧梦。”
田间、陈毅……你想笑死我!大而化之的文章好做,一细读文本便叫人哭笑不得。我记得诗人侯马在读完拙作《给当人事处长的老婆所定的几条家规》后感叹说:“你太爱老G了!”——老G正是我老婆——这是诗人在读诗!他读到的是“诗言情”的“情”!姜飞,你想叫我怎么写?告诉老婆:去偷!去抢!去拿!去占!去巧取豪夺!权力不用过期作废!——这样就“永远先锋”了吗?如果,姜飞先生认为这就是“先锋”的话,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可去关注一下“垃圾派”、“垃圾运动”、“低诗歌”(鼓吹“贱人写作”)这些反文明、反人性、反社会的写作,去写个《垃圾论》什么的。至于你给《我被穷人闪了腰》戴的大帽子,跟太阳社给鲁迅戴的那一顶差球不多,其中暗藏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政治要求的是立场坚定、方向明确、态度坚决,真正的文学恰恰写的是错位、偏移、困惑、矛盾、怀疑……当然,这还牵扯诸多问题,最关键的是人的素质问题,譬如,一个人要是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一点天真一点天然的诗性都没有的话,你把他打死他也是干巴巴的,只能依仗总结主题套概念来读诗。君不见,在中国,把《红楼梦》这样混沌复杂的巨著总结主题加以评论的做法都甚为普遍。
f/姜文写道:“即便是伊沙自视甚高的《唐》,也不过是体积宏大的又一次自我复制而已,摆一本《唐诗三百首》于案头,唐诗一首,自己一首,一一对应,次序不乱,且抄,且操,要么像余光中那样拙劣地断句加楦甚至还不如余光中(余光中是‘当真,露,从今夜白起的吗\而月,当真来处更分明’,伊沙则是‘兰叶在春天葳蕤\桂花在秋天皎洁’,除了比古人罗嗦,呈露的基本是自己的笨拙),或者文白夹杂不知所云(‘齐鲁青未了\帝国的山川青未了’,《唐》这锅夹生饭也是‘青未了’),或者也沿用伊沙式陈旧的解构模式故作‘湿润’,整体观之,不过是机械、笨重而无趣的改写,语言能力远不如柏桦的《水绘仙侣》,像极了一场将其耗尽的漫长劳改。伊沙的语言能力在《唐》中表现得非常可疑,甚至出现“巨制完成的黄昏\是爱子雨伦\放假回家\的第三日\下午以后”这样的上气不接下气的笨重分行并以之终结其‘巨制’”。
说你不笨吧,还知道余光中扛不住这《唐》,就干脆把老余牺牲掉算了,说你聪明吧,又拉出一个素质与才华远不如老余的来做我的“陪衬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还“语言能力”呢,那篇可疑的文本(我不认为是诗),除了语言还能提什么,哦,你可以说:“诗到语言为止”。但是我可以用特朗斯特罗姆的话告诉你:词,不是语言!至于对“语言能力”的判断能力,属于舌尖上的味觉,爹妈如果没给,后天再好的老师也教不会。其他的,随你胡说!
g/姜文写道:“新世纪的伊沙,在事关地位、座次的口舌之争中,在徒子徒孙四世同堂的幻觉中(参阅张后访谈),成功地实现了能力退化,当然,他对自己创造能力的退化并非不觉,比如他自己选编的所谓《现代诗经》,就不收他1990年代以后的作品。”
又在信口开河!编者自选,此中有道。当年,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一口气选进自己20多篇(几乎是其全部的小说),别人最多4篇——台湾诗人瘂弦一定研究过这种选法,他在编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时,反其道而行之,给自己选了4首,给洛夫这种量级的诗人(我认为瘂弦与洛夫是一个量级)选了20多首。我既欣赏鲁迅的霸道(他不舍我其谁还有谁),我又欣赏瘂弦的自律(一贯的谦谦君子),但这是前辈的道行,不是我的。什么才是我的呢?交给别人去选!在自己这里,只选名作就是交给公论。我知道姜飞同志又有话说了:你的三大名作都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说明的还是……君不见,在我的三大名作之后,中国的诗坛已经不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短诗名篇了(偶有也是局限于诗圈内部),为什么?你做为一个有志于诗歌批评的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种现象,难道是集体性的“创造能力的退化”吗?那为什么长诗的名篇又在新世纪出现了呢?譬如你提到的《唐》。
h/姜文写道:“但是,以前的干部经常讲,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吃饭的;现在的诗人应该说,我是来写诗的,不是来争当大师、大师兄的;我是来写诗的,不是来从良的,也不是来立高耸入云的牌坊的。说到底,这是个常识问题,也是个心态问题。”
“以前的干部讲,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吃饭的”——所以,你是不能吃饭的,工作完了也不能吃,你要吃饭就是有罪的;“现在的诗人应该说,我是来写诗的,不是来争当大师、大师兄的”——所以,你必须一心写诗,为诗而诗,挥剑自宫,欲念全无,“存天理,灭人欲”,写好都不许想,因为写好了就可以当大师;“我是来写诗的,不是来从良的,也不是来立高耸入云的牌坊的。”——你既然是个写诗的,就要老老实实当婊子,甘居于下九流,不要有非分之想……
“这是个常识问题”? “也是个心态问题”?
不,我以为这恰恰是缺乏常识的认识,人的常识,文学常识。至于说到“心态”,是姜飞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发育不良——他有一颗处子之心!他用一颗处子之心在要求诗坛、诗歌、诗人……
德国世界杯已经过去三年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决赛前记者采访里皮请其预测赛果时这头老谋深算的“银狐”说过的话:“看谁更有饥饿感!”——结果,24年没有拿到世纪冠军并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意大利队最终战胜了8年前的冠军、那个时期的“全冠王”法国队。
当然,文学艺术不等于竞技体育,但是,它们都是人类为自己发明的游戏——都是由有血有肉的人来玩的。在虚构的高僧和现实的球员之间,它所处的位置还是距后者近些。
2009.9于长安
转自诗生活伊沙专栏: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art&id=56551&str=1268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