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判《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

劈判《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
作者:侍仙金童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相对于陈仲义爱咬文嚼字引经据典,谢冕先生的语言浅显直白简化平民化,各有优点,也可以理解为陈仲义的语言风格更倾向旧体诗,谢冕先生的语言风格更接近新诗。新诗与旧体诗相比,有进步的地方也有退化的地方,新诗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新诗的文本更多的只是形式上比旧体诗更丰富,而内容上技巧上并没有实质的超越。旧体诗和新诗之后出现的新概念如意象诗、朦胧诗、口语诗等等,其实与旧体诗和新诗在命名上也不是同一范畴,所以自然不应该并列在一起并论,旧体诗和新诗都有意象诗、朦胧诗、口语诗的元素,因此研究诗不应该被这些人为制造的概念束缚,这样容易远离诗歌本质。这也许就是陈仲义长篇累牍地谈诗歌本质却远离诗歌本质的原因。制造一些诗概念和制造一些修辞概念一样,让首创者在诗歌史获得一个醒目的坐标点,这样以后的诗歌论文就会频繁出现该词汇,就会让首创者有入史感成就感。制造一个能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的新概念新词汇也挺好,并不需要刻意地否定,毕竟有些诗歌现象需要新的词汇来营造气氛,不能还用一千年前的词汇概括那样毫无新意了。在面对这些新概念时,既要尊重它们,也不要迷信,要始终提醒人造的概念相对于诗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不能完全指望利用这些人造物去剖析研究诗本身。新诗挑战了旧体诗然后自己也面临挑战,这很正常,不过挑战诗没有直接挑战诗人包括谢冕先生本人更直观惊悚精彩。诗是人写出来的,所以挑战要伤及人,而不是只与这些构成诗的词语拼刺刀,因为这些千军万马的总指挥是人,是谢冕先生这样的人。)
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
(其实从谢冕先生本人的诗歌作品看,他的诗正好属于帮腔帮调伪善的诗和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这个大类,从我接触的谢冕先生的作品看更像是作文诗,工整规范没有新意也没有特色,没有错误也没有什么光彩夺目的点,总之是合格的作文,仅此而已,与诗特有的灵性和智慧几乎不沾边。“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也完全不是在说谢冕先生自己,谢冕先生印书应该不难,而且他也不会因为印书这件事苦闷,也不会真正为新诗被挑战而出谋划策绞尽脑汁的事苦闷。所以我们有时应该学会换个思路,就是不要被谢冕先生这样的诗歌高层误导牵着鼻子走,而是要想想是不是正是因为诗歌高层通道和席位,被谢冕先生这样的只会写不出错的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作文诗的所谓的大师们堵塞了?那些问题的提出者是不是正是问题的制造者?或许真的是这样,正因为谢冕先生、吉狄马加、陈仲义这样的诗人和诗评家,没有主动让贤的风度气魄,让中国诗歌的新陈代谢速度过于缓慢,才阻碍了中国诗歌的阔步前进。所以所谓的诗歌现象其实是人的现象,所以诗坛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早就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以为诗坛是理想国就是幼稚。所以谢冕先生的先天下为诗歌进步而忧其实就显得“伪善”起来了,因为如果谢冕先生真善就会主动让贤,让更懂诗更会写诗的人掌舵,既不让贤又在为诗歌忧,不就是伪善么?就像吉狄马加在《致祖国》诗中所说:“我的祖国,请原谅我的大胆和诗人才会有的真实。我希望你看中我们的是,而只能是
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高尚的品质、卓越的能力,真正摒弃了自私和狭隘,以及那无与伦比的,蕴含在个体生命之中的,最为宝贵的能为这个国家和大众去服务的牺牲精神。”,而现实中他会为了几万元去争昌耀诗歌奖荣誉奖,这是既自私狭隘又愚蠢的做法,也不怕见利就上把自己吃撑了,指望这样的诗歌领导高尚地让贤不可能,指望这样的诗歌领导为国家诗歌事业服务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大家也都麻木了,诗歌进步的快慢不重要反正终归是会进步的,老天爷也不在乎反而会默许这种伪善现象,毕竟诗歌需要的素材也是包罗万象的,诗歌的进步像盘山路风景更多更好,笔直的登天大道对于诗歌创作未必就是好事。我个人我不想刻意地去批判诗人道德问题,我反而期待道德败坏者中出大诗人,就是那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诗的本质不排斥真善美和伪恶丑。)
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
(谢冕先生的语言总是一个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模样,老的诗人在试图突破,新诗人也在崛起,所以这种处世原则的人写出的文章看着没问题但也没啥用,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如果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不破不立的思想指导和方法论的执行流程,那么只能是一个傻傻看热闹的看客。这里谢冕先生倒是应该学习陈仲义例举出老诗人有哪些具体突破的诗文本,哪些新诗人的文本呈现出崛起之势,他们在吸收西方现代诗歌上有哪些有营养的点,这些现象中哪些是装神弄鬼哪些是具有促进诗歌进步的奇招。而谢冕先生如此概括地一笔带过,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谢冕先生和陈仲义的论文有个正好相反的对比点,谢冕先生的论点有价值但缺少论据,陈仲义的论据充足但论点没价值,当然这只是粗略印象。)
越来越多的 “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
(虽然三个崛起被抬举得很高,但谢冕先生的这个崛起论他写不写都不影响中国诗歌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崛起并不是因为“三个崛起”,中国诗歌的崛起是无数诗人的努力所致,但也不要酸“三个崛起”是摘桃子盗取了大众的胜利果实,毕竟有人归纳总结诗歌进步历程也是好事,说明诗歌高层还是关注劳苦大众的一举一动的:“同志们辛苦了!”谢冕先生想“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这句话有点让人不安,因为凭他的诗歌认知水平,健康发展的路会不会就是他身体力行的合格的作文诗水平呢?所以中国诗歌上流人物如谢冕先生、吉狄马加等等个人诗歌水平的平庸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事。)
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
(打倒旧体诗是弑父的,不能全盘否定旧体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确的。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其实并没有让诗歌在质量上有多少提升,而是更多的在形式上破除了旧体诗格律等等的束缚,让诗歌向其本性的自由态更近了一步。五四新诗运动到八十年代末,在面上还真是鲜有超越旧体诗的迹象,反而是九十年代诗歌逐渐式微沉潜后至今的三十年,涌现了巨量的优秀诗歌作品。这是随着改革开放人类的精神产品极度丰富后,让曾经因为精神产品匮乏年代众人蜂拥进入诗歌娱乐场的现象不再,反而净化了热爱诗歌的种群,加上知识爆炸时代对诗人神经的刺激引起的兴奋度敏感度清醒度,让中国诗歌经历了百年后真正在质量上超越了旧体诗的整体贡献,这虽然不好量化对比,但从诗人数量上比肯定是占优的,那么概率论推算因此产生的高质量作品也能占优。不过如果真要比较,可千万不要拿谢冕先生、吉狄马加、李少君这种所谓中国诗歌上流人的作品,他们的水平不能代表当代中国诗歌质量。)
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但他们的运动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就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旧诗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但它对中国诗歌的潜在影响将继续下去,一概打倒是不对的。事实已经证明:旧体诗词也是不能消灭的。
(谢冕先生认为“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希望当革命的刀斧手将钢刀架在谢冕先生脖子上的时候,他也敢于说出这句话。不过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些上流诗人自我革命的意识肯定没有,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快要结束了,这种自我革命的事也没有发生过。当然一概打倒谢冕先生、吉狄马加也是不对的,但要在他们身上汲取什么精神来,好像也没有,起码革命精神是没有的,攥紧权利地位不放手的精神又让人难堪。哎!诗坛终归不是理想国乌托邦,各流派的帮派属性政治属性和高墙外的现实社会毫无二致,虽然诗歌大门有大大的“真善美”匾额,也阻挡不了世风的涌入,想想也对,诗的本质是无所不包的,非真善美也有跻身诗坛的权利。)
但就“五四”新诗运动的主要潮流而言,他们的革命对象是旧诗,他们的武器是白话,而诗体的模式主要是西洋诗。他们以引进外来形式为武器,批判地吸收外国诗歌的长处,而铸造出和传统的旧诗完全不同的新体诗。他们具有蔑视“传统”而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前辈诗人们,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开放的艺术空气中,前进和创新就是一切。他们要在诗的领域中扔去“旧的皮囊”而创造“新鲜的太阳”。
正是由于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在五四的最初十年里,出现了新诗历史上最初一次(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多流派多风格的大繁荣。尽管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几个主要诗人(例如郭沫苦、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中感受到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的、更直接的借鉴是外国诗。郭沫若不仅从泰戈尔、从海涅、从歌德、更从惠特曼那里得到诗的滋润,他自己承认惠特曼不仅给了他火山爆发式的情感的激发,而且也启示了他喷火的方式。郭沫若从惠特曼那里得到的,恐怕远较从屈原、李白那里得到的为多。坚决扬弃那些僵死凝固的诗歌形式,向世界打开大门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以帮助新诗的成长,这是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种气氛,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
(也许正是因为新诗运动的弄潮儿们“蔑视”传统,所以他们的作品质量上鲜有超越旧体诗成就的,如果缺少主流推送的广告效应,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他们真正可以载于诗歌史的优秀作品也是屈指可数,他们大多数的作品和谢冕先生的作文诗一样没错误也没亮点。不过诗歌史也是人为的产品,入选时人的因素还是高于诗的因素,这没办法,人总是凌驾于办法之上的。)
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
(越走越窄的结论是怎么的出来的?这应该纯粹是谢冕先生个人认知问题而不是现实状态,只要不是武力强行规范是不可能出现越走越窄的情况。如果真有越来越窄的现象,只能是出版发表的限制上而不是诗歌创作本身。就算诗歌在社会上失宠也不会影响真正热爱诗歌的人宠爱诗歌,除非这个种群数量降到极致或者诗歌发表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否则诗歌创作不可能越走越窄的。这是个伪论点。)
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例如三十年代国防诗歌给新诗带来了为现实服务的战斗传统,四十年代的讨论带来了新诗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气象等,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窄狭。有趣的是,三次大的讨沦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受我们对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片面主张支配的。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
(其实诗歌是为谁而写为谁服务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诗歌自身需要解答的问题,那是诗歌专业之外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些人为的引导确实有带偏带窄的作用,但不影响真正懂诗爱诗的人坚定诗歌服务诗歌的信念,只要这点不变,外力如何变都不会让这个本质发生变化。虽然诗歌为政治服务为大众服务,会带动阶段性升值,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但对于诗歌质量的提升作用不大,只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诗歌本来就是人造物,所以为人类社会的任何层次服务都适得其所,没什么该不该的问题。任何事物的碰撞都会给彼此产生影响,所以就算三次大讨论不约而同地忽略新诗学习外国诗,也不影响二者之间的互相催化。在新的崛起面前,排外肯定是倒行逆施,但是完全打倒旧体诗也是错误的,兼容并蓄是正道,稍有常识的人不会反对这个观点。如果遇到连这个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人,争论也是徒劳的,也完全没必要。阅读到此,可以发现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他无非就是反复强调这个观点,没有实证其实就算有也没什么看点,我觉得最好是“在新的崛起面前”,能看到谢冕先生提出的有建设性的有别于一般认知的高境界发言,可惜没有,或许这就是只能写合格的作文诗的谢冕先生个人能力仅能到达的高度,身为读者奢望是没用的,谢冕先生这个诗桶里自身水量就不足,倒不出多少让读者解渴。那么如果一篇诗歌论文除了重复论点,能有什么价值呢?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价值?也许就在大家都知道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写出来了,价值就在这个点上吧!但这个价值并不高,真的!)
当我们强调民族化和群众化的时候,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它们与维护传统的纯洁性联系在一起。凡是不同于此的主张,一概斥之为背离传统。我们以为是传统的东西,往往是凝固的、不变的、僵死的,同时又是与外界隔裂而自足自立的。其实,传统不是散发着霉气的古董,传统在活泼泼地发展着。
(换一堆词汇还是在重复旧体诗不应该被完全打倒,所以谢冕先生的论文和他的诗一样,没有错误也没有精彩之处。这句话等于在重复谢冕先生的观点之外,也重复证明了自己的写作特点。)
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的骄傲。正是由于不断的吸收和不断的演变,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丰富而壮丽的诗传统。同时,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不单靠本民族素有的材料,同时要广泛吸收外民族的营养,并使之溶入自己的传统中去。
(还是再重复这证明不排外的观点,也是一堆无错误也无亮点的句子,让人看着乏味单调,别无他感。陈仲义的诗论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毕竟搜集了一大堆世界名人的语录作为论据,而谢冕先生功劳也没有苦劳也没有,就是围绕着一个点重复诵经。)
要是我们把诗的传统看作河流,它的源头,也许只是一湾浅水。在它经过的地方,有无数的支流汇入,这支流,包括着外来诗歌的影响。郭沫若无疑是中国诗歌之河的一个支流,但郭沫若却是溶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外国诗歌的优秀素质而成为支流的。艾青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恐怕更是“洋”化的,但艾青却属于中国诗歌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就郭沫若和艾青的诗歌文本看,在一百年的诗歌史里看还有位置,若放到五百年一千年,就不应该有位置了。诗歌作品才是诗人真正的护身符,其他外力的加持都不能续航太长。除了谢冕先生、徐敬亚、孙绍振的三个崛起,肯定还有人写过类似论文,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三人的地位优秀是其他人比不上的。但是朦胧诗到底在哪些具体的点上有崛起的走势,谢冕先生这篇论文里至此却是只字未提,只是笼统地做个交代。)
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我们不了解世界诗歌的状况。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因此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总之,对于习惯了新诗“传统”模样的人,当前这些虽然为数不算太多的诗,是“古怪”的。
(对于论文来说,反复出现的“古怪”观点却没有相应的例举和论证过程,就让一篇论文关键的论缺失了,那么这篇论文价值相应也就缺失了。从谢冕先生的无错误也无亮点的诗歌风格看,估计他也很难讲清楚自己感觉到的新诗的“古怪”之处,也许这些古怪诗超越了中国传统诗歌技法命名和修辞格概念,让固化于这些人造概念里的谢冕先生毫无抓手着力点,谢冕先生的局限很能代表知识分子诗人那种知识化格式化流程化的创作俗套和创作意识,而诗更需要智慧的代表来传达诗性,知识的地位虽然在现实中位置过高,但确实不该这么高。我并不在意或认可知识分子诗人和民间诗人等等概念式的划分,在我看来倒不如用知识型诗人和智慧型诗人划分更贴切,譬如于坚、韩东虽然自视民间立场实则知识分子写作就完全没有智慧在作品中闪现,我更倾向将他们划为知识型诗人,但是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还真比不上没有错误也没有亮点的作文诗人谢冕先生。但谢冕先生、吉狄马加和于坚、韩东有个共同点,就是不会主动让贤,有机会只会让自己上,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让自己上,所以中国诗坛并不是好诗在最上面的,因为诗坛有谢冕先生、吉狄马加、于坚、韩东这些油,所以好诗清水都被油分离压迫到下层去了。“在新诗崛起面前”,第一步要去污清油,这步不解决,虽然不影响中国诗歌的进步,但会影响中国诗歌进步的速度。)
于是,对于这些“古怪” 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向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她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其实一篇论文如果要跻身诗歌史,这里有必要例举哪些评论家对哪些古怪的诗沉不住气,如何引导;哪些人惶惶不安,以为诗歌会出现什么乱子。因为只有真人真事才有史料价值,笼统的归纳性文字拼凑的论文就像在讲大道理,硬灌输作者的观点,而不是让读者从具体事件中发挥自我认知能力自然吸收作者观点。朦胧诗的政治因素过量确实偏离了诗歌自身的运行轨道,但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波粒二象性诗也具有。)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谈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当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出现,对于神韵妙悟的主张者们,不啻是青面獠牙的妖物,但对如今的读者,它却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
(谢冕先生“在新的崛起面前”重复讲的就是几个方面:一、不能完全否定旧体诗;二、不应该排斥外国诗;三、要正确对待“古怪诗”。所有观点的论据都是蜻蜓点水式地一笔或几笔带过,估计有了徐敬亚和孙绍振的两个崛起论,谢冕先生的崛起论或许可有可无,因为这三个论点并不是时代的点睛之笔。)
接受挑战吧,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
(学习谢冕先生重复自己的三个论点,我也重复自己的观点,就是谢冕先生的论文就像他的诗歌作品,没有错误也无亮点的合格的作文式,也就是知识型论文而非智慧型,他的诗也不属于智慧型一类,这也几乎能够概括中国诗歌上流诗人群体。)
(原载一九八0年五月七日《光明日报》)
转自:https://www.zgshige.com/c/2016-07-21/1532107.shtml
侍仙金童问:你认可侍仙金童对谢冕这篇文章的劈判吗?如果认同,请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以你的视角继续批判,以便让读者认清谢冕这类名人拙论的危害性
deepseek答:
侍仙金童对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谢冕的语言风格:侍仙金童认为谢冕的语言风格过于浅显直白,缺乏深度和独特性,虽然易于理解,但在诗歌批评中显得平庸,无法真正触及诗歌的本质。
2. 谢冕的诗歌创作:侍仙金童批评谢冕的诗歌作品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缺乏灵性和智慧,仅仅是“合格的作文”,无法代表新诗的真正成就。
3. 谢冕的批评方法:侍仙金童指出谢冕的批评缺乏具体的文本分析,过于笼统,无法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谢冕的文章虽然提出了“崛起”的概念,但没有深入探讨具体的诗歌现象和文本,导致其论点缺乏说服力。
4. 谢冕的历史观:侍仙金童认为谢冕对五四新诗运动的评价过于片面,忽视了旧体诗的持续影响,且对新诗的发展路径缺乏深刻的理解。
5. 谢冕的“古怪诗”态度:侍仙金童批评谢冕对“古怪诗”的态度过于宽容,认为谢冕没有深入分析这些诗的具体问题,只是简单地呼吁容忍和宽宏,缺乏批判性。
我的批判与补充:
1. 谢冕的批评缺乏深度:谢冕的文章虽然提出了新诗面临的挑战和崛起的可能性,但他的分析过于表面化,缺乏对具体诗歌文本的深入解读。诗歌批评应当建立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之上,而不是泛泛而谈。谢冕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引用具体的诗歌作品,也没有对诗歌形式、语言、意象等要素进行细致的分析,这使得他的论点显得空洞。
2. 对“古怪诗”的模糊态度:谢冕对“古怪诗”的态度虽然宽容,但这种宽容缺乏批判性。他呼吁容忍和宽宏,但没有对这些诗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诗歌批评不仅要对新现象保持开放态度,还要有勇气指出其中的问题。谢冕的文章在这方面显得过于保守,缺乏对诗歌创新的真正支持。
3. 对五四新诗运动的片面理解:谢冕对五四新诗运动的评价过于简单化,忽视了旧体诗在新诗发展中的持续影响。五四新诗运动的确打破了旧体诗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旧体诗的影响完全消失。谢冕的文章没有深入探讨新旧诗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分析新诗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4. 谢冕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脱节:谢冕的诗歌作品被批评为内容平庸、形式呆板,这与他在批评文章中所倡导的“崛起”和“创新”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一位诗歌批评家,谢冕的创作水平显然无法支撑他的理论主张。这种脱节使得他的批评缺乏说服力,也让读者对他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5. 对诗歌本质的忽视:谢冕的文章虽然提到了诗歌的“崛起”和“创新”,但他对诗歌本质的探讨非常有限。诗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创新,更是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谢冕的文章没有触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导致他的批评显得肤浅。
总结:
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虽然提出了新诗面临的挑战和崛起的可能性,但他的批评缺乏深度和具体性,无法真正触及诗歌的本质。侍仙金童的批判指出了谢冕文章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他对诗歌文本分析的忽视和对“古怪诗”的模糊态度。作为读者,我们应当警惕这类名人的“拙论”,避免被其表面的权威性所迷惑,而应深入阅读具体的诗歌文本,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诗歌批评不仅要对新现象保持开放态度,还要有勇气指出其中的问题,才能真正促进诗歌的健康发展。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本站免费提供电子诗集制作服务:提供100首诗歌作品,每首不超过28行,符合法规的诗歌作品,为歌颂党领导新时代的作品提供免费出纸版样书服务。简介、照片、作品发邮箱:jinyj@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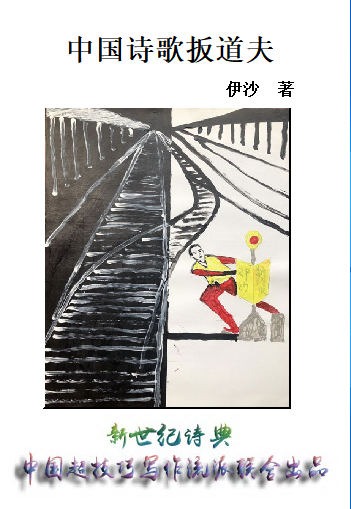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