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沙《界定:发生在90年代的汉语诗歌》的自由答辩

沉河:非常感谢伊沙先生,我是沉河。请伊沙先生向我们描述一下90年代主流以外的暗流的基本情况? 伊沙:主流和暗流的存在形态可以作一个判断。你比如说知识分子写作,杨远宏在一篇文章中说:你也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诗歌,你怎么能说你自已是民间写作?这种浅薄的、低于中国诗人正常智商的提问我就不喜欢,我所指的主流与暗流是什么呢?很俗地说:在国内官方文学主要媒体是知识分子的家园。中国主流媒体的编辑都不是诗人,他们仅仅是大学时候学了中文系,因为分配到了编辑部而已。这个人喜欢小说,那个人喜欢诗,那么这个人去编小说,那个人去编诗。这样的编辑一生都可能是业余编辑,一生都是以诗歌爱好者身份存在的诗歌编辑,那么这种编辑他接受知识分子诗歌是天然的,知识分子诗歌在文字的表面上是很清洁的,在趣味上是非常高雅的,所标举的姿态是非常高蹈的。小布尔乔亚的女编辑很可能从最外在的方面,去判断这是诗;而另外一种风格的比如说沈浩波的诗到了编辑部,恐怕他首先不是判断你好坏的问题,而是编辑首先就认为你这个不是诗,然后稿件被扔到字纸篓里去,这种存在(我不是说什么在暗中操作)也就反过来证明了知识分子写作是极其传统的,它唤起的是一个女诗歌爱好者内在的、血液中的传统。而另外一种形态上的写作,我想在我视野里也存在着两种趋势?我说出有两种趋势可以表证我决不反感另外一种类型的写作,比如以余怒为代表的写作,如果我们以知识分子写作方式来看,它解决了什么?哪些东西中国诗歌有?它更新的东西是在哪些地方?我可以谈出来。在余怒的写作中,我觉得它是一种对纯正现代主义传统的一种清理,尤其是在汉语形态下,他的写作在骨子里是反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是一种纯正的现代主义。这种写作如果一定要按知识分子的体系对照起来的话,它应该是卡夫卡以后的写作。具体到技术上,是中国意象诗歌发展到一个高度的写作,在对意象诗歌的追求上,他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可以回头去研究北岛的意象诗歌,然后你可以在第三代的意象诗人,譬如说孟浪的诗歌中,看到80年代诗歌意象构成的状态。你再看余怒的诗,我不能说他的个人成就一定比北岛好,但我要说,他的追求已经占领了一个新的高点。在他的诗歌中,已经溶了80年代的很多传统,譬如说非非理论中的非常可贵的在语言追求上的东西。另外一类写作,我称之为泛口语写作(不想说后口语写作,因为这个"后"会让人想入非非),也是一个大的系统,其中也有两种流向,一种是后现代文化背景作为它存状态的一种写作,姑且称为后口语;另一种完全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杨键的诗、候马的诗、徐江、朱文的诗,这些诗中呈现的文化形态反而是悲天悯人的,非常富于终极关怀的,就是说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里面全有。在外在的品呈现上,它是非常经典的,追求精致的口语。这样的一种写作的九十年代也保持了活力。我眼中所看到的暗流就是这两个流向。 沉河:另外一个问题,象你讲话中谈到的欧阳江河、西川呀,他们的写作在95年之后是否有一种变化?按你发言的说法,他们是毫无变化的,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象是有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欧阳江河、萧开愚、(王家新没有变化是肯定的)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伊沙:我想我们在谈论一种变化时,是指这种变化是能够生效的,即产生了对于诗歌发展的效果。如果一个人,比如说西川,他突然在90年代后写了汪国真似的诗,他变化了,绝对没问题,但我要说他没变化,我会说这种变化是无效的。我具体告诉你的是孙文波的写作,我已经在文章里公开讲了,他是自近10年知识分子学术炒作中获益最大的一个平庸诗人,比如说王家新仅仅是在重要性上被夸大了,而孙文波则是一个平庸诗人,好像步入了显赫诗人的行列,我认为他的写作在前期是一种抒情的方式,在后期,如果知识分子认为孙文波发明了叙事,我承认孙文波为知识分子抒情诗人发明了叙事,他不是为整个诗坛发明了叙事。整个诗坛最早的叙述(我不称为叙事,因为叙事这个说法太不学术化了,太业余了,为什么呢,《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叙事诗),我说的是叙述是叙述的自呈,是一种面对叙述自身的一种叙述方式,我称之为不及物的叙述。在诗歌中的叙述是一种伪叙述,它不是以叙事为目的的,它是一种写作的策略,这种写作早在第三代诗人,从王小龙在82年的作品中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这种叙述,是当代诗歌叙述意义上的叙述,同时他的叙述是比较有知识分子趣味,就是说叙述的比较经典、比较克制、文雅。其实他们没有以张曙光的早期诗歌作为一个方向,因为这种诗歌的完成仍然是需要才气的。他们为什么要以孙文波的那种想哪儿写哪儿,最平淡的生活场景,最浅薄的哲理渗透这样一种叙述来开始他的诗歌。因为这种诗歌是不需要大脑,更不需要身体,所以我觉得在孙文波那儿,大家找到了一种平庸者的安慰方式,孙文波成了一种自慰手段,所以他确实为知识分子发明了叙事。包括广泛的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人,现在采用的叙述方式都是孙文波式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无法生效,它只对某种腐朽写作的暂时缓解起到了作用,不对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真正主流的诗歌发展产生真正的作用。 沉河:看来你对孙文波阐述的过多,其实我对孙文波也没有过多地看重。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避开不谈。另一个问题:你在阐述写作流程时,主流和暗流,它的基本的依据,或者说是标准好象跟语言的方式有关系。从你提出的诗歌,比如:杨键、候马、朱文的诗歌,他们的基本情趣是悲天悯人的与知识分子有相似的,甚至一致的地方,我比较赞同,那么我想问诗歌流程究竟该依据什么更恰当一些? 伊沙:从原理上讲,任何语言都不是语言决定的,就是说语言向外在所呈现的状态,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在某种情趣上与知识分子相似的那一支,但是他们呈现出的语言风貌是不一样的,那么语言风貌的最终结果不一样,决定了他们内在也是不一样的,内在的本质上也是不一样的。我只能笼统地这样讲,至于这个悲悯怎么样,那个悲悯是假的,那个悲悯是真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曲有源:我不是提问题,伊沙关于海子的评论,我就说一句话,(我心里早有不满,海子的事过头了,信仰过头了)海子的问题应该有个结束的时候。诗人死是应该同情的,但对诗歌发展来说,他应该恢复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海子现象让我想,如果海子死在现在,会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他死在89年,89年人们内心需要发泄的东西很多。恰恰那个时候,四川一批很有希望的诗人都转移到搞书去了,有些人经受了一些特别的待遇,就在这种时候,海子死了。诗人们心里也有一种需要发泄的东西,死亡正是人们发泄的契机。这是海子现象的历史背景,另外,海子现象与开放后盲目和世界接轨有关系,这样评论家们就从国外搬出很多自杀的例子,好像中国也需要一个自杀的,然后大作文章,这样才能跟国外接轨。恰恰中国诗人最不愿死,尽管你伊沙说:"饿死诗人",但"饿死"我也不死(掌声),就这个劲头,中国诗人受道家影响最大,佛教倒影响不大。这种状态与自杀相差十万八千里,(反正在特殊情况下我也不想自杀,我还想很好的活下去),若你是很有出息的诗人,想对中华民族有贡献,那你用你一生的生命去写东西,不是死能解决问题的。继海子死了之后,又有两个自杀的,也在宣传,不过没有宣传起来吧了。 伊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海子神话的内容。 曲有源:这是海子之死的两大背景,后来的诗歌要么表现出不是食古不化,就是食洋不化,海子当时是很郁闷的,海子的郁闷是当时那批写诗的人看他一钱不值,四川去了,四川一些诗人不买他账,把他说成一钱不值。 伊沙:当时尚仲敏谈到海子的诗,他与海子还是朋友,他在《非非评论》里的一篇文章说但丁已经死了多少多少年,不需要一个但丁。 曲有源:所以后来海子的诗歌居然作为现代诗去推崇,我对现代诗就特别怀疑了。他很大程度上是浪漫抒情的东西。而且他的浪漫抒情并不到位,艺术技巧也没有学到家。因为艺术的探索是依据时间的长短来达到高峰的。不是说年轻时激情来了写下一大批,经历后来的创作之后,他很可能要把那些东西烧掉,但我们还把它当精典来评论,这些事情都很可悲啊。有许多东西他的艺术探索没有到达那个位置上。我觉得诗歌的艺术技巧在90年代刚刚步入,还不算正常。海子诗歌的艺术技巧在中国引起了倒退。当时我听命也编选了海子的遗作,但我没有选出我认为好的诗歌。 伊沙:我插一句,比如说黑大春的写作,他自认为写的是新浪漫主义诗歌。尽管他的诗歌有大量现代主义意象构成的技巧,但他总体情绪是浪漫主义的。如果说黑大春自杀了(如果他自杀的时候选得对,正好与90年代真空时候结合起来)的话,他的诗歌一样可以成为90年代海子那个位置上的诗人。 曲有源:以前我对海子事件是否公开谈论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几年来我与诗歌界接触不多。这次吕叶邀请我来,顺便谈到海子。...... 伊沙(插):我觉得曲老师应该是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的一个扶助者和见证人。前几天我们在房间里还谈到,就是当时李亚伟发表的一组关于酒的诗,下面有一个批注,以前你编发诗歌从来没有批注,但那次你可能忍不住了,你说亚伟有李白之才。确实曲老师包括宗仁发老师对第三代整个诗歌发展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而且尽管曲老师本人的创作与第三代诗人的写作没有多大的关系。 曲有源:现在既然把海子的问题提出来了。我觉得一是不要有任何的负作用,从研究他的诗歌艺术技巧到整个关系应该得到澄清,澄清之后人们才会明白,海子的诗歌创作我不要再学了,学也没用。这也是如何研究他创作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评论家不去研究这个问题,他不懂,就起哄,一起哄就造成很不好的现象。我希望这个论坛之后,能进入正常的研究诗歌的状态。不是说...... 伊沙(插):不是说要取消谁就取消谁,而是让他回到他原来应该有的位置上去。他做了什么他就做了什么。 曲有源:就是说有的东西是靠历史去取消的,就是说把历史要做的工作我们提前做一做,当历史明白过来去做这件事时,我们大概已经作古了,包括在坐的人也作古了。那时再回过头来看这时的诗歌怎么样,一看就很清楚。因为那些总结里,一切新闻性的东西都没有了,就只靠作品本身说话。我就补充到这儿。 伊沙:谢谢! 曾蒙:伊沙先生,你刚才谈到十七年的文学,王家新的传统包括在里面,我也比较认同。我问一个问题:你认为1949年前现代诗歌与当前泛口语诗歌之间有没有关系?再问一个问题:现代诗歌的传统是什么,你能描述一下吗? 伊沙:先说第一个问题,泛口语诗歌与以前的诗歌有没有关系,我可以说没有关系。有些评论家在后来总结的时候,(我认为是一种诗歌之外的学术上的附会),比如说胡适提出来的"我手写我口",有个评论家说:于坚做到了。有个评论家说我(伊沙)做到了。我觉得我从来搞不清楚胡适提出"我手写我口"产生的相应背景,我对胡适当时文章的氛围根本不了解。而且胡适所针对的是当时整个白话文的运动。他是对整个白话运动而言的,绝不是对诗歌具体形态发展而言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关系。我们写的口语诗与胡适开始写的口语诗,如果提关系我觉得是很牵强的。事实上在1949年就是一次断裂,这种断裂是与五四以来文学传统的断裂。那种传统跑到台湾去了。台湾的文化包括台湾的诗歌与五四的传统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传统是有关系的,他们反而跟田间和艾青的传统没有关系。所以说那种传统流到那里(台湾)去了,这里反而造成一次断裂。这种断裂有没有好的作用呢?我认为是有的。在中国汉语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是可以提及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把汉语变得干净了,我喜欢大陆的汉语,这决不是因为本土的意识,而是我在写诗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想追求一种纯净的口语的诗歌,在大陆的氛围中我能完成它。如果我是一个台湾人,我很难设想。台湾在内在气质上有非常好的诗人,但是他们一到语言的层面上就变得非常"结实",就是语言的词语化。语言的词语化在知识分子那里是旗帜,王家新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词。知识分子后来都爱说"词"事实上他们是从北岛那里偷来的,北岛在去国外之后就爱说"词",在我看来,"词语化"就是语言"结实"状态的东西。台湾的诗人好像天生具有这种"结实"的能力。这种语言我一直称之为"后五四时期"。 第二问题就是现代诗歌的传统,我这样来说吧:我不习惯说中国的诗人某某某是荷尔德林的孙子、某某某是里尔克的孙子,好像命定他们与那些人就有天然的骨血关系,我非常不习惯这种说法,我排除掉我最外在的民族的尊严。我也不赞成说他是李白的孙子、杜甫的孙子,那样也断裂了,我只是觉得一个传统的建立或者说发生,它不是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从纸面到纸面。不要把从零开始说得那么可怕,没有一个从故纸堆开始的东西搞的那么可怕。我愿意说: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是从食指那儿开始的。新诗的传统当然我认为是从胡适、郭沫若那儿开始的。但是,现代诗的传统与新诗没有关系。它断裂了,是从食指开始的。 曾蒙:我指的现代诗歌,是五、四至49年之间的那个传统。 伊沙:传统是他们自己创立的。尽管你说这个人曾经留学过哪个国家,这个人的文化教育曾受过哪个国家的影响,但我绝不认为他就能把英国的什么文学传统贯输到从零开始的中国诗歌形态里面。我拒绝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认为是胡适他们从零开始的。 徐江:我谈一个细节,比如徐志摩。他在英国时曾拜访过哈代,也译过哈代的诗。但我们看他《再别康桥》里抒情的东西,你能感觉到他从古典里化过来多少东西。而跟哈代截然相反,哈代的东西以及后来发展到七十年代英国运动派上,他可能叙述的成分要重一点。我觉得一个诗人他所受的教育与他诞生的作品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不是那种直接的承接关系,它只是一种潜在的影响,或者说滋养吧。 伊沙:你比如说一个诗人受到某一外国诗人的影响,比如冰心受过泰戈尔的影响,你不能说整个新诗就是从印度文学里挪来的,从英国文学那里挪来的......,我觉得知识分子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变成了知识分子内部比较公共的法则。他们的公共语言便变成了某某之于荷尔德林,某某之于里尔克!......这太可怕了。有人说海子的传统来自于荷尔德林,我一听这种语言我就觉得太可怕了。 徐江:我还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不管看一些诗评家的文章也好、对话也好,我特别害怕一点,就是问我,你喜欢哪个诗人,哪个诗人影响了你。因为我们一生中喜欢的诗人肯定不下一、二十个吧,那你怎么去确定其中的一个。只是某些诗评家去评论你文字的时候说你受了谁的影响,便认定你受到了谁的影响,这种学术太不严谨,我希望大家读书时都注意这一点。 伊沙:我可以告你一个事实,王家新到英国朗诵诗,英国有个诗人认为王家新写的诗是不开化的诗歌,为此,王家新写了文章。他跟着100年前的英国大师亦步亦趋的结果是被这个英国人说成是不开化的诗歌。有一次我跟一位德国汉学家作过一次交谈,我在谈话中刚提到里尔克,这个德国人的反应便吓了我一跳,他非常奇怪我为什么要谈里尔克(当然他知道里尔克),他认为你的诗已经写到了那个地步了,为什么还提里尔克。我觉得,这样一种构成形态,如果某些西方人喜欢这种,那你永远是不开化的。我接触过某一些西方人,未必喜欢你这种形态,未必习惯接受你这样。即使我们最杰出的诗人北岛的诗歌,也被史蒂芬.欧文的一个说法是:一个美国的中年(诗人,当时写文章时非常年轻)认为是让美国的诗人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作品。有一个瑞典的汉学家说北岛作品的构成方式是瑞典50年代诗歌的水平。你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诗歌形态的东西吗?我们都在同一个地球庄落里住着,你愿意我们的诗歌形态一直是这样的东西吗? 钱文亮:我跟伊沙说两个问题,我首先谈我的感受,伊沙先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发言还是很有启发,而且比较客观。因为90年代诗歌牵扯的问题太多,它是在一种非常大的意识流程、在一种多向的文化冲撞中形成的,有很多问题从一个方面谈恐怕不太清楚,所以这种对话非常必要。而且,伊沙先生刚才谈到海子、谈到王家新、谈到知识分子写作,我觉得对诗歌的这种偶像化的瓦解在80年代的写作中我们是一直在进行的。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而且很愿意一直这样做,我想,这个诗坛一定是不能有什么偶像的、有什么神话的。我觉得中国现代诗歌从80年代开始崛起到现在,不能再倒退,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伊沙先生刚才谈到一些“流向”问题,我觉得80年代与90年代,它确实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海子他究竟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他的事件对我们确实是很陌生的。我与几个搞哲学的朋友谈了这个问题。中国文化里面比如儒道都非常重视在世(生命)。海子自杀,他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有很多的亲情呀。比如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我们自杀时也许我们自己不怕死,但一想到有很多牵挂,有很多双手便把我们按住了。我们就死不了。海子的自杀在当代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精神性事件,我至今也搞不懂是什么促成他自杀的,我更愿意把它设想为一种精神上的选择。所以刚才伊沙谈到杨健等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海子的出现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震动。一是他的自杀是重大事件,另外一点与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80年代有一本书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后来有人把它总结为影响当时中国知识青年的一种潮流。刘小枫终极关怀的引入,海子之死在这个时候出现,与哲学上的、思想界的这种潮流起到了应合作用,然后使大家心窗一亮,看见了另外一维,我把它作为中国诗学的超越之维,一种引进。我觉得海子最大的价值,对我们的诗歌与我们的诗人(对人类生存,对个人生存有所领悟的人)来说,他一下把我们打开了。朦胧诗歌在这之前一直心系国家、民族,没有突出人的本体。而第三代诗歌运动,它是从语言上获得了解放。但对诗学本体意义上的一种追求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海子的死让我们对一些外在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一下子觉得不太重要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确立了我们自己的生存,对我们个人的生存有所思考。这个时候,个人化写作出现了。我不太喜欢这些群体、流派之类的化分。我认为90年代最大的收获是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就是诗歌写作、本体论的诗歌写作。如果不能从个人出发,与人类本体的生存处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进行写作的话,任何写作都是虚伪的。这是精神方面。但任何一种精神都不能把它绝对化,普遍化。在这个基础上,个人的实践会有不同的流向、不同的形态。我认为这是90年代(诗歌)最为可贵的地方。有一次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年轻的教授说,90年代诗歌绝对赶不上80年代。我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整个90年代诗歌无论从精神质量上还是语言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80年代。我觉得这种局面不应该在一场争论或一种偏颇的命名中把它截断,我认为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从自身出发,从人类本体出发,不要被任何观念、任何概念所限制了。我觉得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诗歌才能出现它所期望的东西。 格式:刚才伊沙提到海子的诗歌在90年代上半期成为主流,我不太苟同。因为在90年代上半期,很多优秀的诗人他们占主流,海子仅仅是一种泡沫。海子是很多人制造的一种幻觉。海子是89年3月26日去世的,我有一首长诗就是献给海子的,当时我就想以一个小市民的角度去理解海子,不要把海子的死形而上,要形而下,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当一个正常人去理解。海子的抒情是天生的,他诗歌的技艺不可能使他的抒情走很远,这就注定他后期的作品很粗燥、很无奈。再就是海子一个最大的悲剧是把彼岸的东西此岸化,也就说,他把天堂当成了现实,所以走不出来,他只有死,没有别的选择。 伊沙:我给你鼓掌! 伊沙:刚才那位(钱文亮)你向我提出了质疑,我可以反质疑你,你的表述听起来很漂亮,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你抵达了一个词,你说海子解决了本体的问题。你谈到了此岸,而格式又回答了你。这个我就不谈了。我想听你具体地谈海子解决了什么本体的问题? 钱文亮:我觉得他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些问题,用自己的生命去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许多断裂,实际上有些是不存在的,任何东西不可能有完全的断裂。比如你说从食指开始的现代诗歌与新诗传统没有联系。我想问你怎么看待穆旦和朦胧诗的关系呢?不说别的,我就听听你对穆旦的认识吧! 伊沙:我觉得穆旦也是知识分子学术炒作中拉出来的一个牌子,穆旦是一个很平庸的诗人。 钱文亮:啊,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们的对话就非常艰难。 伊沙:不,我不希望你抵达一个名词,我希望你谈到具体的东西,你的发言听起来很漂亮,你说他解决了本体的问题,你告诉我什么是本体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的论题里我希望你提到关于整个诗歌发展海子解决了什么问题。我非常赞同要从形而下来理解海子,这种形而下不是市民的形而下,包括理解昌耀。也许一个新的神话正在建造之中,就是昌耀的神话,一本最新的昌耀诗歌总集正在出版、发行之中,这部诗集的附录部分收录了21封昌耀写给杭州女诗人庐文丽的情书。我读完情书的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不夸大说一夜无眠,我失眠了2个小时,我感到非常的难过。我想到了海子是同一个问题。尽管昌耀的死与海子的死在具体形态上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写作,他们遇到的生命困惑是一个问题,我把这种写作称之为寻找女神的写作,以及寻找女神的生命。他们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女"字身上。我为诗人昌耀写了这21封情书难过。我不是说一个诗人不能向一个平庸的女诗人表达爱情,而是说他在里面采用的方式是让所有的东西都以神圣的名义去做。他到处在讲,哪个大师在哪一年与哪个少女的什么关系,当时他们的那种存在是什么样的。海子的死从形而下来讲就是因为女人,戈麦更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回避这些东西去谈问题。在他们那种生命形态中,心中有一个女神,然后在现实中去找,在他们的审美概念中,找到了女人他要强加给人灵魂以及灵魂的质量。我相信他们两人的灵魂都有质量,但这种质量加注在外表很姣美然而内在不管的女人身上,他们自己失败了也伤及这个无辜的女子。其实对于海子的研究我可以在本体论上研究。我们可以具体地谈这个生命,而不是去抵达一个名词,说它解决了生命形态的问题,好象以前别的诗人都不敢死,或者不敢以这种方式在诗中去面对死亡,我看到了关于死亡的诗歌。在海子之前就看到过不少,比如陆忆敏的诗歌、刘漫流的诗歌,都曾经写到过死亡,写得非常精彩,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人在90年代初傻不到那个程度。 沉河:伊沙先生,我觉得你只看见了太阳,没有看见太阳的光芒。你针对一个人的死,说昌耀的诗歌是给一个女人写的(伊沙插:我没有否认昌耀的诗歌也没有否认海子的诗歌。)你说海子的死是因为一个女人,昌耀的诗歌也可能是因为一个女人,这是不存在的。就像太阳本身一样,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光明,那么海子的死我们不知道他是因为女人还是因为其它因素,它影响、普照的东西是确确实实存在。那么昌耀的诗歌,他是给一个女人写的,但是昌耀的诗歌本身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及所形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再一个,你说写作是与生命有关,与灵魂有关,灵魂又与身体有关。是的,你是回到了身体,但是身体之外更多的东西,难道不存在吗? 伊沙:那么我告诉你,灵魂是长了生殖器的,因为它附着在身体上。 沉河:是的,灵魂可能是长生殖器的,但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见过,我是没有看见过。(笑声) 伊沙:以你们乌托邦的人其想象力应该很发达,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长得像猪,或者长得像四不象...... 主持人:对不起!打断一下,请回到稍微学术的位置上。 曲有源:......我来谈一谈食指的问题:食指的出现是一种地下写作(传抄)的开始,不是现代诗的开始,他的意义在于启发了北岛这批人。另外我觉得现在又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炒完死人,开始炒病人,(笑声、掌声),我觉得食指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但他的写作是浪漫主义写作,应该说他的写法对现代诗没有什么贡献。下面我对新诗传统简要地说一下......(略)...... 后来出现了个性化的写作,有许多诗人默默地写,他们对团体特别反感。另外还有一种民间之外的另一种潜流,他们什么都没有参加,在那儿独立地写作。比如说有一位叫冯杰,就是这种情况,冯杰有几首诗写得特别漂亮,但后来写得不太好了。还有新疆的刘亮程,也属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看实际上他对民族文化有多大的贡献。我觉得这次会很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始进入实实在在的研究问题,然后进入一种实实在在的创作。 (以上根据伊沙在“中国南岳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的发言后引发的自由答辩录音整理) 摘自《锋刃》诗歌论坛
转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780014/?_i=3702169TBPOJwz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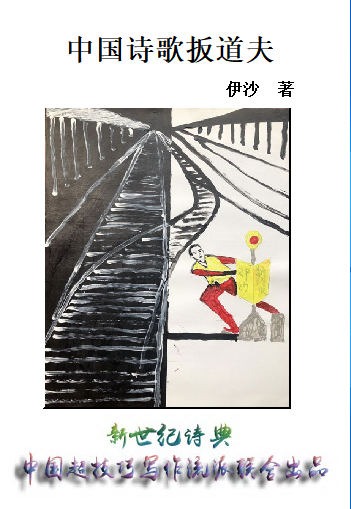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