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诗论争中的伊沙:口语诗人是日常的革新者

口语诗论争中的伊沙:口语诗人是日常的革新者
诗人伊沙仿佛是一个多重性格组合的复杂个体:既有菩萨低眉的柔情,又时常显现出金刚怒目的剽悍。他可以悲悯地关注医院角落里睡在地板上的“人民”,也可以在一次论争中快意恩仇地将对手骂得体无完肤。
他是作家莫言口中“徘徊在食堂和厕所之间的一位诗人,堪称地狱诗人”,也是批评家吴思敬眼中“披上了嬉皮士的外衣的战士”,在更多想入选口语诗而未能如愿者们的笔下,随着伊沙与新诗典群体的日益庞大,他被冠以一个更加惊悚的称号——“诗霸”。
9月份,诗人曹谁一张咄咄逼人的诗界檄文——《中国新诗99%是垃圾,伊沙是垃圾中的垃圾》将口语诗以及伊沙推向风口浪尖。不久,“从孩提时代就是打架好手”的伊沙随即予以反击,回应一篇《口语诗是世界潮流,他这种土鳖和混子,根本不该入诗歌这一行》。至此,双方让双方剑拔弩张,口语诗人与反口语诗人展开了持续月余的激烈论争,随后涌入这场论战的诗人持续加入,使这场诗界的论争持续发酵。
“你跟我叫板,我就跟你斗到底。”伊沙的强硬回应除过论争本身,他更关注的是当代诗歌的命运。“口语诗是中国诗歌的未来,一定会把中国诗歌带向精彩的未来。”自带解构基因的口语诗是信仰,但并不是信条。他在《中国口语诗选》中这样写道:读完本篇扔掉它,不要把它当做信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指导写作,中文口语诗更是如此。
“诗歌界需要一场战争,史诗般的战争最好。”有人如此评价这场论争。而对于伊沙而言,在言语的嬉戏中,扒开一条自由的缝隙,让当代诗歌不再“端着”,是他更乐于看到的情境。
“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1988年,伊沙在《车过黄河》这首诗中为当代诗歌注入进了新鲜血液。这一次论争之后,或者说这一场战役之后,诗人伊沙和他的口语诗又将为当代诗歌带来什么?
文化艺术报:曹谁承认你的《车过黄河》算是有后现代诗的开创意义,只是后来的诗沦为口水诗、打油诗,整体关注屎屁尿的事儿,这样的批评是否客观?
伊沙:本来后现代的口语诗,在正常的古诗里是没有那种轻松愉快的讽刺和调侃。如果说打油诗带来了什么,打油诗带来的正是这个。另外,“口水诗”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对口语诗的蔑称。“口水诗”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口水诗是在口水歌这个概念之后出现的,拿口水歌在歌中的定义来讨论口语诗,是不严谨的。恰恰相反的是,口语诗在中国主流诗歌里是反常的,是别出心裁的。什么是“口水诗”?一般化的抒情诗才是口水诗。所以说,那些污蔑口语诗的人,他们自己首先不够严谨,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1988年,我大四时候写的《车过黄河》,这是我后来道路相当坚定的一个主线,在《车过黄河》这个道路上,我不断地在跨越。而我所理解的美必须是和谐的,黄橙橙的尿液跟黄河和谐度比较大。道在哪里呢?我经常说,“道在屎溺”。大道就是在最平凡的事物中。诗人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是以感觉见长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写的屎尿屁你就堕落了,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也是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事物。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写,如何去呈现它。当一些人,没有任何思想背景而去写这些屎尿屁的时候,就是为脏而脏,哗众取宠。
文化艺术报:您回应曹谁《口语诗是世界潮流,这种土鳖根本不该入诗歌这一行》指出,攻击口语诗的人都是为了蹭新诗百年话题的热度,为了争夺话语权。是不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口语诗的热潮很大程度与《新诗典》有关,很多底层诗人从中脱颖而出,而未能进入者心生愤懑?
伊沙:这也是我一直想回应的一个问题。诗坛的人都很敏感,一到新诗百年的时候,大家都急着回顾这一百年来的新诗,急着做“世纪总结”。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就是口语诗,其实现在说什么话题,都没有口语诗这么有热点性、话题性。
《新诗典》我们已经做了七年半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新诗典》的这七年半,口语诗就没有今天这么强势。和此前我们这些口语诗人居于弱势地位被批不同,这次是口语诗第一次以如此强势的姿态去面对争论。因为,《新诗典》任何一个口语诗人的知名度都要高于曹谁,我们是以绝对的强势去打一场仗。这次如此声势浩大的声讨,在我看来,也是在表扬《新诗典》。是《新诗典》把一帮人做强了,而另一帮很生气。将我形容为掌握诗坛生杀大权的“诗霸”,全球中文诗歌第一平台,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为了做好《新诗典》,我丢失了一些老朋友,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是我已经公平到最大限度了。当然,肯定了一些人,也就有否定一些人的情况,这次在这场争论中曹谁一方的帮手里,有好几位都是给我投过稿的,或者投稿失败的。
文化艺术报:在曹谁批评您的网文下面,有读者留言:“我又想到口语诗:能不能再增加一点美感,哪怕只是一度,就会让99度的水沸腾。”还有,“口语诗能不能再温柔婉约一点,让人看起来不那么僵硬,我想可能是口语诗真正成熟并走向大众的一个标志。”这样的观点,你是否同意?
伊沙:这是对美的认识不一样。比如,我认为尿液和黄河的和谐就是一种美。在时代的变迁里,每个时代对于美的理解也不一样。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是一个美的多元时代。时代越保守越落后越封闭,美的标准越单调,只有在王国,才会人人都爱王子。如果美的标准没有差异化的话,就没有爱情;正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差异,所以爱情才可歌可泣。我们口语诗人也在追求美,只不过我们不想像抒情诗那样陈旧的写法。有时候美就是要有震撼力,是不能勾兑的。
文化艺术报:有网友评价,您的诗作为诗歌来说就是失败的,只是抖机灵,耍小聪明的段子,有点玩世不恭。我又注意到,在真善美中,您似乎更注重“真”表达,您自己的诗学观点是怎样的?
伊沙:我们过去在说真善美的时候,真是善和美的基础,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而现代的一种理论是,我一首诗可以是求美的,另一首诗可以是求真的,所以说,在求真者言真,在求美者言美,在求善者言善。一首诗的容量是有限的,它的企图也不能太大。任何一首诗都要涵盖真善美,这其实是一种虚妄。包括对于善的表达,我们口语诗人在表达善的时候,不是抒情诗那种煽情式的,而是一种节制的、冷叙述的方式,不是一种口号式的善良的表演。
文化艺术报:您之前在文章里说过,最优秀的口语诗人,一定是骨子里的平民主义者,满脑子精英意识是玩不转口语诗的。没有平民主义,就没有口语诗。口语诗是否只能以底层叙述的方式疏离主流之外,才能显示其价值?
伊沙:平民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口语诗人为什么不怕别人说自己浅薄呢?为什么要用大家都能懂得语言说人话呢?口语诗人是“不端着”的,自己把姿态放下来。所以,有些人还再用书面语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诗,可以想象,他相应的世界观里就不会有平民意识。
文化艺术报:有人将您此前的《车过黄河》,视为大陆后现代诗一个重要风向标,其中的句子,“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在网络上已成为励志现代诗句个性签名,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口语诗这样的后现代诗歌以去中心、平面化、反崇高、反优雅等解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也只有保持这样的姿态才能坚守其特点,在当代诗歌中获取一席之地?
伊沙: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它的姿态性肯定是比较强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在黄河上撒一泡尿”是一种姿态。但是,一旦路开启以后,我们就会更自然、更平常,并不需要每首诗都是一个姿态性的动作。当然,姿态性比较强的诗往往容易成为标志性的作品,《车过黄河》就是一个证明。我更多的写日常生活的非常平实的诗,它能够让人理解后现代的口语诗在日常中的状态。事实上,后现代诗写日常生活是它最大的特点,日常生活大部分是平淡的,而这些诗正能够表现出我们所理解的平淡中的美。我们自己其实也在消除自身的姿态化,很深邃的生活之美和诗意,这是我们的追求。
文化艺术报:您与曹谁的论战,有人称之为,揭开新一轮新诗未来发展走向大讨论的序幕,就算曹谁不站出来,别人也会站出来。中国新诗真的到了要讨论何去何从的地步了吗?有人说,中国诗坛应该革除口水诗的弊病,掀起诗学革新,是否有再次革新的必要?
伊沙:我大致回顾一下口语诗的历史,它应该分为前口语和后口语两个时期。像韩东,就是前口语诗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还不是最早的,王小龙是最早的。王小龙的诗最早标注的是1982,韩东和于坚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到1984年,杨黎、李亚伟,这部分诗人出现了。前口语派的诗人,我从来是不予否认你的。我不是口语诗的开创者,只能算是中兴者。开始产生影响,是在1985年—1986年,86年的“两报大展”,不是以口语诗人的身份被大家认识,而是以第三代诗人的身份被认识的。1988年的时候,口语诗迎来了了第一次浪潮。1989年海子死后,海子之死让浪漫主义变成诗坛最大影响力团体,让前口语诗人们“靠边站”了。随后,后口语诗就是从我这里开始了。我从80年代末坚持走口语诗这条路,当然,我比他们要极端。反叛性的,颠覆性的,解构性的这些东西,他们没有我这么极端,我把这定义为后口语。从1988年到现在,我的作品的风格一直是非常稳定的。
从上个月曹谁第一次发抖音发起骂战算起,已经过去一月有余了。但是,论争的一方质量太低,这怎么持续下去呢?双方的学术水平差异太大。如果是论争,双方应该是有来有往,有所撞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双方谁都打不着谁:口语诗一方的理论积淀已经很深厚了,而另一方还是诗歌爱好者。我无法想象,这场大讨论的开始,双方是这样一种水平对比,竟然还掀起了全国的大讨论,还吸引了这么多人参与进来。我怀疑这次论争幕后是有策划人的,从诗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人的水平肯定要比曹谁要高。当这个人现身时,双方才能真正把中国诗坛未来的走向好好讨论一番,这是我看到这次论争积极的一方面。另外,运动式的革新,我们已经不需要了。口语诗人就是日常的革新者,口语诗人天天都在做这件事。如果所有的东西都积压起来的话,那才需要运动式的革新。“润物细无声”式的革新激荡中,口语诗人一直在做。
文化艺术报:您在《中国当代诗歌走向》的一篇发言提纲里,您对从新中国建国之后到新世纪的诗歌史进行了梳理和回顾,那么,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哪里?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伊沙:这个提纲是为中韩诗歌交流会做的发言。创作永远都不可都有一个死板的规划。创作只能说,我现在脚下站在什么地方,大致将走向哪?我只能说,我们现在立足的是“后现代之后”这样一个时空:一方面我们是要救活那些频临死亡的传统,另一方面是进行新的、更大的开拓。创作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探险精神,冒险精神。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转自网络: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615914101820359176/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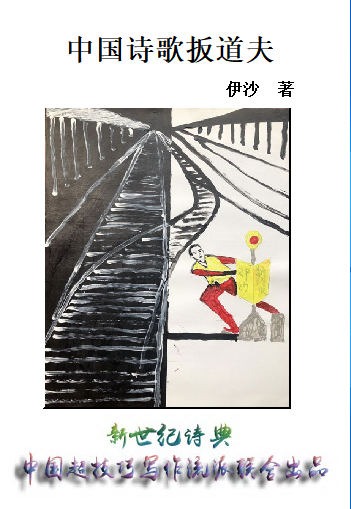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