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岛:那些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

(个人收藏,参考用有利于北岛诗歌批判)
那些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对话北岛------转自南方周末
不能把批评美国变成赞扬自己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写到什么程度了?
北岛:接近尾声了,还要三四个月吧。这本书是从我出生写到1969年上山下乡,侧重童年经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说:人生像彗星一样,头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头部是童年时期,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说得好像挺邪乎,其实很有道理。回顾童年,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早已被决定了。记忆像迷宫的门,追溯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开门的过程。
人物周刊:以后会写自传吗?
北岛:大概不会真的写自传。我今年60岁,可分为3段:出生到20岁开始写诗,这是第一段;20岁到40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阶段;40岁那年开始漂泊至今,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阶段很清晰,这样交代起来省事。
今天编辑部组织的郊游。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1970年代末,创刊时期的芒克和北岛
人物周刊:漂泊了这么多年,中间回过几次北京?
北岛:从1989年到现在回过5次,每次不能超过一个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从父亲病危到安葬。2001年底是13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动最大。北京完全变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联系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让我痛苦,好像在故乡反而迷失了,连自己的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或有人陪着。这倒也好,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人物周刊: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北岛: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的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
人物周刊:在美国时也批评美国主流文化吗?
北岛:当然。在一个社会生活久了,如果没发现任何问题,就说明你有问题了。但我觉得,谈论一个国家,最好能放在这个国家的语境中——脱离这个语境很难理清来龙去脉。我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民主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重。
人物周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民主是很欣赏的。
北岛: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和每个人的阅历、知识背景有关,立场观点像光谱那样复杂,很难简单分类。我看过《民主四讲》(作者持新左派立场),很多地方讲得是对的,但不能把对美国制度的批评简单地转化成自我颂扬。美国民主制度是有种种问题,但并不能反证中国的现状就是好的。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肯认真反省这60年,将来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权贵还是大众。
人物周刊:您的文集近年在大陆陆续出版,有删改情况吗?
北岛:最近出香港牛津版5卷本,编辑和我共同校对,才发现大陆的每本散文集都删了上百处。有些出版社,如三联,就做得比较好,《七十年代》删节得很少。
“文革”中的地下文化运动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算是对少年时代经历的反省吗?
北岛:1966年我17岁,曾很深地卷进“文革”的浪潮中。我想探讨的是一个少年在“文革”中的成长经验,包括对当时狂热的忏悔。我最近刚完成的这篇是《北京四中》。四中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其中潜藏和爆发的危机也很有代表性。在我看来实际上有两个四中:一个是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贵族”四中,一个是以思想文化为动力的“平民”四中。这种内在的分裂在“文革”前被所谓“平等意识”掩盖了,而“文革”不仅暴露,甚至加深了这种对立,鸿沟一直延伸到现在,双方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恰好与当今的政治、社会形态挂上了钩。
人物周刊: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评价反差特别大。《七十年代》里,徐冰和陈丹青的观点就很不同。
北岛:这也正是我们编辑《七十年代》的意图之一。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很接近——上山下乡、自学,还有来自底层的社会经验,但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观点。这种矛盾恰好构成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我觉得徐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简单否定,而是把看来愚昧的东西转化成营养,转化成再创造的可能。比如正是由于读书被禁,人们反而产生精神上的饥渴。一本书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专制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是单向的,而消费主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人物周刊:对您这代人来说,反抗是必然的选择吗?
北岛:到7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绝境,这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其实对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还远没有说透,往往还停留在肤浅而简单化的陈词滥调之中。我跟朋友建议做《六十年代》,那是埋下种子的时段,也就是所谓童年经验。70年代是破土与艰难生长的过程。你也可以把这一过程叫做反抗。60年代末,即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有个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食指。他这颗种子和大地的关系有点儿特别。他是红卫兵运动走向高潮时开始失落的,他的代表作《鱼群三部曲》描述的就是这一点。而恰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把他的诗带向四面八方。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食指一下触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关。如果说反抗是某种必然,那么反抗是否都能开花结果就难说了。这背后的复杂性需要好好梳理。
人物周刊:您是当年地下文化的见证者,能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的文化圈子吗?
北岛:打个比方,北京的文化圈子有点儿像大小涟漪,扩张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涟漪,最终才能兴风作浪。比如我先在几个同班同学组成的小圈子混,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芒克、彭刚和多多等人,他们都属于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渊,当时只是20岁出头的女孩。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现象,她扮演着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样的沙龙女主人的角色,指点江山,说谁成谁就成。说到底,这也是中国革命带来的结果,胆大,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中办过地下画展,还投票选出最佳作品。而像这样的沙龙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被忽略了。《七十年代》正打算出下一卷,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再现这些被忽略的细节,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历史质感。
恢复现代汉语的尊严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自己早年的诗作,包括它们和当时的政治之间的张力?
北岛:我没有保留最初的诗稿,但我还能记得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在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压力下,我们这代人存在着虚无颓废的倾向,那首诗针对的是这一倾向,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当时就有个朋友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我早期写作中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其实《回答》也还是有道德说教的影子,只不过在反抗的姿态中似乎被掩盖了。《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第二年春天被《诗刊》转载。由于过于鲜明的政治反抗色彩,为安全起见,发表时标的创作时间是1976年。
人物周刊:您的诗从一开始就具有启蒙色彩,怎么看这种启蒙者的身份?
北岛:启蒙者都喜欢道德说教,这大概就是症结所在。其实我在我们那代人中是比较笨的,是需要被启蒙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笔名根子),横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坛全都震住了。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自70年代初以来现代诗歌的开端。当然,由于他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很早接触到西方诗歌。所谓白洋淀诗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响。
人物周刊:《回答》影响了一代人,您却说要对它要有一个反省,反省什么?
北岛:对抗是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官方话语到“文革”算是走到了头,甚至所有词与物的关系都被确定了。1972年初,我写了首诗《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树缝中游窜”。我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让我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的呢?如果说这40年来,我们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恢复了现代汉语的尊严,值得骄傲,那同时我们也很可悲,因为我们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扮演的是“低级侍从”的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只会行走,不会飞翔;只会战斗,不会做梦。放在这样的语境中,你就会明白我对《回答》的不满了。
人物周刊:1979年,官方刊物发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响,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北岛:《诗刊》给了我9块钱稿费,我请当时办《今天》的朋友们撮了顿。这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感觉?
北岛:什么是时代前沿?在《今天》出现前我们其实都很消沉,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刚一起喝酒,从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到中国的未来。我们发誓,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为之献身。四中有个同学叫张育海,70年代初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他临死前不久,曾给同学写了封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有了机会由于没做好准备,往往错过。这封信在知青中流传甚广,对我影响很大。十年磨一剑,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现在看来,我们准备得很不够,否则还应该走得更远些。
人物周刊:官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岛:在今天,官方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比如不少现当代文学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关于《今天》及地下文学的回忆录,在报刊上有关于《今天》的访谈等。这并不等于得到承认,当然承认不承认没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回顾当年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已恍如隔世。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当时主管文艺的官员及其理论家,他们组织人马大力“推广”“今天派”(“朦胧派”)诗歌,让它们深入人心,功不可没。
商业化出现以后这代人纷纷落马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时代的压力与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北岛:对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压力有时反倒是更大的压力。关键是作家是否能将压力转化并升华为写作的动力与资源。或许最值得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这真得感谢“文革”,正是由于“文革”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带来我们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偏离,我们这帮人有了新的创造空间,这恐怕是祖辈、后代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如今这传统又回到老路上,每个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阴影中。看看那些文人为蝇头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就是明证。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人物周刊:听说您跟中国电影界的人很熟。
北岛:我认识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时,他们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地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细节。他参与过《今天》的活动,发过短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负责张贴海报、代售刊物。总体而言,我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了。可惜。恐怕只有田壮壮是个例外,他还在孤军奋战。
前两年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教中国当代电影,觉得还是《黄土地》好。我真纳闷,难道“第五代”不但没长进,反而倒退了吗?他们后来的电影你可以看出不断妥协让步放弃的过程,直到完全从艺术中撤离。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
这又回到刚才提到的张玉海的那句话: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没有准备,有了机会也往往错过。不能说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识不完整,信念不坚定,一句话,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所以走不了多远。再赶上商业化——活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钱,于是纷纷落马。从70年代末开始,包括《今天》、“星星”、四月影会、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寻根文学、试验小说,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由于准备不足,这能量没持续多久就衰败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和艾青曾关系很近,后来出现分歧。能说说这段公案吗?
北岛:说来话长。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政治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出了门,《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对随行的年轻编辑(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说,艾青今天涉及北岛的话要全部删掉。她的职业道德多少保护了我。
我和艾青是他1976年从新疆到北京治眼病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白塔寺的一个小院里,单间,上下铺,他们夫妇和两个儿子挤在一间小屋。我跟艾未未很要好,我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的封面是他手绘制作的,总共100本。其中《太阳城札记》中的最后一节是“生活·网”,艾青到处公开引用批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强调这是一首组诗中的一小节,你要批评,也应说明原委。我接着说,你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对我们的写作应持有宽容公正的态度。收到此信,艾青给我打电话,我们几乎就在电话里吵起来。其实我和不少前辈都成了忘年之交。70年代是两代人互动交错的特殊时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很遗憾,我和艾青的关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人物周刊: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北岛:在西方普遍是20年一代,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变化太快,代与代之间被压缩了,有人说5年一代,有人说10年一代。总之由于距离太近,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就更显而易见。
超时了,掏出手枪,接着读
人物周刊:1989年之后,您开始了在海外的漂泊,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北岛:我算比较幸运的,最初有奖学金,后来混到大学教书。我生存能力比较强。刚到国外的那几年,一直拒绝学外语,直到1993年去美国,才真正感到语言的压力。我用英文教诗歌写作,胆儿够大的。每天花大量时间读英文备课,最麻烦的是看不懂学生的作业,诗歌的词汇量大,一个词卡住就无法继续分析。后来买到一种扫描笔,碰到生祠一扫就出现中文解释,我管它叫“扫盲笔”,这玩意儿可救了我。我上课时跟学生说,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人物周刊:生活上的压力有多大?
北岛:在国外生活需要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台湾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比专制还厉害——老虎猛于苛政。幸好“美国之音”约我写《作家手记》,救我于水生火热中,还逼出写散文的能力。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
人物周刊:朗诵也用英文吗?
北岛:我一直坚持用中文朗诵诗歌,用英文朗诵散文。因为中文是我诗歌的身份,不能放弃。在美国的大学系统,英文系几乎都设有创作课,由诗人作家担任教授,与创作课配套的是朗诵系列。互相请来请去,这是美国诗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人物周刊:在《朗诵记》中,您提到过一些奇闻轶事,特别有意思,还能说一些吗?
北岛:朗诵会一般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由于诗人的EGO太强,常常会尽量多占领舞台,夺走别人朗诵的时间。我认识一个叫乔治的美国诗人,当过兵,参加过越战,因反战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来又去日本学武术。有一回,他在旧金参加一个朗诵会,坐他旁边的是个黑人诗人,人高马大,而乔治比较矮小。台上小说家正在朗诵,规定每人为20分钟,那家伙念了45分钟还没完。可把乔治激怒了,他跟那位黑人诗人商量,上台揍他一顿,乔治打下三路,黑人打上三路。台上那家伙预感到了,先从书包里取出个木盒,再从里边掏出手枪,边读边挥着手枪,把大家全镇了。他一口气朗诵了一个半钟头,然后收起手枪,扬长而去。
人物周刊:2007年底您开始定居香港,香港对您意味着什么?
北岛:我感谢香港收留了我。香港多年来收留过很多人,包括孙中山。虽是弹丸之地,却提供了另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形态。当然香港有香港的问题。教书时,我发现我学生的外国诗歌知识几乎是零,让我大吃一惊。所以我们正筹备“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人物周刊:是什么帮您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北岛:第一是写作。写作首先是与自己对话,相当于心理治疗。在写作中,你才会不断重新定位,确定生存的意义。第二是对家人、朋友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对女儿的责任。第三就是喝酒。
人物周刊:想过别的选择吗?
北岛:在绝望时刻,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每过一关都是胜利,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最幸福的时刻。
北岛: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现在我已到了耳顺之年,生命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不再为生计发愁。我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
转自网络:https://www.douban.com/note/188340412/?from=author&_i=70170990Qj3gcu,77377130Qj3gcu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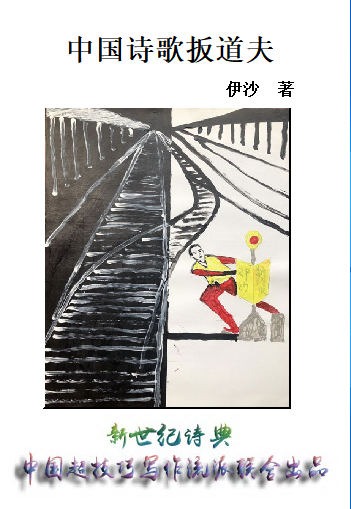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