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骆一禾诗学建构的存在主义路径:“与闻于世界之创造”

论骆一禾诗学建构的存在主义路径:“与闻于世界之创造”
内容摘要:骆一禾与存在主义思想的遭遇对他的诗学建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诗论充满存在主义因素,但对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诗乃是‘创世’的‘是’”则将希腊哲学传统与希伯来宗教传统结合了起来,是借西方传统而完成的诗学思想。以海德格尔为中介,骆一禾进入了荷尔德林浪漫诗学的核心,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新浪漫主义诗学。其诗歌创作表现出诗歌隐喻与哲学概念之间的张力。骆一禾经由1960年代的“内部读物”《存在主义哲学》而完成的诗学转化也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骆一禾 雅斯贝尔斯 海德格尔 存在主义 新浪漫主义
一 、骆一禾与存在主义的遭遇
骆一禾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趣值得关注。他两次在给张玞的情书中谈到过一本书:“那本《存在主义哲学》看得我好吃力,现在还没看完海德格尔,但是,这些论文写得虽难,却是让人动脑筋的难。让人有兴趣读,你到时续借一些日子”(1984年1月4日),另一次说:“我看完《存在主义哲学》就写《海淀》和《长水了》,说来你可能觉得好笑,我看了《存在主义哲学》这本书,好像无形中支持了我的某些想法”(1984年3月7日),中间相隔了两个月,骆一禾对这本书的阅读应该很认真。
然而,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经查,大陆出版的名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书一共有两本,一本是由徐崇温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内容大致分为导论、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存在主义在西方各国等,这本书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于1986年,骆一禾写信时不可能看到。而另一本《存在主义哲学》则是1963年出版的“内部读物”,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属于“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中的一种。大陆外倒是有劳思光独力撰写的专著《存在主义哲学》,论海德格尔的部分在第五章,其体例类似于徐崇温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但篇幅仅有两百页且带有一定的绍介性质。大陆出版的两本《存在主义哲学》都是五六百页的长篇巨制。1963年的内部读物《存在主义哲学》其实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论文(节选)汇编,开头就是海德格尔的两篇论文《存在与时间》(节选)和《论人道主义》,这也和骆一禾的阅读感受一致。
半年之后,在给张玞的一封长信中,骆一禾又一次援引了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核心概念,可以表明他阅读的正是这本《存在主义哲学》。他借叶嘉莹在《迦陵论词从稿》中对温庭筠等词人的评价展开了自己对文学批评方法的思考,骆一禾谈到了叶嘉莹与克罗齐批评方法的相似,并进一步借用存在主义思想家批判了克罗齐的概念:“实际上,直觉美学的核心是:直觉即表现即联想即心灵活动,是整合的,直觉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观照,而是心灵的活动。哲学地说,不要直觉地看待心灵活动,而要心灵活动地看待直觉。换句话说,应该把心灵活动看成是‘无所不包’(海德格尔)看成是‘大全’(雅斯贝尔斯)”(1984年10月9日)。这一具有深度的美学批判不仅表露出他已开始成熟的批评天才尤其方法论思考,而且也流露了他个人的诗学观念和未来的诗学路径,在信的结尾部分他仍借温庭筠说:“当问题被视为心灵活动的不足时,词人温庭筠艺术人格,艺术气质和艺术内形式的匮乏也就进入了视野……温庭筠是一个东方词人,他的艺术得失不在于他的观相,而在于这种观相本身不是一种与心灵活动浑一的观相,这是远远低于东方诗词伟大作品的所在。”这些观点无疑都体现了骆一禾的批评独创性。然而,他援引的存在主义概念就出自《存在主义哲学》这本书:
……对我们来说,存在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是没封闭的;它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而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它永远让我们发现还另有新的有规定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前进不已的认识进程。当我们在这个进程中反思的时候,我们就不免要追问什么是存在自身,因为它在一切逐步显現的东西都显現了以后似乎永远只往后退,远离我们。这个存在,我们称之为无所不包者,或大全(das Umgreifende);它不是我们某一时候的知识所达到的视野边际,而是一种永远看也看不見的视野边际,却倒一切新的视野边际又都是从它那里产生出来。
“无所不包者”和“大全”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和骆一禾那句话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字面上都非常相似。显然,骆一禾半年后记忆有误,才把“无所不包”当成了海德格尔的概念。但这些援引或误引无伤大雅,它们都表明了骆一禾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直接影响了骆一禾的诗学批评和诗学观点,使骆一禾表现出一种以“心灵”接近“大全”的特征。
骆一禾的其他概念或论断也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关,诸如诗是“‘它在’的蛮貊之音”、“它在的语言”、“它在的显示”以及“诗是‘创世’的‘是’字”等。它们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联系不是特别明显,而是经过了骆一禾诗学思想的转化,是需要我们细致辨析的。
二 、骆一禾诗学中的存在主义因素
诚然,众多思想家在骆一禾诗学形成中发挥了作用,诸如斯宾格勒、容格、汤因比。然而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影响却被忽略。实际上,在骆一禾的诗论和诗歌批评中常能够看到存在主义的思想因素。其中,雅斯贝尔斯的核心概念“大全”显然是骆一禾钟情的思想,甚至直接促成了骆一禾“诗歌共时体”、“诗歌心象学”概念的产生,骆一禾在《火光》中如是论述:
世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不仅是一个诗学的范畴,它意味着创作活动所具有的一个更为丰富和渊广的潜在的精神层面,在这个层面自我的价值隆起绝非自我中心主义、唯我论的隆起,从这个精神层面里,生命的放射席卷着来自幽深的声音,有另外的黑暗之中的手臂将它的语言交响于本于我的语言之中,这是一种“它在”的显现……并非只是某种知识渊博的结果,而是生命潜层、它在的语言,一种自身的未竟追蹑未竟之地的探求之声留下的痕迹。这时候,那些容格称为阴影、阿尼姆斯、阿尼玛和自性的层面进入了生命之中,不可说的进入了可说的。我想,所谓“生命自身”乃是一个“生命构造”,诗人所看到和触及的是这个大全,它是“世界”这个词汇里所蕴含的本义……诗人触及了大全、生命构造而不可化学式地“还原为人”…………诗歌心象将同一因素的静态解放为活的动势,从而诗学属性里深植着有人的和众神的诗学成分。
在骆一禾看来,生命、世界、大全这些词汇可以彼此代替,但他又着重强调了“大全”这一概念带来的存在论视野。正是雅斯贝尔斯建议以“大全”取代“存在”这一古老的概念,理由如下:“不论什么,凡是对我来说成为对象的,它就是许多其他存在中的一个有规定的存在,它就只是存在的一个方式。当我思维存在的时候,比如说,把它当作物质,当作能力,当作精神,当作生命,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可以思维的范畴都已尝试过了——我最后总是发现我已把出现于整个存在之内的某一有规定的存在方式绝对化了,使之成为存在自身。但是,任何被认识了的存在,都不是存在本身。(das Sein)”而大全这一概念则有许多优点:“大全是那样一种东西,它永远仅仅透露一些关于它自身的消息——通过客观存在着的东西和视野的边际透露出来——,但它从来不成为对象。它是那样一种东西,它自身并不显现,而一切别的东西却在它的里面对我们显现出来。它同时又是那样一种东西,由于它,一切事物不仅成为它们各自直接显现的那个样子,而且还都继续是透明的。”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存在是指无所不包的大全所代表的那个至大无外的空间,在这里面,为我的存在,对我们当下现在着。”骆一禾后来在向张玞解释《世界的血》长诗构想时这样谈到“大全”:“……我把‘生命自身’看作是‘生命结构’,从而也就是说,诗人所说的‘生命’不是苍生一芥,而是深层构造的统摄和大全,因此个体的能力遂不呈封闭状,这是‘天才’的生命形态的本质。血、文化、世界也就并非隔绝了。”骆一禾一定注意到了(das Umgreifende)的不同译名,在《存在主义哲学》这本属于“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内部读物”中,它被译为“大全”,这一概念后来又被译为“统摄”。骆一禾无疑对大全这一译名情有独钟。或许在他看来,“大全”这一概念也适合于诗的本体论,虽然它本来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概念。在骆一禾看来,“大全”显然应该是诗人心灵的活动范围。
雅斯贝尔斯谈到了大全的几种样式,从一般的大全里分解出“世界”和“一般意识”,但不管“世界”还是“一般意识”都是“内在存在”,因而还存在着一个从内在存在达到超越存在的过程。这一过程雅斯贝尔斯称之为向上飞跃:“事实上,人已经完成了他从内在存在出发的向上飞跃,那就是,从世界向上帝和从自觉的精神的实存向生存的飞跃。生存乃是自身存在,它跟它自己发生关系并在其自身中与超越存在发生关系,它知道它自己是由超越存在所给予,并且以超越存在为根据。”这应该是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内涵,在他眼中,“生存”这一概念应该取代“存在”,并由此摆脱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二元论思维,后者进一步孽生了现代的科学主义。这一向超越存在飞跃的思想对骆一禾影响极深。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个飞跃决定着我的自由。因为自由是通过超越而达到超越存在。”因而产生了相对的自由、否定的自由(思维的自由),而肯定的自由则“只产生于在飞跃中所达到的生存(Existenz)”。骆一禾同样谈到了自由的问题:“自我的发展,沿着觉醒的上冲曲线不断扬弃着大地——或我们无论用什么名字去称谓它——而形成着自由。……人于他的基本状态分解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往来成为一种主观与客观的折射投影,从而把浓密的、厚实的、不可化解的人分析开来——把不断地生长(becoming)变为存在物(becomed things),从而堆积了大量的抽象物和社会抽象体,同时在上冲力的曲线上,把人抛入了空中:孤独、荒诞、可怕的自由。人和背景的脱节。……也无法了解歌德所说的‘一种霹雳,把我推坠在万丈深坑’的事实是从何而来。……把孤独当作上帝以修饰自己……我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描写自我与孤独两个母题”,值得注意的是,骆一禾的诗论既有一种雅斯贝尔斯式的对于“现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揭示,也就是社会思想批判,同时也有一种对当代诗歌写作状况的诊断或症候性分析。
在社会批判的意义上,骆一禾谈到的自由问题尤其自由的两重性让人想到雅斯贝尔斯“论自由的危险与机会”一类表述,当然他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关心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迷失于客观事物的思维转变为发自无所不包的大全的思维。当我们涉及到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在行动上和思维上同时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向度……我们就跟我们的意愿之所自出的那个无条件者(Unbedingte)合二为一。……自由、对无条件者的了然或明亮、与自身存在的本质相交往,——此三者是同一回事。”而在诗学诊断的意义上,骆一禾的判断更是针对当时国内的写作状况有感而发,尤其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对现代主义趣味的盲目追求,诸如自我与孤独、非理性、“本能和深层潜意识写作”、“死亡拜物教”甚至“裸露丑”等等,骆一禾一律视之为“艺术思维中的惯性”,这是极为有力的诗学批判。他同样也反感唯现代主义马首是瞻的“线性思维惯性及单一进化论”。骆一禾给友人的书信不乏这样的诗学诊断。
对于骆一禾来说,只有肯定的自由才能引领诗人达到生命本原,他由此深化了诗坛流行的语言陌生化原则,“偏离习惯联想规则务去陈言是一个向度,而它也包含着超越旧有感性积淀,直达生命本原的努力,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和指归”。雅斯贝尔斯借谢林“与闻于世界之创造(Mitwissenschaft mit der Schöpfung)”的隽语来论述进入大全或本原的努力:“在我们的根源里我们曾经参与或知道万物的本原,而在我们的世界这个窄狭范围里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从事哲学思维活动,就在于唤醒我们的回忆,从而让我们返回本原。”“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或许我在我自己的实质之丧失中体会到虚无,或许我在我之被赠与性 (Mitgeschenktwerden)中体到大全的充实。……但是因为人决不仅只是手段,而永远同时是终极目标,所以从事哲学思维的人,面对着上述的两种可能性,在虚无的经常威胁下,总愿意体会到出之于本原的充实。”雅斯贝尔斯创造不同的哲学概念并设定一套哲学思维程序以返回本原,而骆一禾则必须要在诗学体验和建构中获得这一点,他说:
……诗歌是一未竟之地,或它从未竟而来。……诗歌之垂直是未竟之地踵身而下,进入我们的渊薮。它是称为“上帝”和称为“本无”的本体的通明,其间不乏充满了危险的、一连串魅惑的漩涡。诗人与未竟之地之间,以他的创造发现表示了不同的价值隆起。在伟大的诗歌共时体中,它们确实不是一种进化或顶替,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做的是把阿波罗神庙祭祀的预言改编成诗歌,他的这一举动意味着这样的心象“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一首诗”,埃利蒂斯说:“诗从哲学终止的地方开始”,这是一种世代的合唱,如果不同的诗歌创造力型态不是混淆的话,它们哪个反对哪个?——这样我感到创作的真正艰难。
“未竟之地”应该是大全、本原的另一种说法。在这段话中,骆一禾模仿博尔赫斯“神的文字与我们垂直”的说法而论断道:“诗歌的未竟之地的属性,与我们是一种垂直关系”,显然骆一禾认为诗人应该是诗的工具,原因在于诗人触及了“大全”这一更高的精神力量,“大全”甚至对他构成了一种压力,于是出现了被动的诗人形象,骆一禾将“神来之笔”视为一种“语言超前性”并论断说:“从整个诗的创作活动来说,如果整个精神世界活动不能运作起来,这种语言超前性是不会产生的,它是一种加速度,是为精神运作的劳动提供的速度驱动的,它是精神活动逼近生命本身时,生命自身的钢花焰火和速度,这里呈现给我们以生命自明中心吹入我们个体的气息”,其中存在着一种极为紧迫的被动性,犹如雅斯贝尔斯论述到的“人的可能性”:“由于体会到大全而产生出可以无限进展的洞见能力和心愿。这样,在大全中的存在就从一切起原上走向我,呈现在我面前。我自己就变成为被赠与给我的我。”而诗人的任务即在于“以我的自身未竟进入未竟之地”。骆一禾这句堪称经典的表述中蕴含的深刻洞察,“称为‘上帝’和称为‘本无’的本体的通明”,其灵感来源于何处呢?在《存在主义哲学》收录的《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一文中,雅斯贝尔斯如是论述:“我们通过哲学思维,我们就得到确信,不是相信上帝,就是相信虚无。可是‘要么就是上帝,要么就是虚无’这个非此即彼,却被神学家们改换成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非此即彼:‘要么就是基督,要么就是虚无’。”这也许给了骆一禾以启发。其实,“上帝或虚无”这样的表达式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话说回来,骆一禾认为存在着不同的诗歌创造力型态,并将诗歌的历史看作“世代的合唱”,都源于他从根本上将诗歌视为“返回本原”的努力。他有关“诗歌共时体”、“诗歌心象学”的概念也是如此。由于建立了与大全、本原或未竟之地的关联,自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诗歌乃是一个集合概念”,并且,诗歌首先是“我们精神中的诗歌心象”。
三 、诗乃是“创世”的“是”
相比于《美神》(1987年),骆一禾的最后一篇诗论《火光》(1989)更多凸显了他与存在主义的关联。其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如果不了解骆一禾早年阅读的存在主义哲学背景,它甚至是晦涩难解的:
诗歌是使我写作的力量,它不是写作的结果,我听到一个声音说:“在这样的说之外不该有对于它的说了”,在创作活动范围内而不是诗学所说的诗,具有这个本性,当我们认识和判断什么东西时,便要使用“是”这个词语,“它是诗”或“它不是诗”,而诗正是说这个使其他的得以彰显的、照亮的“是”,“是”作为贯通可说的不可说的、使之可以成立的记号,是更深邃的根子,诗歌就是“是”本身,而未竟之地在这里打开。在《圣经·旧约·创世纪》的第一章里,有一些段落带有“神说”的记号,创世行为以“神说”来给标志揭示,万物万灵不仅长在天空、大地、海洋,也是长在“神说”里的,诗歌作为“是”的性质在此可以见出,而不带有“神说”记号的段落由三句伟大诗歌构成:“起初,神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这里诗、“创作”已成为“创世”的开头,诗歌使创世行为与创作行为相迴,它乃是“创世”的“是”字。——这样在“是”里我们也看到了它具有的“创作”和“创世”的无止境,那人类以自身的未竟追蹑未竟之地的活动,就涌现在我的面前。
这段话中首先谈到了诗人的被动性,而后涉及到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本性”,然而紧接着“是”这个词却发生了转义或意义变化,“是”本身作为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被确立了起来。“是”其实是骆一禾对“在”/“存在”这一哲学概念在汉语中的诗性模仿,抑或说对“在”/“存在”(Das Sein)的另一个译名。否则,骆一禾所说“诗歌……乃是‘创世’的‘是’字”就是缺少根据因而不可靠的个人化表达,徒然显露了作者在遣词造句时的权力意志的随意性。虽然我们明白这段话将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结合了起来,但仍然对骆一禾如此表述的原因不甚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将其追溯到西方哲学概念的语文学和词源学考察的话。实际上,骆一禾如此表述的灵感可能正得自于他对《存在主义哲学》一书所收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一文的阅读,后者谈到了对Das Sein(存在/在/是)这一概念的取舍:
在《存在与时间》(第212页)中有意而且小心地写道:il y a l’être:“es gibt”das Sein(“有”在)。用il y a去译“es gibt”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此“有”者就是在本身。这个“有”却是指称那有着而又维持着自己的真理的在的本质的。这个和在的本质本身一起有出来的东西就是在本身。
同时却要用“有”这个字,以求暂时避免这样的讲法:“在在”;因为通常是用“在”这个字来谈在着的东西。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在者。但在恰恰不“是”“在者”。如果不加进一步的限制而即用“是”来谈在,那么在就太容易被按照众所周知的在者的样式设想为一个“在者”了,这个在者就是作为原因起作用与作为结果接受作用的那种在者。
在《存在主义哲学》的简短前言中,编者贺麟也谈到了各位译者对这一哲学基本概念的译名不尽相同,但全书保留了这些译名的差异。骆一禾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引用了巴门尼德“在就是在”的希腊语原文后说:“也许‘是’这个字以恰当的方式只能用来谈在,所以一切在者其实都不而且从来不‘是’。但因为思才刚要争取能就在的真理来谈在,而不是从在者来把在解释得像个在者一样,所以还必须让思便于细心地去想想:在是否在以及如何在。”毫无疑问,在对哲学文本的阅读中,骆一禾体会到了西方语言尤其德语中作为哲学概念的“在/是”:“我们的动词‘存在’(Sein,也包括印欧语系里其他的对应语言)的最重要的意义和功能是:1.表达‘存在’、‘实存’;2.用作系动词。”而骆一禾索性以“是”来代替“在”,体现了他对诗歌与哲学运作方式不同的考虑,“是”在现代汉语中也不妨承担这两种意义和功能。骆一禾对“是”一词的匠心独造,不仅仅是对海德格尔“诗化哲学”的接近,更是一种融合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独特诗学建构。有趣的是,《存在主义哲学》中收录的《存在与时间》节选和《论人道主义》这两篇文章正是由海德格尔的亲炙弟子熊伟翻译。从熊伟到骆一禾的转换,应该说是从哲学到诗学的转换,这一思想的传奇,同时构成了存在主义在中国颇为有趣的变形记之一。可以肯定的是,熊伟的海德格尔译文对骆一禾建构自己的诗学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骆一禾并非直接袭取了海德格尔,而是使后者融入自己的诗学发展过程之中,从而生成了一种独特的诗学模式。如果不知晓骆一禾在八十年代的阅读情况——这一点由新近出版的《骆一禾情书》所透露——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诗学思想的灵感来源所在。骆一禾的诗学表述新颖而准确:“‘创作’”已成为‘创世’的开口,诗歌使创世行为与创作行为相迴,它乃是‘创世’的‘是’字。——这样在‘是’里我们也看到了它具有的‘创作’和‘创世’的无止境,那人类以自身的未竟追蹑未竟之地的活动,就涌现在我的面前。”这既是他对圣经《创世纪》开头一段话的阐释,同时也是他有关“创造”的诗学表达,显然骆一禾认为诗人的创造可以与神的创造相比附,这个世界的创造尚未完成,所以才需要诗人的语言创造来参与世界的创造。骆一禾的这段话其实也将希腊的哲学传统与希伯来传统结合了起来,是一个中国诗人借西方传统而完成的独特诗学思想的表达。细究来说,此处的“是”即为存在(das Sein),有存在者之存在(das Sein des Seienden)的含义,“未竟之地”则类乎雅斯贝尔斯的“大全”。这就将诗人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赋予了诗歌以崇高的含义。从总体上可以说,骆一禾将海德格尔式的诗化哲学转变为了对诗的本体(论)的洞察。而诗歌的本体论绝不仅仅是对语言本体的探讨,后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主要的诗歌潮流;在这个意义上,骆一禾也完成了对八十年代语言诗学思想的超越;虽然他在诗论中也极力强调语言在创造中扮演的作用,他对节奏、音乐性的讨论可以表明这一点。
四、从存在主义到新浪漫主义
骆一禾在1983年计划写一篇两万字的《人道主义提纲》,他几乎同时对海德格尔的《论人道主义》发生兴趣并非偶然。实际上,可能正是海德格尔的《论人道主义》,使骆一禾放弃了《人道主义提纲》这一宏伟的写作计划,这不仅是因为在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一文中,人道主义的内涵发生了极大变化,甚至不成其为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人道主义,还因为《论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海德格尔从逻各斯向后期语言思想的转向,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骆一禾诗学思想的形成,对骆一禾来说,这种诗学建构较人道主义的思想争论可能更有吸引力。作为诗人,他肯定更多视诗学为职责或天命所在,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在他的诗学建构中始终萦绕着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思想氛围。
在骆一禾这里,应该发生了一个和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类似的思想过程,即将人道与存在的真理联系起来,海德格尔说:“人的本质基于存在。事情主要在于此存在,这就是说,从在本身方面来存在,而此时在就在作为存在着的人的人们中为看护在的真理而实现到在的真理本身中去。假若我们决心坚持‘人道主义’这个词的话,那么现在‘人道主义’的意思就是:人的本质是为在的真理而有重要意义的,所以,事情因此恰恰不是视仅仅是人的人而定。我们正这样思一个稀罕种类的‘人道主义’。这个词成为一个文不对题的名称。”“思在的真理,这同时就叫做:思人道的人的人道。主要的事是人道,要从在的真理着想,却不要形而上学意义之下的人道主义。”进而转变为对思、在与诗的关系的探讨:“思在其说中只把在的没有说的话形诸语言。”以与“在”的关系而言,诗甚至比思更为优越:“诗的创作和思一样以同一方式面对着同一问题。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讲的一句几乎未被深思过的话仍然还适用,他说作诗比在者的探究更真。”这个时候语言凸显了出来,“一切都只系于在的真理形诸语言而思进入语言。”这些讨论,与骆一禾对大全(生命)、思想与诗的关系的思考极为相似:“语言中的生命的自明性的获得,也就是语言的创造。……当没有艺术思维中一系列思想活动作为压强和造型的动力时,固有的词符是没有魔力的,必须将它置于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这置入的力量前已所述:生命自明),它本身的魔力才会像被祝颂的咒语一样彰显出来,成为光明的述说,才能显示其躯骸,吹息迸射而有其身。这一叙述的过程,实际上与我们所有的思索,所有超出自我、追蹑美神、人类思乡的精神活动,乃是一种同步的过程,而不是绝缘于这一切的,思想也不是诗之外的一种修养。”骆一禾甚至写了题为《为美而想》的诗,不妨全文引用如下:
在五月里一块大岩石旁边
我想到美
河流不远,靠在一块紫色的大岩石旁边
我想到美,雷电闪在离寂静不远的
地方
有一片晒烫的地衣
闪耀着翅膀
在暴力中吸上岩层
那只在深红色五月的青苔上
孜孜不倦的公蜂
是背着美的呀
在五月里一块大岩石的旁边
我感到岩石下面的目的。
有一层沉思在为美而冥想
沉思是为诗而准备,正如哲学是诗的准备。可与骆一禾的诗论相对照:“诗必然完成在语言创造中。最重要的不是依循前定的艺术规则,使用某种艺术手法,而是使整个精神世界通明净化。在写一首诗的活动中,诗化的首先是精神本身。……沉思不是谛视自己的一种逻辑或一个结论,而是一种能力,当意识深层的原生质,最富创造力的瞬间闪耀时,它使其辉煌并把握它们最完美的状态。”相比于海德格尔,骆一禾显然更关注诗的创作过程。
骆一禾对诗歌创作活动的解释,“诗歌心象将同一因素的静态解放为活的动势,从而诗学属性里深植着有人的和众神的诗学成分”,应该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论述有关:“荷尔德林对希腊文化的关系是在本质上和人道主义不同的东西。”在《论人道主义》中,海德格尔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赫拉克利特的箴言:“居留对人说来就是为神的在场而敞开的东西。”这不仅意味着希腊文化的指向,同时也是荷尔德林诗学的指向。海德格尔对“形诸语言”的论述,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自己1936年就荷尔德林“然而有诗意地居住”一诗所作演讲的再阐释:“在此用的‘形诸语言’的讲法现在要完全照着字面来掌握。在恬然澄明地来到语言。在总是在来到语言的途中。这个来到的东西把存在着的思从它那方面在它的说中形诸语言。于是这个语言本身被举入在的澄明中。于是语言才以那种十分神秘却完全支配着我们的方式在。”“形诸语言”在骆一禾这里变成了“语言创造”,而其背后的支撑用骆一禾的话说则是“精神诗化”。从创作的结果来看,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这样,语言才不是一道屏障,而是我们的头脑的思维与大化的存在合为整体,体验生命并自明了它的存在。”究其原因是因为“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生命作为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这些雅斯贝尔斯式的论述表明,骆一禾所说的生命不过是存在、大全的另一个同义语。可以说,经由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中介,骆一禾其实接触到了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但最终形成了一种多少充满人道关怀——考虑到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张力——的中国式的新浪漫主义诗学,骆一禾以及海子的新浪漫主义和刘小枫的“诗化哲学”是一种类似的思想存在,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启蒙和浪漫美学思潮的一部分。骆一禾经由1960年代的“内部读物”《存在主义哲学》而完成的诗学转化也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五 、“性灵本体论”:思想与诗的张力
思想与诗之间的张力不仅存在于骆一禾的诗学中,更直接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在解释长诗《世界的血》创作时说:“《世界的血》主要的主题是‘生命’,……全诗共分六章,以万灵合唱为始,以伟大生命为终,在哲学上是性灵本体论的。”然而,性灵本体论本身就是一个折衷的说法,性灵诚然是诗歌书写的对象,也是诗歌发生作用的方式,本体则直接是一个哲学概念。从诗歌隐喻到哲学概念恐怕还有不少距离。骆一禾的同代人陈超评论说:“在诗学立场上,骆一禾强调身心合一意义上的性灵本体论。但他反对由此导向‘放纵主义’(Bohemianism)――这是我们常见的诗人性灵扩张的后果。怎样整合这一矛盾状态?他选择了永恒理念图式对性灵的加入。这种‘加入’,使个体生命的性灵本体论不再按这个概念的准确内含体现于他的诗学中。因此,他的诗学意志很难施放于广大的诗人/读者,他们宁愿放弃他的诗学而专注于他的创作本身。这无论如何是十分可惜的事。”其实,骆一禾未尝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在《美神》中他就宣称自己主张一种“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这一概念似乎离诗学更为接近。
骆一禾从未隐讳对哲学概念的运用,不仅在文论中,甚至在诗篇里也是如此。他对昌耀诗歌的评论“趋于本体的超越努力”,同样也适合于他自己,这是一种雅斯贝尔斯式的向超越存在的飞跃。他津津乐道的“飞行”也只能作如是解,诸如长诗《世界的血》第一章“飞行(合唱)”,长诗《大海》第十三歌“飞行:驰往黑潮和斧子(洪波)”和第十四歌“飞行是另一个极端(峰)”。其中出现了这样的诗行:
光明而来,谁更向光明而去?
每一种未来之前
这光明的通道上 塔顶未全
失败建造了男子的双眼
光明倾注,不许睡眠
我注目光明之塔,父性耸动
于是加快飞行
飞行是塔顶完美。塔顶就全了。
——《大海》之《第十四歌:飞行是另一个极端(峰)》
在生活里我耕耘着我的躯体
提起犁铧
深深地翻开真实 屋宇四面升起
每逢我注视着精神般的 空旷的海
那无影无形 无边无际
我的心就忍不住嘭嘭地剧跳着
感觉到屋宇是无辜的
大自然在它的四周轰轰作响
生存在无声无息地带着它们运行
——《世界的血》之第六章《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穹顶)》
真理只能生存百年
一代人过去 一代人又来
激荡在我们奔腾的大限
只有在屋宇的筑造当中
巨大的日轮在我们的光里呈现
这才是我们获得的:今天
这人类所产生的都会消逝
那产生了的 儿女们仍要一一经历
那大地上流布的屋宇盛纳
那屋宇苏醒时大地也在苏醒
烈火于鸟背站立 今天一再一再
锤炼于我的屋宇
——《世界的血》之第六章《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穹顶)》
《大海》中“塔顶”意象即类似于《世界的血》中的“屋宇”或“穹顶”,《世界的血》以第一章《飞行》始,以第六章《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穹顶)》终。骆一禾诗歌的最大命意就是为人类生存建立一个精神基础。《世界的血》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第三章“世界之一:缘生生命(孤独动力)”和第五章“世界之二:本生生命(恐惧动力)”,骆一禾自己说过:“缘生出来的诗学,若不乏体验,则与诗创作不可分。”可见缘生生命实乃世俗生存或历史生存,也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自身存在”,而本生生命则是生命本原,亦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超越存在”或“本原”。这样看来,《世界的血》第四章“曙光三女神(颂歌)”可以看作从世俗生存到生命本原的过渡。骆一禾对世俗经验的书写不同于第三代诗人,后者和九十年代诗人一样相信通过经验的累加可以自动达到一个整体性,达到“大全”。骆一禾却更看重一个反思性的前提,和“大全”建立一种相对直接的逻辑关系。在骆一禾诗中总是有一些绕不过去的抽象概念名词,如在《世界的血》之第六章《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穹顶)》的诗行里,这尤其使他的长诗表现出诗歌隐喻与哲学概念之间的张力。缘生生命意象意在刻画世俗生存图景并对历史生存展开批判,长诗《大海》中的“金币地帝城”仿佛一个具有预言能力的集结了资本和权力之恶的反乌托邦,展现了一副生存的地狱图景;而本生生命意象则意味着生存的可能和未来,并反过来为民族生存甚至民族精神提供一副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图景,而这一点也契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和浪漫的思想潮流。
六、余论:骆一禾与八十年代文化意识
骆一禾成长并不幸殁于八十年代,是一位典型的八十年代文化之子。然而,他独特的诗学建构路径,尤其他对1960年代“内部读物”《存在主义哲学》的倚重都可以表明,八十年代的思想和诗学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和复活了在社会主义前期曾经受到压抑甚至批判的思想和诗学资源。骆一禾是一个值得考察的个案,不仅对于“内部读物”的隐秘影响,而且对于新时期个体诗学的神秘发生来说都是如此。而他由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海氏后期的语言转向),回溯到治疗“现代性”疾病的新浪漫主义,此一精神探险实在令人称奇;骆一禾的诗学转化先声夺人,并且走在了八十年代相关西学思想译介的前面。
骆一禾和荷尔德林的思想亲缘性并不弱于海子之于荷尔德林,而这是以前被低估的。在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中,与骆一禾、海子最为接近的无疑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尤其是刘小枫式的“诗化哲学”和周国平式的“诗人哲学家”。在《拯救与逍遥》的引言中,刘小枫还借审美主义的话题回顾了《诗化哲学》的思路:
最初,由康德所暗示的审美的终极解决,到席勒的极力推演,发展为一种明确的审美主义的主张。随后的早期浪漫派哲学在启蒙精神对神性传统的巨大冲击下,起初大都走向了这条由康德暗示、由席勒呼吁的审美之路。但在究竟审美最高还是神性最高的两难抉择面前,早期浪漫派哲学的代表们最终还是返回到神启的世界中去了(谢林、荷尔德林、F.施勒格尔、诺瓦利斯)。经过晚期浪漫派的折腾,尼采才终于看清上帝已死,重新举起审美主义的大旗。只有当神性的根基遭到摧毁之后,审美主义才会作为替代品被提出来。席勒和尼采都相信诗可以取代宗教,它具有调节的功能和解救的作用,任何带根本性的两难对立可以靠诗来沟通。
然而,骆一禾表现出一个相反的思维过程,由存在主义上溯到浪漫主义,再回溯到两希传统。这种溯洄从之的对“美神”的追寻,让骆一禾从单一的直线叙事中摆脱出来,也改变了刘小枫叙述中的审美主义的颓势,——由于对历史势能的耗尽,优越十足的审美主义未必不会显露颓势。不同于诗化哲学的单一目标,骆一禾的“精神诗化”则重新将诗学置于人类思想的核心,使其直面诗歌与哲学之争、启蒙与浪漫之争、启蒙与神性传统之争等诸多语境。但最终,骆一禾和刘小枫殊途同归。骆一禾的诗学建构预示着一条能够超越种种纷争的审美教育、陶冶和教化(Bildung)之路,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也完全能够支撑起这一条诗学教养和教化之路。教化的观念与启蒙并无矛盾,而是延续和补充了启蒙。这是我们重返八十年代时需要注意的。
骆一禾几乎接触到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诸如人道主义和异化、存在主义、美学热等等,并对之进行了一种有效的诗学转化。其诗学建构过程本身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镜像,而又对后者有所突围、偏离和重塑。这一方面固然有赖于骆一禾的思想能力,另一方面也和诗歌话语的独特性有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既是尼采意义上的“人类意志力的反规范性表现”,同时又是狄尔泰意义上的“人类经验的一种规范性表达”。诗学因而可以穿越文化意识的矛盾而获得一种圆融的表象,更为重要的是,诗学可以重塑文化意识并使之具有雄浑的感性。这也是美学教化的应有之义。可以说,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拥有一条从启蒙到教化的演变线索,而诗学和美学教化的观念应该是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发展顶峰,有论者称,“‘人道主义’的核心内涵便是秉持一种浪漫主义的主体性认知”,即是对这一条发展线索的体认,但在对启蒙的降格中也存在着将启蒙与教化混淆起来的危险。骆一禾深植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文化意识之中,这使他有可能形成一种有关诗人的自我教育和美学教化的观念。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转自潜溪文学:http://www.qianxiwenxue.cn/qxwx/vip_doc/25019877.html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本站免费提供电子诗集制作服务:提供100首诗歌作品,每首不超过28行,符合法规的诗歌作品,为歌颂党领导新时代的作品提供免费出纸版样书服务。简介、照片、作品发邮箱:jinyj@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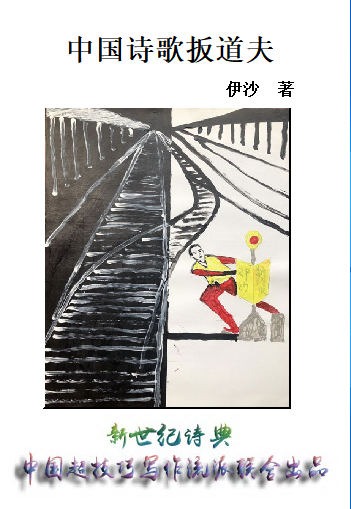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