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写西读掏话叨》二十九:戈麦

《东写西读掏话叨》计划:粗略分析名人诗论出现的著名诗人,选顶尖好诗人,显名大诗小者。
戈麦
原名褚福军,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祖籍山东省巨野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时年仅24岁。
如果种子不死
如果种子不死,就会在土壤中留下
许多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东西
这些地层下活着的物件,像某种
亘古既有的仇恨,缓缓地向一处聚集
这些种子在地下活着,像一根根
炼金术士在房厅里埋下的满藏子弹的柱子
而我们生活在大厅的上面
从来没有留意过脚下即将移动的痕迹
种子在地下,像骨头摆满了坟地的边沿
它们各自系着一条白带,威严地凝视着
像一些巨蚁被外科大夫遗忘在一个巨人的脑子里
它们挥动着细小的爪子用力地挠着
而大地上的果实即使在成熟的时候
也不会感到来自下方轻微的振动
神在它们的体内日复一日培养的心机
终将在一场久久酝酿的危险中化为泡影
读戈麦《如果种子不死》
作者:侍仙金童
这是诗人试图用诗的语言思考的留痕
他设置一个比喻然后静静地展开延伸
行文有跳跃如亘古既有的仇恨炼金术士
但都是依附于种子这个大的比喻之上的
这些跳动的意象有助于种子形象的完善
毕竟诗人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完美表达
所以试图用更多意象加以补充及润色
这比臧棣随意截取生活画面拼凑要规矩
即使鼓吹这是臧棣的创作魔法也没用
虽然这首诗如愿表达出了悲观和无奈
但相对于诗的精要简洁显然过于杂乱
诗人着力在每一刀的花饰上多匠人气
而诗歌的灵性往往会被这些人造物所伤
有人说戈麦的创作是追随海子显然胡诌
如果用诗性表述海子是空气戈麦是地气
海子是浪漫主义泡沫破灭走向铁轨
戈麦是现实主义顽石所伤走向水底
撇开附着物单看文本都未抵达诗艺标高
引起共鸣大多是因触事悲己的情绪所致
不乏过度占用诗歌上升通道的人来哭坟
真相不影响清醒者对他们热爱过诗的尊敬
即使死亡仪式一个没带诗集一个撕毁诗稿
也许我们确实不能对诗歌期望值太高
它不能带我们脱离苦海但诗确有能量
如果沉浸诗歌海洋就能看到无限生机
但是心生妄念也会破坏诗歌固有生态
2023-11-29
(粗读的第一印象,期待随着阅读量增加观点会转变,真实记录每一次阅读后的直觉,如有冒犯敬请谅解。)
02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草生长的时候,我在林中沉睡
我最后梦见的是秤盘上的一根针
突然竖起,撑起一颗巨大的星球
我感到草在我心中生长
是在我看到一幅六世纪的作品的时候
一个男人旗杆一样的椎骨
狠狠地扎在一棵无比尖利的针上
可是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这就和
没有人站在草坪的塔影里观察一小队蚂蚁
它们从一根稗草的旁边经过时
草尖要高出蚂蚁微微隆起的背部多少,一样
但草不是在我心中生长
像几世不见的恐慌,它长过了我心灵的高度
总有一天,当我又一次从睡梦中惊醒
我已经永远生活在一根巨草的心脏

03
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
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
黑夜像一片沉默的沙子填满了高悬海面的岸
成千上万的克里特人曾经攻打一座孤独的城
现在,成千上万的沙子围困一颗破碎的心
此时除了我,不会再有什么人在等候
我就是这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盏黑暗的灯
是最后一个夜晚水面上爱情阴沉的旗帜
在黑暗中鞭打着一颗干渴的心沿着先知的梯子上下爬行
我所等候的人一定不是感情冷漠的人
蒙着一团湿漉的衣服像沙漠上的一团炽烈的火
她所稔熟的艳枝早已向死者们奉献
在罗德,星星斜着忧伤的尾巴挂在天空
我倚着空空的躺椅还在等候着什么
像山坡后的一株草其实并没有静候掠过他的那一阵干燥的风
04
献给黄昏的星
黄昏的星从大地海洋升起
我站在黑夜的尽头
看到黄昏像一座雪白的裸体
我是天空中唯一 一颗发光的星星
在这艰难的时刻
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人类的昨天
三个相互残杀的事物被怼到了一起
黄昏,是天空中唯一的发光体
星,是黑夜的女儿苦闷的床单
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
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竟能梦见
这荒芜的大地,最后一粒种子
这下垂的时间最后一个声音
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件事情,黄昏的星
05
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
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是不幸的人
他们是一队白袍的天使被摘光了脑袋
悒郁地在修道院的小径上来回走动
并小声合唱,这种声音能够抵达
塔檐下乌鸦们针眼大小袖珍的耳朵
那些在道路上梦见粪便的黑羊
能够看见发丛般浓密的白杨,而我作为
一条丑恶的鞭子
抽打着这些抵咒死亡的意象
那便是一面旗,它作为黑暗而飞舞
死后,谁还能再看见阳光,生命
作为庄严的替代物,它已等待很久
明眸填满了褐色羊毛
可以成为一片夜晚的星光
我们在死后看不到熔岩内溅出的火光
死后我们不能够梦见梦见诗歌的人
这仿佛是一个魔瓶乖巧的入口
飞旋的昆虫和对半裂开的种子
都能够使我们梦见诗歌,而诗歌中
晦暗的文字 就是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们
06
彗星
你莅临这生长人番的汪洋
几千日一个轮转,你为何不能遗忘
这指针一样精确的记忆
抛进大海它只是一颗颗瘦小的盐粒
千万颗灰尘,你用其中的一个
印刻了我们这个默默无闻的球体
当故国的河山又一次印章一样在下界闪现
你空茫的内核为之一颤
万人都已入睡,只有我一人
瞥见你,在不眠之夜
神秘之光,箭羽之光
砂纸一样地灼烧,我侧耳倾听
今夜过后,你是燃毁于云层
还是穿越环形的大地,这可怕的意念
在茫茫的寰宇之中我触及了
你一年一度的隐痛和焦虑
人迹罕至,惊人的景象已不多见
在沉酣如梦的世上,今夜
这星球之上,只有一双尘世的双眼,望着你
你寒冷的光芒已渐趋消弱
多年之后,你运行的海王星的外围
在椭圆的诡计最疾速易逝的弧段
你的内心为遥远的一束波光刺痛
那唯一的目击熬不过今夜,他合上了双眼
07
眺望时光消逝
箭羽飞逝的声音还在鸣响,停留的是光的影子
马的背影留下的只有风声,风头已汇入旷宇
只有天空中一只大箫,用雷声挽留在匣中的天籁
一切变得像你刚刚叠起的乌云,海兽沉伏的项背
多少个钟点,光终于走完一把利刃的形状
斩断天堂的钢索,垩白而真实,它大而无形
群星寂灭,理性的组合舱变得亏空
由一个单数到复数,造物主的精神像雪迹一样污黑
岩石在大地上迟滞,像是树木的纹理上生长的岩石
白垩的光,白垩的表面像是自生自灭的晶体
盛开的大丽,自主而无边,冷漠的花的海洋
一只大鱼驮走神器,驮走一箱箱的言语
还会有异象在天际闪现,像被摘成倒刺的闪电
“V”字形密得像暴雨,向地缘处的深渊扎着
是时间倒立而出的脚,不可复得的脚
显现给世界最后一种物质,它带着一声尖叫
不断有隆起的身影向上漂浮,由最小处上升
向我们表达最终的问候,这些弓起而相背的脸呀
是光,从最大处消失,像有的罪的天使
不能原谅,伴随着时光,恒星离我们远去


戈麦,或不死的种子
文/胡续东
1991年9月,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同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诗人戈麦在万泉河自沉。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戈麦是什么人,因为我那时还和那几届不幸的北大新生一样,在石家庄接受整整一年的“军政训练”。一年以后,我才正式跨进北大的校门,并迅速开始写作。随着习诗阶段对戈麦其人其事其诗的逐步深入的了解,我越来越觉得,我和这个在我考上北大的同时悄然逝去的诗人之间,似乎有一种超出了阅读、领悟、技艺承传的神秘的联系。
几乎所有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诗人,特别是在各大高校依靠一种近乎于兄弟情谊的帮会伦理来相互砥砺的习诗者,都有一段迷恋在那时刚刚逝去的海子和戈麦的时期。我也不例外。在习诗的早期生涯里,海子和戈麦总是成为朋友们之间谈论诗歌的中心话题,关于他们的诗歌理想、他们的才能和禀赋、他们的死亡和他们留给我们的可供汲取的技艺。我记得当时我还曾经为无法在海子和戈麦之间确认最喜爱的一个而苦恼终日——因为虽然海子的作品凭借其剧烈的情感强度和诡异的想象力可以让我烂熟于心,但戈麦作品中的纯正、绝望、谦逊和强大的表意密度也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戈麦的很多“写作性格”被当时的我们当作“遗训”草草继承了起来。譬如在“逃避抒情”的理念下进行更谨慎和隐秘的抒情;譬如在“厌世者”的自况之中为诗歌开辟另一个自足的想象世界;譬如在“诗人是发现奇迹的人”的信条之下在各种习以为常的表达素材中挖掘“元素态”的诗意;譬如书写一种铿锵、缜密、具有戏剧对白性质的“无韵体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诗歌写作、尤其是对诗歌和当代生活之间的一种微妙而富有喜剧性的互文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朋友们之间的诗歌话题开始偏离了“死亡的加速度”或者“我们脊背上的污点”,更多地讨论着精湛而狡猾的技艺手术刀如何在驳杂的万象和漆黑的记忆之间来回穿梭。戈麦,还有海子,渐渐地从我们的日常切磋之中消失。
但这是否意味着戈麦就真的成为一种被“厌弃”的过期精神商品?不。在北大,近10年以来,每年都有纪念海子的春季未名湖诗会和纪念戈麦的秋季诗会,由于我是这两个小小的“传统活动”的肇始人之一,几乎年年都要参加,而每次在参加活动之前我多少都要重温这二位诗歌“先贤”的作品,因而,我总是将每年自己在诗歌上新的想法和做法和海子、戈麦所形成的某种不定形的“传统”相比较。我发现其中的继承还是远远大于断裂和背离。海子,尤其是戈麦,他们作品中的某些品质已经成为我们写作中牢固的后景,成为我们理解诗歌的某种前提,就像我们日常的言谈无须逐个用拼音拼读出来一样,他们的写作抱负、写作伦理、写作技艺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常识和“前理解”之中了。这不是“过期”,而是更深的渗透,一种不被察觉的敬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面对戈麦(包括海子),我永远怀着一个离乡别井闯世界的人对他的乡村启蒙教师所怀有的难以言传的感激之情。
戈麦的那首《如果种子不死》我一直非常偏爱,虽然它在戈麦丰富、多变的诗歌作品中并不属于在技艺上无可挑剔的那一类,但我偏爱它的理由非常简单,一是它像谶语一样说出了戈麦自己死后他的诗歌在汉语诗歌史上的命运,二是它隐约触及了我在前面提到的、我所感到的我和他之间的某种神秘的关联。这首诗中写道:
如果种子不死,就会在土壤中留下
许多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东西
这些地层下活着的物件,像某种
亘古既有的仇恨,缓缓地向一处聚集
在我看来,戈麦的诗歌正是一粒不死的种子,它在汉语的土壤里和所有其它怀着伟大的诗歌理想的汉语诗人所留下的未竟事业一道,在后来者写作行为的深层驱动空间释放着隐秘的力量,这力量终将促使迟到的现代汉语诗歌以复仇者的身份向古典、向世界诗歌索取它应有的成熟。
转自网络: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1107/20/49165069_1054990582.shtml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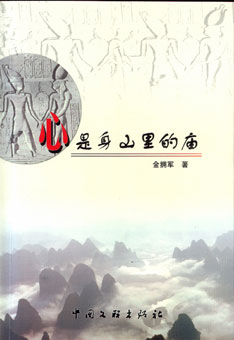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