怼余秀华的“食指”变成了中指

怼余秀华的“食指”变成了中指
这几天疑似得了流感,高烧刚退,在家养病,本来想写的一篇文字就被搁下了,想起来重新炒一下冷饭。
诗人食指在一场活动中突然炮轰余秀华,原文如下:
“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曾被媒体污名化为“脑瘫诗人”的余秀华也不甘示弱,直接怼回去,除了微博回应,还写了一篇《兼致食指,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其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活着,是因为我们在寻找真理,一个不明白真理是何物的人是说不出来真话的。如同孩子那样,他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对,那是真话。但是还有一句话叫:童言无忌!是人们不与他计较,而不是他说的就是对的。而大人呢。大人如果还这样,那是无知而不是真诚。”
我不懂诗,但是也听过食指的名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还有他十年后写下的姊妹篇,“但我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个性/虽是历经挫败,我绝不轻从/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读这些文字,我还是非常喜欢食指先生的,有评论表达得更精准,这首诗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理想主义中出现的裂缝,人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初步觉醒。此诗从情调到结构上,都有一种缓缓拉开的张力,体现出它开始告别一个集体暴力的诗歌时代,而开启了对个人真实心灵中矛盾纹理的凝神与吟述”。
然而,写下这首《相信未来》的半个世纪之后,食指先生却在制造新的“集体暴力”,当他用“农村出来的诗人”这种身份去定义余秀华的时候,就在制造刻板印象,并且用群体特征来直接定义诗人该怎么写,食指先生似乎忘了当年这首《相信未来》就是被“点名批评”的对象,真是无比讽刺。
唐山在针对此事的评论中指出二人话语体系完全不同,俨然在两个平行空间中“对话”,几乎无法达成共识。而食指意在强调白话诗应该回归“大众性”与“民族性”,通过批评余秀华来表达他的焦虑。恰恰是这种“大众性”与“民族性”的标准,最值得质疑。
这个标准被宗城称之为“士大夫诗人”的标准,这一代诗人心中总存着“修齐治平”的理念,如果从美学上追溯,这恐怕是儒家美学系统下,有关社会功能的审美主张,将“善”置于“美”之前,尽善尽美,艺术被赋予教化功能。延续到新中国成立,现实主义艺术大行其道,将音乐、绘画、文学都被作为工具,容易失去艺术的主体性。
然而,我们应该警惕,家国天下的“大众性”与“民族性”标准,可能是鸡血,也可能是屠刀。
有评论说,“余秀华是贴上了命运坎坷的底层农民诗人标签的,作为该标签的明显受益者,她固然有随着现实命运的改变而不断调适自己诗歌形象的自由,但别人也有权以她过去赖以成名的作品,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这种论调的搞笑之处,就在于你因别人贴的标签受益,别人就有权以标签来提要求和期望。
诗人什么时候要通过标签评判,诗歌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审美主体,不针对语言和意象,直接用社会功能和阶层属性来评判?这与思想警察何异?
如果用食指的标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小情小调,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阿谀奉承之作,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就不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柳永的“寒蝉凄切”不过是个眠花宿柳者的自哀,林妹妹的“花谢花飞花满天”不过是小女子情态……到了白话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是否也脱离了“大众性”和“民族性”的标准而值得被批判?
我甚至极端地认为,给诗歌制定标准,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任何脱离审美意义的标准,都是耍流氓。当然,在美学主张上可以有康德或者黑格尔之分,但一定要附加上标签以及相关的社会功能,就是另外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语言霸权。
艾略特曾说,“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乃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通过语言建立“想象的逻辑”和“想象的秩序”,这是艾略特一种学究式的实践和探索,他认为“某一语言的伟大作家应该是该语言的伟大仆从”,《T.S.艾略特的标准》一文认为《荒原》追寻着基督教精神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可能性,而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试图探究的是基督教精神的个体可能性。
就这个意义上,艾略特与里尔克,难道有高下之分吗?
说到到里尔克,我想起他在写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内容,“你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若是这个答复表示同意,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单纯的“我必须”来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都必须是这个创造冲动的标志和证明。然后你接近自然。你要像一原人似地练习去说你所见、所体验、所爱、以及所遗失的事物。”
冯至在《我们为什么要读里尔克》里写到,“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是情感,但是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遍尝众生的苦恼一般。”
食指对余秀华的评论之所以让我感到恐惧,是这种诛心式的批判竟然再次出现在文学的范畴,出自一个曾受文革压迫的诗人。这种霸权复制,让中国的言论空气陷入恶性循环:
首先是功能性前置于美学之前。“从农村出来的诗人,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这不仅对诗人的单一身份进行了限定,更包含了对诗歌功能的约束。难道农民的生活就一定是痛苦的?或者说,“喝喝咖啡聊聊天”不是对小康生活的向往?在我看来,这种向往有着比小康生活这种物质目标更丰富的精神追求,“打打炮”还表达了从身体到灵魂的解放。如果诗歌只有一种功能,整个社会连诗歌这种最“没用”的艺术,都要“有用”,都必须要肩负起家国天下,那我们这身体和灵魂,都不过是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即使涂上鲜艳的色彩,也无法获得自由,还让我们相信一个怎样的未来?
其次是身份对个人的取代。诚如里尔克所说,“请走向你的内心”,而每个人的内心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农村人这个身份来说,农村本来就是有差异的,陕北土窑洞、河南平原、东北黑土地、江苏华西村……农村这个群体本来就千差万别,忽略语境的批判只能说明浅薄。而即使具体到一个村里,也有个体差异,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利用集体身份取代个人选择,是对个体的侵犯和要挟,也是对自由的漠视,如此写出的文字,与“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口号无异,这倒是符合“大众性”与“民族性”的标准,口号存在,诗却死了。
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食指的指责,是阶级观念介入文化领域的死灰复燃。有评论戏谑“食指变成了中指”,他的言论中先强调了“农民”,第二强调了“历史”,要“对历史负责”,北京大学的罗新恰好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过去是此刻之前的一切,是一团混沌,当我们从中抽取某些内容,赋予它意义与秩序,并讲述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了历史。”而食指如此强调历史和群体身份,恐怕回到了狭义的阶级冲突史观,有人说这是士大夫诗人,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是给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给别人扣帽子。只能表达阶级利益、民族国家乃至家国天下的诉求,这种限定背后隐含了阶级和道德判断,仿佛“小生活”就是自私的、小资的。这种观念,恰恰是文化清洗和压迫的思想根源。
诗人,可以自己去经验,可以用自己的探求使语言就范,可以创造自己的意象国度,可以如堂吉诃德般冲向怪物,但不可以如大字报一般,以道德和阶级为名,把语言的刀剑抛向另一个自由的诗人。
冯至引用了里尔克的《随笔》:“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 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想到儿童的疾病……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许多的海,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 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得到。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要记住分娩者痛苦的呼喊,和轻轻睡眠着、翕止了的白衣产妇。但是我们还要陪伴过临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息。……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
在我心中,诗人是纯洁而任性的孩子,就像顾城那首: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针砭时弊,不舍慈悲
理性思考,不许骂人
转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0403156908334498&wfr=spider&for=pc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cn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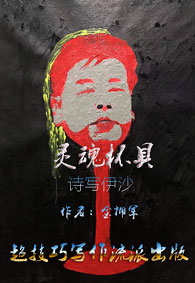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