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诗歌再批判之《河流》
于坚诗歌再批判
陈仲义在其《叙述与抒情的 “博弈”——以于坚诗为中心》对于坚大加赞赏,一会儿称其是抒情高手,一会儿说他获得切片专利金奖,一会说他是大象级诗人,这让我想到第一次批判于坚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韩东称其为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是第三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已被当代文学是反复描述的诗人,是一位开宗立派的诗人,于是又激发起了我第二次批判于坚的兴趣。这次就参照陈仲义《叙述与抒情的 “博弈”——以于坚诗为中心》一文中出现的于坚作品进行批判。
陈仲义在文中写到:“早期于坚,也算得上抒情高手,左拥《河流》(1983)右抱《高山》(1984),1990年代发出《哀滇池》,排比复沓、疾呼问责,率领众多语气词、感叹号,浩浩荡荡。及至超高《飞行》:“在机舱中我是天空的核心/在金属的掩护下我是自由的意志”“万物中的一员 我也是光辉中的生命/神啊 我知道你的秘密”,近乎某种神谕的代言。照此路线,于坚成为后浪漫时期最后一批抒情诗人之一,与“扑向太阳的豹”们平起平坐,不是没有可能。但于坚不想重返老路,他意识到一个不可避免的工业化时代,必须要有另一种言说出路,这种出路必然反浪漫,恢复物的原生态,并以原初的词说出它的“呈现”。”那么这次我们就把于坚这四首诗比下去:
《河流》
在我故乡的高山中有许多河流
它们在很深的峡谷中流过
它们很少看见天空
在那些河面上没有高扬的巨帆
也没有船歌引来大群的江鸥
要翻过千山万岭
你才听得见那河的声音
要乘着大树扎成的木筏
你才敢在那波涛上航行
有些地带永远没有人会知道
那里的自由只属于鹰
河水在雨季是粗暴的
高原的大风把巨石推下山谷
泥巴把河流染红
真像是大山流出来的血液
只有在宁静中
人才看见高原鼓起的血管
住在河两岸的人
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
但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听见人们谈论这些河
就像谈到他们的神
这首诗作为日常练笔是及格的,因为有点像老师布置了一个歌颂家乡的作文,于坚为了完成写作任务按时写出来了,这首诗读完给我的印象之一就有这个点。只要读者不被陈仲义那种诗论鼓吹而迷惑,这首诗的普通就很明显,首先技法上就是常规套路,就是一张照片上出现的构图色块的介绍:“河水流过峡谷、没有巨帆没有海鸥、乘坐木筏航行、大风吹落巨石、河水变成血色、于坚想到神。”,这些色块有些出现在画面上,有些没有的风帆、海鸥也被写进去,包括最后于坚想到点睛的升华主题的神。这首诗通过对故乡的回忆展开,在叙述中由静至动地写河流,由河水舒缓的流动进入雨季河流的粗暴,最后将故乡的河流提升到和神话一样的高度。这首诗的语言是极其平常的,而且于坚最后的点睛之笔还是在平庸的高度,主要在于技法和想象毫无新意。这首诗在小说中装饰下还可以,如果单选出来当做优秀的诗是不够格的,及格没问题。我找几首好诗比较下:
《车过黄河》
(伊沙)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我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做眉檐
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帐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功夫
黄河已经流远
中国诗歌评论界有个极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把诗往反叛精神上联想,以为有抗争精神就可以入史,正如能够入人类史的都是一些革命事件爆闪的节点,而总是忽略普通人的生活画面及其感悟。在大容量存储设备出现之前,这是没办法的,就算一个人的一生也只会记录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经历,不过如今存储设备容量巨大,记录人类活动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存储了,那么诗歌史也会逐步扩大收藏品种。伊沙《车过黄河》的出名虽然有诗评家的一臂之力,但文本内容总体意识是高于于坚的《河流》的,在九十年代,能将小便入诗就是一种先锋性是诗创的革命性突破,几十年后的现在是不觉得稀奇,但在当时确实是技惊四座的,这个亮点于坚的《河流》就没有,它只有平淡的像中学生完成老师写作任务的听话懂事。伊沙这首诗从头至尾都是叙事,但是按照评论家的过度解读,这首诗完成了一次很伟大的抒情。伊沙好像说过他写作现场并没有“颠覆了关于祖国母亲河的神话,是对传统观念的权威与规约的反叛,”的意识,或许会有伊沙并未察觉的这个潜意识在影响他的这次创作,这也可以理解,正如我们的写作有时确实不是自发的而更像是被动的催生出来的。而评论家品出这个反叛意识,且不说是不是伊沙本义,但能借此看到中国诗歌评论界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有一股力量在引导舆论,让人感觉是不是神仙在为下一次打架做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力量,把诗歌的本职工作扭曲了,所以中国诗坛宣传一个海子就引出麦地潮,宣传一下朦胧诗就引出一大批模仿者,解读伊沙的反叛意识就出现一大批先锋诗人。我在想,为什么这股力量从来不选真正高于海子、于坚的优秀作品宣传呢?很显然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诗歌上。《车过黄河》从技巧上看并不是伊沙最好的,甚至可以说这首诗伊沙没有刻意运用技巧,但是他里面的点正好成为了那股力量的可用之物。再联想到崔健的《一块红布》,北岛的《回答》,你就能感受到那股力量,是神仙备战的力量。如果我说的你不懂,那可以再联想到王勃被高宗逐出沛王府的《檄英王鸡》,你或许就懂了,历史是螺旋循环下前行的,地球和光的运动都是这个模式,或许这就是宇宙模式,人逃不了,人类历史也逃不了。于坚写的是小我的母亲河,伊沙写的是大我的母亲河,伊沙的手法上有突破,于坚相对传统保守,于坚在布局上有动静的处理,伊沙则显得更随性。从伊沙几十年的写作进程看,他是有主动放弃技巧向下的运动趋势,他是在试图寻找诗的原点并回到最本真的写作状态的,也就是那种无我无技巧的最纯的炁态写作,就是传说的大道的状态。而于坚没有过伊沙的高级技巧的,虽然他表明自己反技巧反抒情反隐喻,但他自己并不是到达了技巧抒情隐喻的高级状态后放弃的,这和伊沙不同,所以于坚的反没有底气比较空也不值得推崇,如果研究他的理论会发现他缺失一块,就是伊沙有过的高级技巧的运用。伊沙的高级技巧的运用反而不是他的名篇,譬如《最后的长安人》、《木偶剧团》、《张常氏你的保姆》等,对技巧的探索属于诗歌本职工作的基础工作之一,虽然它会一定程度限制诗创,或许伊沙有意识地逐渐放弃技巧性,就是为了在尽可能最大化的创作面上进行探索,寻找新的突破点。于坚《河流》结尾安排神出场,其实是为了拔高自己,这不是潜意识的行为,是一种故意,是于坚精心安排的。只可惜从河流的静动叙述来引出神,有点牵强僵硬甚至造作,因为单靠对河流一般性叙述的铺垫,不足以把神请上来。而伊沙没有向上的妄念,他反而是向下的一泡尿,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势能。
说到诗歌技巧和艺术性,我也搬来自己的《诗歌的源头是有话要说》:
《诗歌的源头是有话要说》
诗歌的源头是有话要说
涓涓溪流只见鱼肥虾多
艺术雕琢太多就是泥沙
老百姓只能打口井养家
翻译古诗诠释新诗的人
成了自来水厂和漂白粉
真知应是生命的救苦药
艺术家采药总在那山脚
大诗人把自己看得威武
怕你只是评论家的玩物
用泥沙将河床抬得高高
你是黄河千万别破堤了
用工业废水把诗歌弄脏
你们却一哄到京城领奖
当你们汹涌地流入海口
又要弄晕多少鱼苗的头
1999年
相对于于坚的看河是河,我的诗歌之河就有明显的艺术性,这是一目了然不需要借助评论家过度解读就有的。于坚《河流》的平庸就是他只描写了河流的自然呈现,没有经过诗化处理,虽然最后的神化收尾也没有达到诗化的目的,这是功力不够的表现。我的《诗歌的源头是有话要说》从诗歌的源头说起,在被著名诗人和评论家误导的无数源头中正本清源,写诗就是有话要说,不是无话找话不是装腔作势不是无病呻吟。“涓涓溪流只见鱼肥虾多”就是诗歌语言不要晦涩难懂,而这个发声,就是针对当下看不懂的诗大行其道的现实,诗要写得清澈。“真知应是生命的救苦药”,不是北岛们毫无建设性地呐喊,如果真有智慧,那就拿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来。“用泥沙将河床抬得高高”,于坚、韩东就是把自己看得威武的大诗人,平庸作品获得泥沙般赞誉的抬举,抬得再高,也让人担心“你是黄河千万别破堤了”。“用工业废水把诗歌弄脏”又让人联想到臧棣的《诗歌植物学》工业模具的量产。我在1999年写了这句“你们却一哄到京城领奖”,从臧棣获鲁奖的2022年来看,这个现象持续的时间够久了,这期间也是读者逃离诗歌阅读的空窗期。诗歌失去了读者已经很可怕了,而最可怕的是,这些工业废水污染的诗歌,正“汹涌地流入海口”,又不间断地“弄晕多少鱼苗的头”,在祸害诗歌初学者的大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样一比较,不怪我小看了于坚这首《河流》吧!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人救护车发布,转载内容来自网络有链接的会添加,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原出处,本站含电子诗集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会立即删除,致敬诗人!
本站免费提供电子诗集制作服务:提供100首诗歌作品,每首不超过28行,符合法规的诗歌作品,为歌颂党领导新时代的作品提供免费出纸版样书服务。简介、照片、作品发邮箱:jinyj@sia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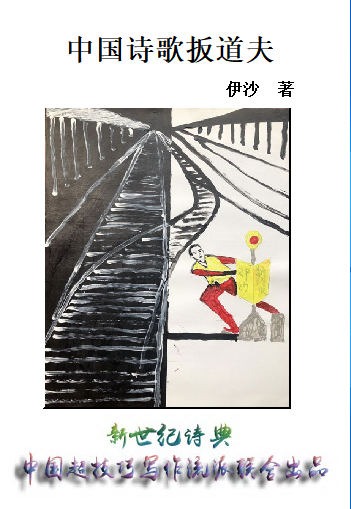







 皖ICP备2022012765号-1
皖ICP备2022012765号-1